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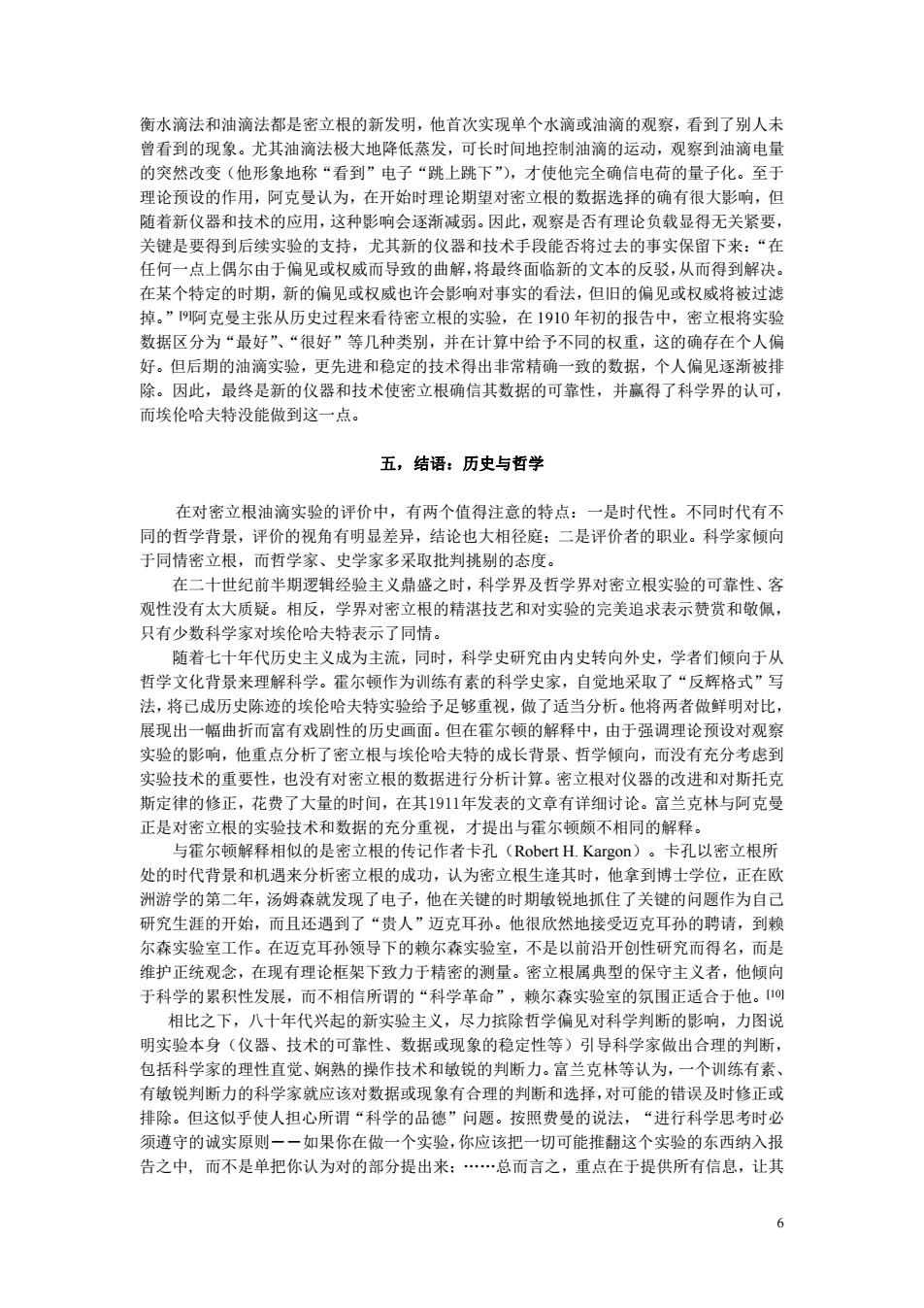
衡水滴法和油滴法都是密立根的新发明,他首次实现单个水滴或油滴的观察,看到了别人未 曾看到的现象。尤其油滴法极大地降低蒸发,可长时间地控制油滴的运动,观察到油滴电量 的突然改变(他形象地称“看到”电子“跳上跳下”),才使他完全确信电荷的量子化。至于 理论预设的作用,阿克曼认为,在开始时理论期望对密立根的数据选择的确有很大影响,但 随着新仪器和技术的应用,这种影响会逐渐减弱。因此,观察是否有理论负载显得无关紧要, 关键是要得到后续实验的支持,尤其新的仪器和技术手段能否将过去的事实保留下来:“在 任何一点上偶尔由于偏见或权威而导致的曲解,将最终面临新的文本的反驳,从而得到解决。 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新的偏见或权威也许会影响对事实的看法,但旧的偏见或权威将被过滤 掉。”阿克曼主张从历史过程来看待密立根的实验,在1910年初的报告中,密立根将实验 数据区分为“最好”、“很好”等几种类别,并在计算中给予不同的权重,这的确存在个人偏 好。但后期的油滴实验,更先进和稳定的技术得出非常精确一致的数据,个人偏见逐渐被排 除。因此,最终是新的仪器和技术使密立根确信其数据的可靠性,并赢得了科学界的认可, 而埃伦哈夫特没能做到这一点。 五,结语:历史与哲学 在对密立根油滴实验的评价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时代性。不同时代有不 同的哲学背景,评价的视角有明显差异,结论也大相径庭:二是评价者的职业。科学家倾向 于同情密立根,而哲学家、史学家多采取批判挑剔的态度。 在二十世纪前半期逻辑经验主义鼎盛之时,科学界及哲学界对密立根实验的可靠性、客 观性没有太大质疑。相反,学界对密立根的精湛技艺和对实验的完美追求表示赞赏和敬佩, 只有少数科学家对埃伦哈夫特表示了同情。 随着七十年代历史主义成为主流,同时,科学史研究由内史转向外史,学者们倾向于从 哲学文化背景来理解科学。霍尔顿作为训练有素的科学史家,自觉地采取了“反辉格式”写 法,将己成历史陈迹的埃伦哈夫特实验给予足够重视,做了适当分析。他将两者做鲜明对比, 展现出一幅曲折而富有戏剧性的历史画面。但在霍尔顿的解释中,由于强调理论预设对观察 实验的影响,他重点分析了密立根与埃伦哈夫特的成长背景、哲学倾向,而没有充分考虑到 实验技术的重要性,也没有对密立根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密立根对仪器的改进和对斯托克 斯定律的修正,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其1911年发表的文章有详细讨论。富兰克林与阿克曼 正是对密立根的实验技术和数据的充分重视,才提出与霍尔顿频不相同的解释。 与霍尔顿解释相似的是密立根的传记作者卡孔(Robert H.Kargon)。卡孔以密立根所 处的时代背景和机遇来分析密立根的成功,认为密立根生逢其时,他拿到博士学位,正在欧 洲游学的第二年,汤姆森就发现了电子,他在关键的时期敏锐地抓住了关键的问题作为自己 研究生涯的开始,而且还遇到了“贵人”迈克耳孙。他很欣然地接受迈克耳孙的聘请,到赖 尔森实验室工作。在迈克耳孙领导下的赖尔森实验室,不是以前沿开创性研究而得名,而是 维护正统观念,在现有理论框架下致力于精密的测量。密立根属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倾向 于科学的累积性发展,而不相信所谓的“科学革命”,赖尔森实验室的氛围正适合于他。 相比之下,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实验主义,尽力摈除哲学偏见对科学判断的影响,力图说 明实验本身(仪器、技术的可靠性、数据或现象的稳定性等)引导科学家做出合理的判断, 包括科学家的理性直觉、娴熟的操作技术和敏锐的判断力。富兰克林等认为,一个训练有素、 有敏锐判断力的科学家就应该对数据或现象有合理的判断和选择,对可能的错误及时修正或 排除。但这似乎使人担心所谓“科学的品德”问题。按照费曼的说法,“进行科学思考时必 须遵守的诚实原则一一如果你在做一个实验,你应该把一切可能推翻这个实验的东西纳入报 告之中,而不是单把你认为对的部分提出来:…总而言之,重点在于提供所有信息,让其 66 衡水滴法和油滴法都是密立根的新发明,他首次实现单个水滴或油滴的观察,看到了别人未 曾看到的现象。尤其油滴法极大地降低蒸发,可长时间地控制油滴的运动,观察到油滴电量 的突然改变(他形象地称“看到”电子“跳上跳下”),才使他完全确信电荷的量子化。至于 理论预设的作用,阿克曼认为,在开始时理论期望对密立根的数据选择的确有很大影响,但 随着新仪器和技术的应用,这种影响会逐渐减弱。因此,观察是否有理论负载显得无关紧要, 关键是要得到后续实验的支持,尤其新的仪器和技术手段能否将过去的事实保留下来:“在 任何一点上偶尔由于偏见或权威而导致的曲解,将最终面临新的文本的反驳,从而得到解决。 在某个特定的时期,新的偏见或权威也许会影响对事实的看法,但旧的偏见或权威将被过滤 掉。”[9]阿克曼主张从历史过程来看待密立根的实验,在 1910 年初的报告中,密立根将实验 数据区分为“最好”、“很好”等几种类别,并在计算中给予不同的权重,这的确存在个人偏 好。但后期的油滴实验,更先进和稳定的技术得出非常精确一致的数据,个人偏见逐渐被排 除。因此,最终是新的仪器和技术使密立根确信其数据的可靠性,并赢得了科学界的认可, 而埃伦哈夫特没能做到这一点。 五,结语:历史与哲学 在对密立根油滴实验的评价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一是时代性。不同时代有不 同的哲学背景,评价的视角有明显差异,结论也大相径庭;二是评价者的职业。科学家倾向 于同情密立根,而哲学家、史学家多采取批判挑剔的态度。 在二十世纪前半期逻辑经验主义鼎盛之时,科学界及哲学界对密立根实验的可靠性、客 观性没有太大质疑。相反,学界对密立根的精湛技艺和对实验的完美追求表示赞赏和敬佩, 只有少数科学家对埃伦哈夫特表示了同情。 随着七十年代历史主义成为主流,同时,科学史研究由内史转向外史,学者们倾向于从 哲学文化背景来理解科学。霍尔顿作为训练有素的科学史家,自觉地采取了“反辉格式”写 法,将已成历史陈迹的埃伦哈夫特实验给予足够重视,做了适当分析。他将两者做鲜明对比, 展现出一幅曲折而富有戏剧性的历史画面。但在霍尔顿的解释中,由于强调理论预设对观察 实验的影响,他重点分析了密立根与埃伦哈夫特的成长背景、哲学倾向,而没有充分考虑到 实验技术的重要性,也没有对密立根的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密立根对仪器的改进和对斯托克 斯定律的修正,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在其1911年发表的文章有详细讨论。富兰克林与阿克曼 正是对密立根的实验技术和数据的充分重视,才提出与霍尔顿颇不相同的解释。 与霍尔顿解释相似的是密立根的传记作者卡孔(Robert H. Kargon)。卡孔以密立根所 处的时代背景和机遇来分析密立根的成功,认为密立根生逢其时,他拿到博士学位,正在欧 洲游学的第二年,汤姆森就发现了电子,他在关键的时期敏锐地抓住了关键的问题作为自己 研究生涯的开始,而且还遇到了“贵人”迈克耳孙。他很欣然地接受迈克耳孙的聘请,到赖 尔森实验室工作。在迈克耳孙领导下的赖尔森实验室,不是以前沿开创性研究而得名,而是 维护正统观念,在现有理论框架下致力于精密的测量。密立根属典型的保守主义者,他倾向 于科学的累积性发展,而不相信所谓的“科学革命”,赖尔森实验室的氛围正适合于他。[10] 相比之下,八十年代兴起的新实验主义,尽力摈除哲学偏见对科学判断的影响,力图说 明实验本身(仪器、技术的可靠性、数据或现象的稳定性等)引导科学家做出合理的判断, 包括科学家的理性直觉、娴熟的操作技术和敏锐的判断力。富兰克林等认为,一个训练有素、 有敏锐判断力的科学家就应该对数据或现象有合理的判断和选择,对可能的错误及时修正或 排除。但这似乎使人担心所谓“科学的品德”问题。按照费曼的说法,“进行科学思考时必 须遵守的诚实原则――如果你在做一个实验,你应该把一切可能推翻这个实验的东西纳入报 告之中, 而不是单把你认为对的部分提出来;……总而言之,重点在于提供所有信息,让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