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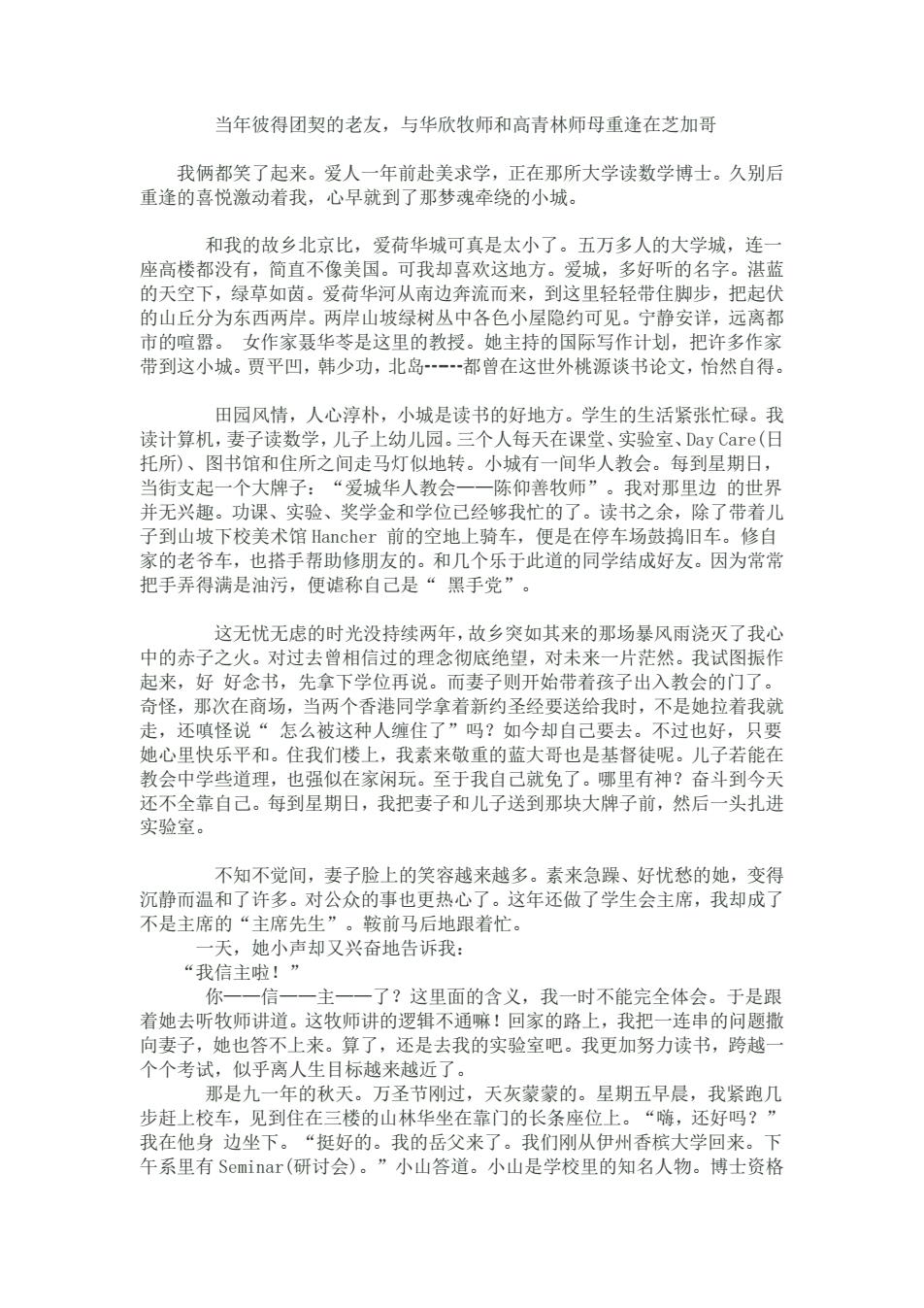
当年彼得团契的老友,与华欣牧师和高青林师母重逢在芝加哥 我俩都笑了起来。爱人一年前赴美求学,正在那所大学读数学博士。久别后 重逢的喜悦激动着我,心早就到了那梦魂牵绕的小城。 和我的故乡北京比,爱荷华城可真是太小了。五万多人的大学城,连一 座高楼都没有,简直不像美国。可我却喜欢这地方。爱城,多好听的名字。湛蓝 的天空下,绿草如茵。爱荷华河从南边奔流而来,到这里轻轻带住脚步,把起伏 的山丘分为东西两岸。两岸山坡绿树丛中各色小屋隐约可见。宁静安详,远离都 市的喧嚣。女作家聂华苓是这里的教授。她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把许多作家 带到这小城。贾平凹,韩少功,北岛一-都曾在这世外桃源谈书论文,怡然自得。 田园风情,人心淳朴,小城是读书的好地方。学生的生活紧张忙碌。我 读计算机,妻子读数学,儿子上幼儿园。三个人每天在课堂、实验室、Day Care(日 托所)、图书馆和住所之间走马灯似地转。小城有一间华人教会。每到星期日, 当街支起一个大牌子:“爱城华人教会一一陈仰善牧师”。我对那里边的世界 并无兴趣。功课、实验、奖学金和学位已经够我忙的了。读书之余,除了带着儿 子到山坡下校美术馆Hancher前的空地上骑车,便是在停车场鼓捣旧车。修自 家的老爷车,也搭手帮助修朋友的。和几个乐于此道的同学结成好友。因为常常 把手弄得满是油污,便谑称自己是“黑手党”。 这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持续两年,故乡突如其来的那场暴风雨浇灭了我心 中的赤子之火。对过去曾相信过的理念彻底绝望,对未来一片茫然。我试图振作 起来,好好念书,先拿下学位再说。而妻子则开始带着孩子出入教会的门了。 奇怪,那次在商场,当两个香港同学拿着新约圣经要送给我时,不是她拉着我就 走,还嗔怪说“怎么被这种人缠住了”吗?如今却自己要去。不过也好,只要 她心里快乐平和。住我们楼上,我素来敬重的蓝大哥也是基督徒呢。儿子若能在 教会中学些道理,也强似在家闲玩。至于我自己就免了。哪里有神?奋斗到今天 还不全靠自己。每到星期日,我把妻子和儿子送到那块大牌子前,然后一头扎进 实验室。 不知不觉间,妻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素来急躁、好忧愁的她,变得 沉静而温和了许多。对公众的事也更热心了。这年还做了学生会主席,我却成了 不是主席的“主席先生”。鞍前马后地跟着忙。 一天,她小声却又兴奋地告诉我: “我信主啦!” 你一一信一一主一一了?这里面的含义,我一时不能完全体会。于是跟 着她去听牧师讲道。这牧师讲的逻辑不通嘛!回家的路上,我把一连串的问题撒 向妻子,她也答不上来。算了,还是去我的实验室吧。我更加努力读书,跨越一 个个考试,似乎离人生目标越来越近了。 那是九一年的秋天。万圣节刚过,天灰蒙蒙的。星期五早晨,我紧跑几 步赶上校车,见到住在三楼的山林华坐在靠门的长条座位上。“嗨,还好吗?” 我在他身边坐下。“挺好的。我的岳父来了。我们刚从伊州香槟大学回来。下 午系里有Seminar(研讨会)。”小山答道。小山是学校里的知名人物。博士资格当年彼得团契的老友,与华欣牧师和高青林师母重逢在芝加哥 我俩都笑了起来。爱人一年前赴美求学,正在那所大学读数学博士。久别后 重逢的喜悦激动着我,心早就到了那梦魂牵绕的小城。 和我的故乡北京比,爱荷华城可真是太小了。五万多人的大学城,连一 座高楼都没有,简直不像美国。可我却喜欢这地方。爱城,多好听的名字。湛蓝 的天空下,绿草如茵。爱荷华河从南边奔流而来,到这里轻轻带住脚步,把起伏 的山丘分为东西两岸。两岸山坡绿树丛中各色小屋隐约可见。宁静安详,远离都 市的喧嚣。 女作家聂华苓是这里的教授。她主持的国际写作计划,把许多作家 带到这小城。贾平凹,韩少功,北岛┅┅都曾在这世外桃源谈书论文,怡然自得。 田园风情,人心淳朴,小城是读书的好地方。学生的生活紧张忙碌。我 读计算机,妻子读数学,儿子上幼儿园。三个人每天在课堂、实验室、Day Care(日 托所)、图书馆和住所之间走马灯似地转。小城有一间华人教会。每到星期日, 当街支起一个大牌子:“爱城华人教会——陈仰善牧师”。我对那里边 的世界 并无兴趣。功课、实验、奖学金和学位已经够我忙的了。读书之余,除了带着儿 子到山坡下校美术馆 Hancher 前的空地上骑车,便是在停车场鼓捣旧车。修自 家的老爷车,也搭手帮助修朋友的。和几个乐于此道的同学结成好友。因为常常 把手弄得满是油污,便谑称自己是“ 黑手党”。 这无忧无虑的时光没持续两年,故乡突如其来的那场暴风雨浇灭了我心 中的赤子之火。对过去曾相信过的理念彻底绝望,对未来一片茫然。我试图振作 起来,好 好念书,先拿下学位再说。而妻子则开始带着孩子出入教会的门了。 奇怪,那次在商场,当两个香港同学拿着新约圣经要送给我时,不是她拉着我就 走,还嗔怪说“ 怎么被这种人缠住了”吗?如今却自己要去。不过也好,只要 她心里快乐平和。住我们楼上,我素来敬重的蓝大哥也是基督徒呢。儿子若能在 教会中学些道理,也强似在家闲玩。至于我自己就免了。哪里有神?奋斗到今天 还不全靠自己。每到星期日,我把妻子和儿子送到那块大牌子前,然后一头扎进 实验室。 不知不觉间,妻子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素来急躁、好忧愁的她,变得 沉静而温和了许多。对公众的事也更热心了。这年还做了学生会主席,我却成了 不是主席的“主席先生”。鞍前马后地跟着忙。 一天,她小声却又兴奋地告诉我: “我信主啦!” 你——信——主——了?这里面的含义,我一时不能完全体会。于是跟 着她去听牧师讲道。这牧师讲的逻辑不通嘛!回家的路上,我把一连串的问题撒 向妻子,她也答不上来。算了,还是去我的实验室吧。我更加努力读书,跨越一 个个考试,似乎离人生目标越来越近了。 那是九一年的秋天。万圣节刚过,天灰蒙蒙的。星期五早晨,我紧跑几 步赶上校车,见到住在三楼的山林华坐在靠门的长条座位上。“嗨,还好吗?” 我在他身 边坐下。“挺好的。我的岳父来了。我们刚从伊州香槟大学回来。下 午系里有 Seminar(研讨会)。”小山答道。小山是学校里的知名人物。博士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