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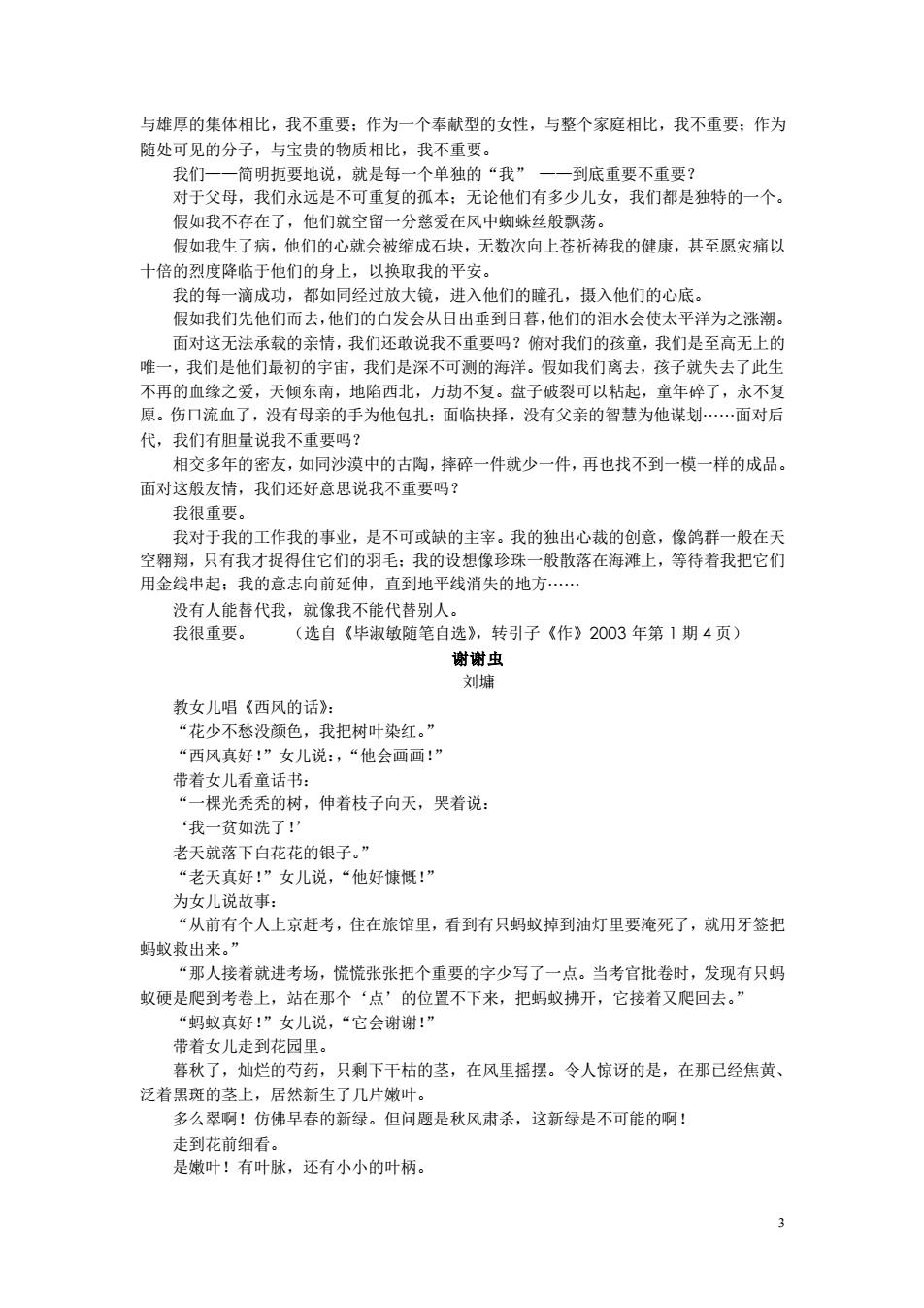
与雄厚的集体相比,我不重要:作为一个奉献型的女性,与整个家庭相比,我不重要:作为 随处可见的分子,与宝贵的物质相比,我不重要 我们 一荷明扼要地说,就是句 个单独的“我 到底重要不重要 对于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 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分慈爱在风中蜘蛛丝般飘荡。 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被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健康,甚至愿灾痛以 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的身上,以换取我的平安 我的每 ”都如 经过放大镜 进入他们的瞳孔,摄入他们的心底 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 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俯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无上的 唯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字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离去,孩子就失去了此生 不再的血缘之爱,天领东南,地路西北,万不复。盘子破裂可以粘起,童年碎了,永不复 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划 面对后 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 相交多年的密友,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捧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 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 我很重要。 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室,我的独出心栽的创意,像鸽群一般在天 空翱翔,只有我才指 般散落在海 上 ,等待着我把它们 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代替别人。 我很重要。 (选自《毕淑敏随笔自选》,转引子《作》2003年第1期4页) 谢谢虫 教女儿唱《西风的话》: “花少不愁没颜色,我把树叶染红。 “西风真好!”女儿说:,“他会画画!” 带着女儿看帝话书: “一棵光秃秃的树,伸着枝子向天,哭着说: “我一贫如洗了! 老天就落下白花花的银子。” “老天真好!”女儿说,“他好慷慨!” 为女儿说故事 “从前有个人上京赶考,住在旅馆里,看到有只蚂蚁掉到油灯里要淹死了,就用牙签把 蚂蚁救出来。 “那人接着就进考场,慌慌张张把个重要的字少写了一点。当考官批卷时,发现有只蚂 蚁硬是爬到考卷上,站在那个‘点'的位置不下来,把蚂蚁拂开,它接着又爬回去。” “蚂蚁真好!”女儿说,“它会谢谢!” 带若女儿走到花园甲」 暮秋了,灿烂的芍药,只剩下干枯的茎,在风里摇摆。令人惊讶的是,在那己经焦黄、 泛着黑斑的茎上,居然新生了几片嫩叶 多么翠啊!仿佛早春的新绿。但问题是秋风肃杀,这新绿是不可能的啊! 走到花前细看。 是嫩叶!有叶脉,还有小小的叶柄 33 与雄厚的集体相比,我不重要;作为一个奉献型的女性,与整个家庭相比,我不重要;作为 随处可见的分子,与宝贵的物质相比,我不重要。 我们——简明扼要地说,就是每一个单独的“我” ——到底重要不重要? 对于父母,我们永远是不可重复的孤本;无论他们有多少儿女,我们都是独特的一个。 假如我不存在了,他们就空留一分慈爱在风中蜘蛛丝般飘荡。 假如我生了病,他们的心就会被缩成石块,无数次向上苍祈祷我的健康,甚至愿灾痛以 十倍的烈度降临于他们的身上,以换取我的平安。 我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摄入他们的心底。 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 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俯对我们的孩童,我们是至高无上的 唯一,我们是他们最初的宇宙,我们是深不可测的海洋。假如我们离去,孩子就失去了此生 不再的血缘之爱,天倾东南,地陷西北,万劫不复。盘子破裂可以粘起,童年碎了,永不复 原。伤口流血了,没有母亲的手为他包扎;面临抉择,没有父亲的智慧为他谋划.面对后 代,我们有胆量说我不重要吗? 相交多年的密友,如同沙漠中的古陶,摔碎一件就少一件,再也找不到一模一样的成品。 面对这般友情,我们还好意思说我不重要吗? 我很重要。 我对于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是不可或缺的主宰。我的独出心裁的创意,像鸽群一般在天 空翱翔,只有我才捉得住它们的羽毛;我的设想像珍珠一般散落在海滩上,等待着我把它们 用金线串起;我的意志向前延伸,直到地平线消失的地方. 没有人能替代我,就像我不能代替别人。 我很重要。 (选自《毕淑敏随笔自选》,转引子《作》2003 年第 1 期 4 页) 谢谢虫 刘墉 教女儿唱《西风的话》: “花少不愁没颜色,我把树叶染红。” “西风真好!”女儿说:,“他会画画!” 带着女儿看童话书: “一棵光秃秃的树,伸着枝子向天,哭着说: ‘我一贫如洗了!’ 老天就落下白花花的银子。” “老天真好!”女儿说,“他好慷慨!” 为女儿说故事: “从前有个人上京赶考,住在旅馆里,看到有只蚂蚁掉到油灯里要淹死了,就用牙签把 蚂蚁救出来。” “那人接着就进考场,慌慌张张把个重要的字少写了一点。当考官批卷时,发现有只蚂 蚁硬是爬到考卷上,站在那个‘点’的位置不下来,把蚂蚁拂开,它接着又爬回去。” “蚂蚁真好!”女儿说,“它会谢谢!” 带着女儿走到花园里。 暮秋了,灿烂的芍药,只剩下干枯的茎,在风里摇摆。令人惊讶的是,在那已经焦黄、 泛着黑斑的茎上,居然新生了几片嫩叶。 多么翠啊!仿佛早春的新绿。但问题是秋风肃杀,这新绿是不可能的啊! 走到花前细看。 是嫩叶!有叶脉,还有小小的叶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