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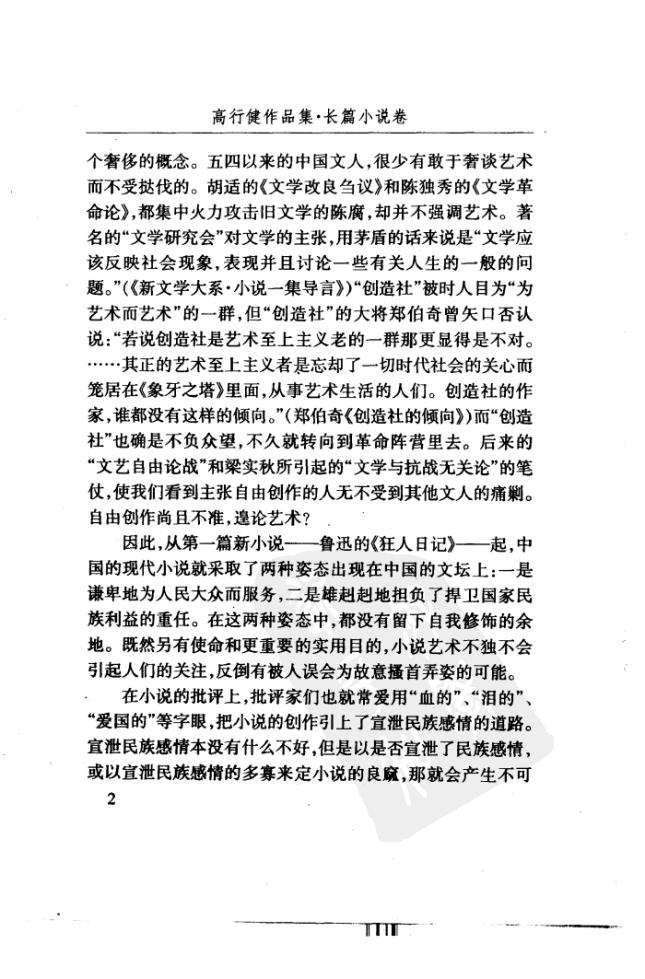
高行健作品集·长篇小说卷 个奢侈的概念。五四以来的中国文人,很少有敢于奢谈艺术 而不受挞伐的。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 命论》,都集中火力攻击旧文学的陈腐,却并不强调艺术。著 名的“文学研究会”对文学的主张,用茅盾的话来说是“文学应 该反映社会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的一般的问 题。”(《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创造社”被时人目为“为 艺术而艺术”的一群,但“创造社”的大将郑伯奇曾矢口否认 说:“若说创造社是艺术至上主义老的一群那更显得是不对。 …其正的艺术至上主义者是忘却了一切时代社会的关心而 笼居在《象牙之塔》里面,从事艺术生活的人们。创造社的作 家,谁都没有这样的倾向。”(郑伯奇《创造社的倾向》)而“创造 社”也确是不负众望,不久就转向到革命阵营里去。后来的 “文艺自由论战”和梁实秋所引起的“文学与抗战无关论”的笔 仗,使我们看到主张自由创作的人无不受到其他文人的痛剿。 自由创作尚且不准,逢论艺术? 因此,从第一篇新小说一鲁迅的《狂人日记》—起,中 国的现代小说就采取了两种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文坛上:一是 谦卑地为人民大众而服务,二是雄赳赳地担负了捍卫国家民 族利益的重任。在这两种姿态中,都没有留下自我修饰的余 地。既然另有使命和更重要的实用目的,小说艺术不独不会 引起人们的关注,反倒有被人误会为故意搔首弄姿的可能。 在小说的批评上,批评家们也就常爱用“血的”、“泪的”、 “爱国的”等字眼,把小说的创作引上了宣泄民族感情的道路。 宜泄民族感情本没有什么不好,但是以是否宜泄了民族感情, 或以宣泄民族感情的多寡来定小说的良魔,那就会产生不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