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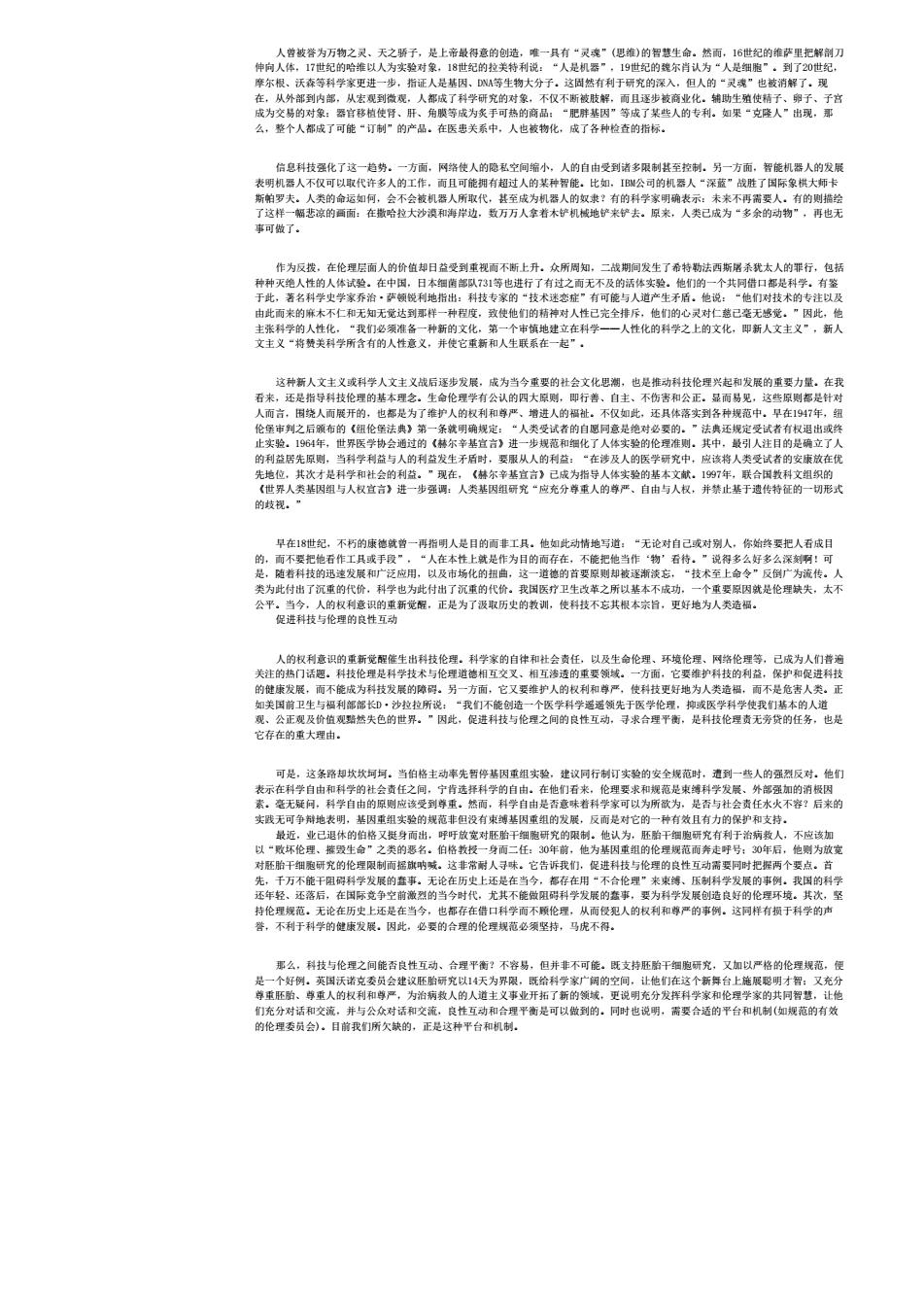
人曾被誉为万物之灵、天之骄子,是上帝最得意的创造,唯一具有“灵魂”(思维)的智慧生命。然而,16世纪的维萨里把解剖刀 伸向人体,17世纪的哈维以人为实验对象,18世纪的拉美特利说:“人是机器”,19世纪的魏尔肖认为“人是细胞”。到了20世纪, 摩尔根、沃森等科学家更进一步,指证人是基因、NA等生物大分子。这固然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但人的“灵魂”也被消解了。现 在,从外部到内部,从宏观到微观,人都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不断被肢解,而且逐步被商业化。辅助生殖使精子、卵子、子宫 成为交易的对象:器官移植使肾、肝、角膜等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肥胖基因”等成了某些人的专利。如果“克隆人”出现,那 么,整个人都成了可能“订制”的产品。在医患关系中,人也被物化,成了各种检查的指标。 信息科技强化了这一趋势。一方面,网络使人的隐私空间缩小,人的自由受到诸多限制甚至控制.另一方而,智能机器人的发展 表明机器人不仅可以取代许多人的工作,而且可能拥有超过人的某种智能。比如,IW公司的机器人“深蓝”战胜了国际象棋大师卡 斯帕罗夫。人类的命运如何,会不会被机器人所取代,甚至成为机器人的奴隶?有的科学家明确表示:未来不再需要人·有的则描绘 了这样一辐悲该的面面:在撒哈拉大沙漠和海岸边,数万万人拿着木铲机械地铲来铲去。原来,人类已成为“多余的动物”,再也无 事可做了。 作为反拨,在伦理层面人的价值却日益受到重视而不断上升。众所周知,二战期间发生了希特勒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包括 种种灭绝人性的人体试验。在中国,日本细菌部队731等也进行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活体实验。他们的一个共同借口都是科学。有鉴 于此,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萃颜悦利地指出:科技专家的“技术迷恋症”有可能与人道产生矛盾。他说:“他们对技术的专注以及 由此而来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达到那样一种程度,致使他们的精神对人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感觉。”因此,他 主张科学的人性化,“我们必须谁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一一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新人 文主义“将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 这种新人文主义或科学人文主义战后逐步发展,成为当今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也是推动科技伦理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 看来,还是指导科技伦理的基本理念。生命伦理学有公认的四大原则,即行善、自主、不伤害和公正。显而易见,这些原则都是针对 人而言,围绕人而展开的,也都是为了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增进人的福祉。不仅如此,还具体落实到各种规范中。早在1947年,纽 伦堡审判之后颁布的《纽伦堡法典》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法典还规定受试者有权退出或终 止实验。1964年,世界医学协会通过的《赫尔辛基宜言》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了人体实验的伦理准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确立了人 的利益居先原则,当科学利益与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要服从人的利益:“在涉及人的医学研究中,应该将人类受试者的安康放在优 先地位,其次才是科学和社会的利益。”现在,《赫尔辛基宜言》已成为指导人体实验的基本文献。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宜言》进一步强调:人类基因组研究“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与人权,并禁止基于遗传特征的一切形式 的歧视。” 早在18世纪,不朽的康德就曾一再指明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他如此动情地写道:“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你始终要把人看成目 的,而不要把他看作工具或手段”,“人在本性上就是作为目的而存在,不能把他当作“物'看待。”说得多么好多么深刻啊:可 是,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以及市场化的扭曲,这一道德的首要原则却被逐渐淡忘,“技术至上命令”反倒广为流传。人 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科学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国医疗卫生改革之所以基本不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伦理缺失,太不 公平。当今,人的权利意识的重新觉醒,正是为了汲取历史的教训,使科技不忘其根本宗旨,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促进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 人的权利意识的重新觉醒催生出科技伦理。科学家的自律和杜会责任,以及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网铬伦理等,已成为人们普遍 关注的热门话题。科技伦理是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重要领域。一方而,它要维护科技的利益,保护和促进科技 的健康发展,而不能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它又要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危害人类。正 如美国前卫生与福利部部长D·沙拉拉所说:“我们不能创造一个医学科学遥遥领先于医学伦理,抑或医学科学使我们基本的人道 观、公正观及价值观璐然失色的世界。”因此,促进科技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求合理平衡,是科技伦理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 它存在的重大理由。 可是,这条路却坎坎坷坷。当伯格主动率先暂停基因重组实验,建议同行制订实验的安全规范时,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 表示在科学自由和科学的社会责任之间,宁肯选择科学的自由。在他们看来,伦理要求和规范是束簿科学发展、外部强加的消极因 素。毫无疑问,科学自由的原则应该受到尊重。然而,科学自由是否意味者科学家可以为所欲为,是香与社会责任水火不容?后来的 实践无可争辩地表明,基因重组实验的规范非但没有束缚基因重组的发展,反而是对它的一种有效且有力的保护和支持。 最近,业已退休的伯格又挺身而出,呼吁放宽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他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有利于治病数人,不应该加 以“败坏伦理、摧毁生命”之类的恶名。伯格教投一身而二任:30年前,他为基因重组的伦理规范而弃走呼号:0年后,他则为放宽 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限制而摇旗呐喊。这非常耐人寻味。它告诉我们,促进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需要同时把握两个要点。首 先,千万不能干阻碍科学发展的蠢事。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都存在用“不合伦理”来束缚、压制科学发展的事例。我国的科学 还年轻、还落后,在国际竟争空前激烈的当今时代,尤其不能做阻碍科学发展的蠢事,要为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伦理环境。其次,坚 持伦理规范,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也都存在借口科学而不顾伦理,从而侵犯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事例。这同样有损于科学的声 誉,不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必要的合埋的伦理规范必须坚持,马虎不得。 那么,科技与伦理之间能否良性互动、合理平衡?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既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又加以严格的伦理规范,便 是一个好例。英国沃诺克委员会建议胚胎研究以14天为界限,既给科学家广闲的空间,让他们在这个新舞台上施展聪明才智:又充分 尊重胚胎、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为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事业开拓了新的领域,更说明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共同智慧,让他 们充分对话和交流,并与公众对话和交流,良性互动和合理平衡是可以做到的。同时也说明,需要合适的平台和机制(如规范的有效 的伦理委员会)。目前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这种平台和机制。人曾被誉为万物之灵、天之骄子,是上帝最得意的创造,唯一具有“灵魂”(思维)的智慧生命。然而,16世纪的维萨里把解剖刀 伸向人体,17世纪的哈维以人为实验对象,18世纪的拉美特利说:“人是机器”,19世纪的魏尔肖认为“人是细胞”。到了20世纪, 摩尔根、沃森等科学家更进一步,指证人是基因、DNA等生物大分子。这固然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但人的“灵魂”也被消解了。现 在,从外部到内部,从宏观到微观,人都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不断被肢解,而且逐步被商业化。辅助生殖使精子、卵子、子宫 成为交易的对象;器官移植使肾、肝、角膜等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肥胖基因”等成了某些人的专利。如果“克隆人”出现,那 么,整个人都成了可能“订制”的产品。在医患关系中,人也被物化,成了各种检查的指标。 信息科技强化了这一趋势。一方面,网络使人的隐私空间缩小,人的自由受到诸多限制甚至控制。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的发展 表明机器人不仅可以取代许多人的工作,而且可能拥有超过人的某种智能。比如,IBM公司的机器人“深蓝”战胜了国际象棋大师卡 斯帕罗夫。人类的命运如何,会不会被机器人所取代,甚至成为机器人的奴隶?有的科学家明确表示:未来不再需要人。有的则描绘 了这样一幅悲凉的画面:在撒哈拉大沙漠和海岸边,数万万人拿着木铲机械地铲来铲去。原来,人类已成为“多余的动物”,再也无 事可做了。 作为反拨,在伦理层面人的价值却日益受到重视而不断上升。众所周知,二战期间发生了希特勒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包括 种种灭绝人性的人体试验。在中国,日本细菌部队731等也进行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活体实验。他们的一个共同借口都是科学。有鉴 于此,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锐利地指出:科技专家的“技术迷恋症”有可能与人道产生矛盾。他说:“他们对技术的专注以及 由此而来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达到那样一种程度,致使他们的精神对人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感觉。”因此,他 主张科学的人性化,“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新人 文主义“将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 这种新人文主义或科学人文主义战后逐步发展,成为当今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也是推动科技伦理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 看来,还是指导科技伦理的基本理念。生命伦理学有公认的四大原则,即行善、自主、不伤害和公正。显而易见,这些原则都是针对 人而言,围绕人而展开的,也都是为了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增进人的福祉。不仅如此,还具体落实到各种规范中。早在1947年,纽 伦堡审判之后颁布的《纽伦堡法典》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法典还规定受试者有权退出或终 止实验。1964年,世界医学协会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了人体实验的伦理准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确立了人 的利益居先原则,当科学利益与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要服从人的利益:“在涉及人的医学研究中,应该将人类受试者的安康放在优 先地位,其次才是科学和社会的利益。”现在,《赫尔辛基宣言》已成为指导人体实验的基本文献。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进一步强调:人类基因组研究“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与人权,并禁止基于遗传特征的一切形式 的歧视。” 早在18世纪,不朽的康德就曾一再指明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他如此动情地写道:“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你始终要把人看成目 的,而不要把他看作工具或手段”,“人在本性上就是作为目的而存在,不能把他当作‘物’看待。”说得多么好多么深刻啊!可 是,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以及市场化的扭曲,这一道德的首要原则却被逐渐淡忘,“技术至上命令”反倒广为流传。人 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科学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国医疗卫生改革之所以基本不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伦理缺失,太不 公平。当今,人的权利意识的重新觉醒,正是为了汲取历史的教训,使科技不忘其根本宗旨,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促进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 人的权利意识的重新觉醒催生出科技伦理。科学家的自律和社会责任,以及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等,已成为人们普遍 关注的热门话题。科技伦理是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它要维护科技的利益,保护和促进科技 的健康发展,而不能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它又要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危害人类。正 如美国前卫生与福利部部长D·沙拉拉所说:“我们不能创造一个医学科学遥遥领先于医学伦理,抑或医学科学使我们基本的人道 观、公正观及价值观黯然失色的世界。”因此,促进科技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求合理平衡,是科技伦理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 它存在的重大理由。 可是,这条路却坎坎坷坷。当伯格主动率先暂停基因重组实验,建议同行制订实验的安全规范时,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 表示在科学自由和科学的社会责任之间,宁肯选择科学的自由。在他们看来,伦理要求和规范是束缚科学发展、外部强加的消极因 素。毫无疑问,科学自由的原则应该受到尊重。然而,科学自由是否意味着科学家可以为所欲为,是否与社会责任水火不容?后来的 实践无可争辩地表明,基因重组实验的规范非但没有束缚基因重组的发展,反而是对它的一种有效且有力的保护和支持。 最近,业已退休的伯格又挺身而出,呼吁放宽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他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有利于治病救人,不应该加 以“败坏伦理、摧毁生命”之类的恶名。伯格教授一身而二任:30年前,他为基因重组的伦理规范而奔走呼号;30年后,他则为放宽 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限制而摇旗呐喊。这非常耐人寻味。它告诉我们,促进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需要同时把握两个要点。首 先,千万不能干阻碍科学发展的蠢事。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都存在用“不合伦理”来束缚、压制科学发展的事例。我国的科学 还年轻、还落后,在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当今时代,尤其不能做阻碍科学发展的蠢事,要为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伦理环境。其次,坚 持伦理规范。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也都存在借口科学而不顾伦理,从而侵犯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事例。这同样有损于科学的声 誉,不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必要的合理的伦理规范必须坚持,马虎不得。 那么,科技与伦理之间能否良性互动、合理平衡?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既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又加以严格的伦理规范,便 是一个好例。英国沃诺克委员会建议胚胎研究以14天为界限,既给科学家广阔的空间,让他们在这个新舞台上施展聪明才智;又充分 尊重胚胎、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为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事业开拓了新的领域,更说明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共同智慧,让他 们充分对话和交流,并与公众对话和交流,良性互动和合理平衡是可以做到的。同时也说明,需要合适的平台和机制(如规范的有效 的伦理委员会)。目前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这种平台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