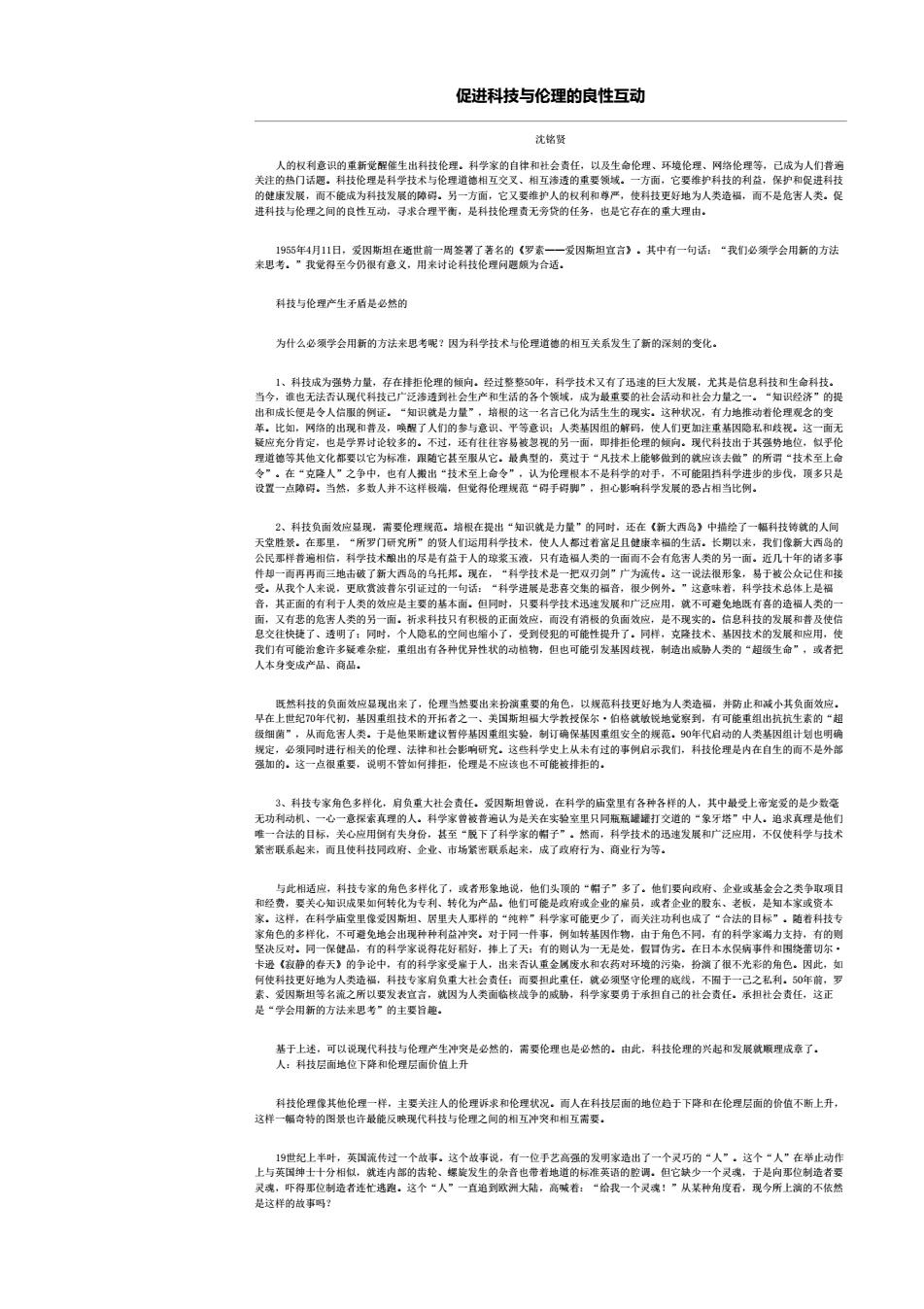
促进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 沈铭贤 人的权利意识的重新觉醒催生出科技伦理。科学家的自律和社会责任,以及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等,已成为人们普遍 关注的热门话愿。科技伦理是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交叉、相互漆透的重要领域。一方而,它要维护科技的利益,保护和促进科技 的健康发展,而不能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另一方而,它又要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福,面不是危害人类。促 进科技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求合理平衡,是科技伦理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它存在的重大理由。 1955年4月11日,爱因斯坦在逝世前一周签署了著名的《罗素一一爱因撕坦宜言》。其中有一句话:“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 来思考。”我觉得至今仍很有意义,用来讨论科技伦理问腿颜为合适。 科技与伦理产生矛盾是必然的 为什么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呢?因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新的深刻的变化。 1、科技成为强势力量,存在排拒伦理的倾向。经过整整50年,科学技术又有了迅速的巨大发展,尤其是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 当今,谁也无法否认现代科技已广泛渗透到杜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力量之一。“知识经济”的提 出和成长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这一名言已化为活生生的现实。这种状况,有力地推动着伦理观念的变 苹。比如,网络的出现和普及,唤醒了人们的参与意识、平等意识:人类基因组的解码,使人们更加注重基因隐私和歧视。这一面无 疑应充分肯定,也是学界讨论较多的。不过,还有往往容易被忽视的另一而,即排拒伦理的倾向。现代科技出于其强势地位,似乎伦 理道德等其他文化都要以它为标准,跟随它甚至服从它。最典型的,莫过于“凡技术上能够做到的就应该去做”的所谓“技术至上命 令”。在“克隆人”之争中,也有人搬出“技术至上命令”,认为伦理根本不是科学的对手,不可能阻挡科学进步的步伐。顶多只是 设置一点障碍。当然,多数人并不这样极端,但觉得伦理规范“碍手碍脚”,担心影响科学发展的恐占相当比例。 2、科技负面效应显现,需要伦理规范。培根在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同时,还在《新大西岛》中描绘了一幅科技铸就的人间 天堂胜景。在那里,“所罗门研究所”的贤人们运用科学技术,使人人都过者富足且健康幸福的生活。长期以来,我们像新大西岛的 公民那样普遍相信,科学技术酿出的尽是有益于人的琼浆玉液,只有造福人类的一面而不会有危害人类的另一面。近几十年的诸多事 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击破了新大西岛的乌托邦。现在,“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广为流传。这一说法很形象,易于被公众记住和接 受。从我个人来说。更欣赏波普尔引证过的一句话:“科学进展是悲喜交集的福音,很少例外。”这意味者,科学技术总体上是福 音,其正面的有利于人类的效应是主要的基本面。但同时,只要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就不可避免地既有喜的造福人类的 面,又有悲的危害人类的另一面。析求科技只有积极的正面效应,而没有消极的负面效应,是不现实的。信息科技的发展和普及使信 息交往快捷了、透明了:同时,个人隐私的空间也缩小了,受到侵犯的可能性提升了。同样,克隆技术、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 我们有可能治愈许多疑难杂症,重组出有各种优异性状的动植物,但也可能引发基因歧视,制造出威胁人类的“超级生命”,或者把 人本身变成产品、商品。 既然科技的负而效应显现出来了,伦理当然要出来扮演重要的角色,以规范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福,并防止和减小其负而效应,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基因重组技术的开拓者之一、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尔·伯格就敏锐地觉察到,有可能重组出抗抗生素的“超 级细菌”,从而危害人类。于是他果断建议暂停基因重组实验,制订确保基因重组安全的规范。90年代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明确 规定,必须同时进行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研究。这些科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例启示我们,科技伦理是内在自生的而不是外部 强加的。这一点很重要,说明不管如何排拒,伦理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排拒的。 3、科技专家角色多样化,肩负重大社会责任。爱因斯坦曾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最受上帝宠爱的是少数毫 无功利动机、一心一意探索真理的人。科学家曾被普遍认为是关在实验室里只同瓶瓶罐罐打交道的“象牙塔”中人·追求真理是他们 唯一合法的目标,关心应用倒有失身份,甚至“脱下了科学家的帽子”。然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使科学与技术 紧密联系起来,面且使科技同政府、企业、市场紫密联系起来,成了政府行为、商业行为等。 与此相适应,科技专家的角色多样化了,或者形象地说,他们头顶的“帽子”多了。他们要向政府、企业或基金会之类争取项目 和经费,要关心知识成果如何转化为专利、转化为产品。他们可能是政府或企业的扉员,或者企业的股东、老板,是知本家或资本 家。这样,在科学庙堂里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那样的“纯粹”科学家可能更少了,而关注功利也成了“合法的目标”。随着科技专 家角色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利益冲突。对于同一件事,例如转基因作物,由于角色不同,有的科学家竭力支持,有的则 坚决反对。同一保健品,有的科学家说得花好稻好,棒上了天:有的则认为一无是处,假冒伪劣。在日本水促病事件和围绕蕾切尔· 卡逊《寂静的春天》的争论中,有的科学家受缩于人,出来否认重金属废水和农药对环境的污染,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因此,如 何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技专家肩负重大社会责任:而要担此重任,就必须坚守伦理的底线,不阿于一己之私利。0年前,罗 素、爱因斯坦等名流之所以要发表宜言,就因为人类而临核战争的威胁,科学家要男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这正 是“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的主要旨趣。 基于上述,可以说现代科技与伦理产生冲突是必然的,需要伦理也是必然的。由此,科技伦理的兴起和发展就顺理成章了。 人:科技层而地位下降和伦理层而价值上升 科技伦理像其他伦理一样,主要关注人的伦理诉求和伦理状况。而人在科技层面的地位趋于下降和在伦理层面的价值不断上升, 这样一幅奇特的图景也许最能反映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需要。 19世纪上半叶,英国流传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位手艺高强的发明家造出了一个灵巧的“人”。这个“人”在举止动作 上与英国绅士十分相似,就连内部的齿轮、螺旋发生的杂音也带着地道的标准英语的腔调。但它缺少一个灵魂,于是向那位制造者要 灵魂,吓得那位制造者连忙逃跑。这个“人”一直追到欧洲大陆,高喊着:“给我一个灵魂!”从某种角度看,现今所上演的不依然 是这样的故事吗?
促进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 沈铭贤 人的权利意识的重新觉醒催生出科技伦理。科学家的自律和社会责任,以及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等,已成为人们普遍 关注的热门话题。科技伦理是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它要维护科技的利益,保护和促进科技 的健康发展,而不能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它又要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危害人类。促 进科技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求合理平衡,是科技伦理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它存在的重大理由。 1955年4月11日,爱因斯坦在逝世前一周签署了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其中有一句话:“我们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 来思考。”我觉得至今仍很有意义,用来讨论科技伦理问题颇为合适。 科技与伦理产生矛盾是必然的 为什么必须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呢?因为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新的深刻的变化。 1、科技成为强势力量,存在排拒伦理的倾向。经过整整50年,科学技术又有了迅速的巨大发展,尤其是信息科技和生命科技。 当今,谁也无法否认现代科技已广泛渗透到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力量之一。“知识经济”的提 出和成长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的这一名言已化为活生生的现实。这种状况,有力地推动着伦理观念的变 革。比如,网络的出现和普及,唤醒了人们的参与意识、平等意识;人类基因组的解码,使人们更加注重基因隐私和歧视。这一面无 疑应充分肯定,也是学界讨论较多的。不过,还有往往容易被忽视的另一面,即排拒伦理的倾向。现代科技出于其强势地位,似乎伦 理道德等其他文化都要以它为标准,跟随它甚至服从它。最典型的,莫过于“凡技术上能够做到的就应该去做”的所谓“技术至上命 令”。在“克隆人”之争中,也有人搬出“技术至上命令”,认为伦理根本不是科学的对手,不可能阻挡科学进步的步伐,顶多只是 设置一点障碍。当然,多数人并不这样极端,但觉得伦理规范“碍手碍脚”,担心影响科学发展的恐占相当比例。 2、科技负面效应显现,需要伦理规范。培根在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同时,还在《新大西岛》中描绘了一幅科技铸就的人间 天堂胜景。在那里,“所罗门研究所”的贤人们运用科学技术,使人人都过着富足且健康幸福的生活。长期以来,我们像新大西岛的 公民那样普遍相信,科学技术酿出的尽是有益于人的琼浆玉液,只有造福人类的一面而不会有危害人类的另一面。近几十年的诸多事 件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击破了新大西岛的乌托邦。现在,“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广为流传。这一说法很形象,易于被公众记住和接 受。从我个人来说,更欣赏波普尔引证过的一句话:“科学进展是悲喜交集的福音,很少例外。”这意味着,科学技术总体上是福 音,其正面的有利于人类的效应是主要的基本面。但同时,只要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就不可避免地既有喜的造福人类的一 面,又有悲的危害人类的另一面。祈求科技只有积极的正面效应,而没有消极的负面效应,是不现实的。信息科技的发展和普及使信 息交往快捷了、透明了;同时,个人隐私的空间也缩小了,受到侵犯的可能性提升了。同样,克隆技术、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 我们有可能治愈许多疑难杂症,重组出有各种优异性状的动植物,但也可能引发基因歧视,制造出威胁人类的“超级生命”,或者把 人本身变成产品、商品。 既然科技的负面效应显现出来了,伦理当然要出来扮演重要的角色,以规范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福,并防止和减小其负面效应。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基因重组技术的开拓者之一、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尔·伯格就敏锐地觉察到,有可能重组出抗抗生素的“超 级细菌”,从而危害人类。于是他果断建议暂停基因重组实验,制订确保基因重组安全的规范。90年代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也明确 规定,必须同时进行相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影响研究。这些科学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例启示我们,科技伦理是内在自生的而不是外部 强加的。这一点很重要,说明不管如何排拒,伦理是不应该也不可能被排拒的。 3、科技专家角色多样化,肩负重大社会责任。爱因斯坦曾说,在科学的庙堂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其中最受上帝宠爱的是少数毫 无功利动机、一心一意探索真理的人。科学家曾被普遍认为是关在实验室里只同瓶瓶罐罐打交道的“象牙塔”中人。追求真理是他们 唯一合法的目标,关心应用倒有失身份,甚至“脱下了科学家的帽子”。然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不仅使科学与技术 紧密联系起来,而且使科技同政府、企业、市场紧密联系起来,成了政府行为、商业行为等。 与此相适应,科技专家的角色多样化了,或者形象地说,他们头顶的“帽子”多了。他们要向政府、企业或基金会之类争取项目 和经费,要关心知识成果如何转化为专利、转化为产品。他们可能是政府或企业的雇员,或者企业的股东、老板,是知本家或资本 家。这样,在科学庙堂里像爱因斯坦、居里夫人那样的“纯粹”科学家可能更少了,而关注功利也成了“合法的目标”。随着科技专 家角色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利益冲突。对于同一件事,例如转基因作物,由于角色不同,有的科学家竭力支持,有的则 坚决反对。同一保健品,有的科学家说得花好稻好,捧上了天;有的则认为一无是处,假冒伪劣。在日本水俣病事件和围绕蕾切尔· 卡逊《寂静的春天》的争论中,有的科学家受雇于人,出来否认重金属废水和农药对环境的污染,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因此,如 何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福,科技专家肩负重大社会责任;而要担此重任,就必须坚守伦理的底线,不囿于一己之私利。50年前,罗 素、爱因斯坦等名流之所以要发表宣言,就因为人类面临核战争的威胁,科学家要勇于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这正 是“学会用新的方法来思考”的主要旨趣。 基于上述,可以说现代科技与伦理产生冲突是必然的,需要伦理也是必然的。由此,科技伦理的兴起和发展就顺理成章了。 人:科技层面地位下降和伦理层面价值上升 科技伦理像其他伦理一样,主要关注人的伦理诉求和伦理状况。而人在科技层面的地位趋于下降和在伦理层面的价值不断上升, 这样一幅奇特的图景也许最能反映现代科技与伦理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需要。 19世纪上半叶,英国流传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有一位手艺高强的发明家造出了一个灵巧的“人”。这个“人”在举止动作 上与英国绅士十分相似,就连内部的齿轮、螺旋发生的杂音也带着地道的标准英语的腔调。但它缺少一个灵魂,于是向那位制造者要 灵魂,吓得那位制造者连忙逃跑。这个“人”一直追到欧洲大陆,高喊着:“给我一个灵魂!”从某种角度看,现今所上演的不依然 是这样的故事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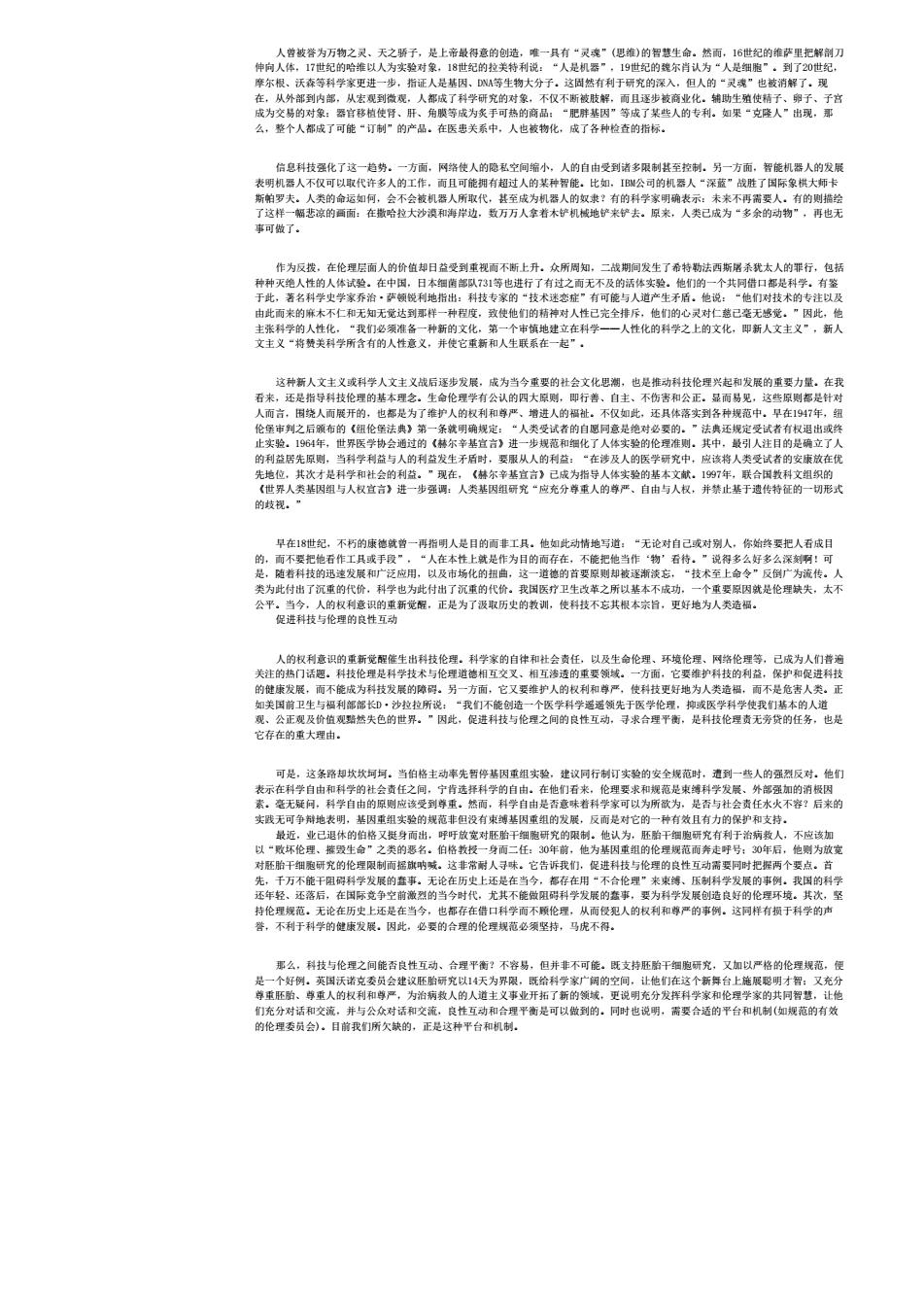
人曾被誉为万物之灵、天之骄子,是上帝最得意的创造,唯一具有“灵魂”(思维)的智慧生命。然而,16世纪的维萨里把解剖刀 伸向人体,17世纪的哈维以人为实验对象,18世纪的拉美特利说:“人是机器”,19世纪的魏尔肖认为“人是细胞”。到了20世纪, 摩尔根、沃森等科学家更进一步,指证人是基因、NA等生物大分子。这固然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但人的“灵魂”也被消解了。现 在,从外部到内部,从宏观到微观,人都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不断被肢解,而且逐步被商业化。辅助生殖使精子、卵子、子宫 成为交易的对象:器官移植使肾、肝、角膜等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肥胖基因”等成了某些人的专利。如果“克隆人”出现,那 么,整个人都成了可能“订制”的产品。在医患关系中,人也被物化,成了各种检查的指标。 信息科技强化了这一趋势。一方面,网络使人的隐私空间缩小,人的自由受到诸多限制甚至控制.另一方而,智能机器人的发展 表明机器人不仅可以取代许多人的工作,而且可能拥有超过人的某种智能。比如,IW公司的机器人“深蓝”战胜了国际象棋大师卡 斯帕罗夫。人类的命运如何,会不会被机器人所取代,甚至成为机器人的奴隶?有的科学家明确表示:未来不再需要人·有的则描绘 了这样一辐悲该的面面:在撒哈拉大沙漠和海岸边,数万万人拿着木铲机械地铲来铲去。原来,人类已成为“多余的动物”,再也无 事可做了。 作为反拨,在伦理层面人的价值却日益受到重视而不断上升。众所周知,二战期间发生了希特勒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包括 种种灭绝人性的人体试验。在中国,日本细菌部队731等也进行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活体实验。他们的一个共同借口都是科学。有鉴 于此,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萃颜悦利地指出:科技专家的“技术迷恋症”有可能与人道产生矛盾。他说:“他们对技术的专注以及 由此而来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达到那样一种程度,致使他们的精神对人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感觉。”因此,他 主张科学的人性化,“我们必须谁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一一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新人 文主义“将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 这种新人文主义或科学人文主义战后逐步发展,成为当今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也是推动科技伦理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 看来,还是指导科技伦理的基本理念。生命伦理学有公认的四大原则,即行善、自主、不伤害和公正。显而易见,这些原则都是针对 人而言,围绕人而展开的,也都是为了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增进人的福祉。不仅如此,还具体落实到各种规范中。早在1947年,纽 伦堡审判之后颁布的《纽伦堡法典》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法典还规定受试者有权退出或终 止实验。1964年,世界医学协会通过的《赫尔辛基宜言》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了人体实验的伦理准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确立了人 的利益居先原则,当科学利益与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要服从人的利益:“在涉及人的医学研究中,应该将人类受试者的安康放在优 先地位,其次才是科学和社会的利益。”现在,《赫尔辛基宜言》已成为指导人体实验的基本文献。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宜言》进一步强调:人类基因组研究“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与人权,并禁止基于遗传特征的一切形式 的歧视。” 早在18世纪,不朽的康德就曾一再指明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他如此动情地写道:“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你始终要把人看成目 的,而不要把他看作工具或手段”,“人在本性上就是作为目的而存在,不能把他当作“物'看待。”说得多么好多么深刻啊:可 是,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以及市场化的扭曲,这一道德的首要原则却被逐渐淡忘,“技术至上命令”反倒广为流传。人 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科学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国医疗卫生改革之所以基本不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伦理缺失,太不 公平。当今,人的权利意识的重新觉醒,正是为了汲取历史的教训,使科技不忘其根本宗旨,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促进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 人的权利意识的重新觉醒催生出科技伦理。科学家的自律和杜会责任,以及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网铬伦理等,已成为人们普遍 关注的热门话题。科技伦理是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重要领域。一方而,它要维护科技的利益,保护和促进科技 的健康发展,而不能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它又要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危害人类。正 如美国前卫生与福利部部长D·沙拉拉所说:“我们不能创造一个医学科学遥遥领先于医学伦理,抑或医学科学使我们基本的人道 观、公正观及价值观璐然失色的世界。”因此,促进科技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求合理平衡,是科技伦理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 它存在的重大理由。 可是,这条路却坎坎坷坷。当伯格主动率先暂停基因重组实验,建议同行制订实验的安全规范时,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 表示在科学自由和科学的社会责任之间,宁肯选择科学的自由。在他们看来,伦理要求和规范是束簿科学发展、外部强加的消极因 素。毫无疑问,科学自由的原则应该受到尊重。然而,科学自由是否意味者科学家可以为所欲为,是香与社会责任水火不容?后来的 实践无可争辩地表明,基因重组实验的规范非但没有束缚基因重组的发展,反而是对它的一种有效且有力的保护和支持。 最近,业已退休的伯格又挺身而出,呼吁放宽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他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有利于治病数人,不应该加 以“败坏伦理、摧毁生命”之类的恶名。伯格教投一身而二任:30年前,他为基因重组的伦理规范而弃走呼号:0年后,他则为放宽 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限制而摇旗呐喊。这非常耐人寻味。它告诉我们,促进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需要同时把握两个要点。首 先,千万不能干阻碍科学发展的蠢事。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都存在用“不合伦理”来束缚、压制科学发展的事例。我国的科学 还年轻、还落后,在国际竟争空前激烈的当今时代,尤其不能做阻碍科学发展的蠢事,要为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伦理环境。其次,坚 持伦理规范,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也都存在借口科学而不顾伦理,从而侵犯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事例。这同样有损于科学的声 誉,不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必要的合埋的伦理规范必须坚持,马虎不得。 那么,科技与伦理之间能否良性互动、合理平衡?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既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又加以严格的伦理规范,便 是一个好例。英国沃诺克委员会建议胚胎研究以14天为界限,既给科学家广闲的空间,让他们在这个新舞台上施展聪明才智:又充分 尊重胚胎、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为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事业开拓了新的领域,更说明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共同智慧,让他 们充分对话和交流,并与公众对话和交流,良性互动和合理平衡是可以做到的。同时也说明,需要合适的平台和机制(如规范的有效 的伦理委员会)。目前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这种平台和机制
人曾被誉为万物之灵、天之骄子,是上帝最得意的创造,唯一具有“灵魂”(思维)的智慧生命。然而,16世纪的维萨里把解剖刀 伸向人体,17世纪的哈维以人为实验对象,18世纪的拉美特利说:“人是机器”,19世纪的魏尔肖认为“人是细胞”。到了20世纪, 摩尔根、沃森等科学家更进一步,指证人是基因、DNA等生物大分子。这固然有利于研究的深入,但人的“灵魂”也被消解了。现 在,从外部到内部,从宏观到微观,人都成了科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不断被肢解,而且逐步被商业化。辅助生殖使精子、卵子、子宫 成为交易的对象;器官移植使肾、肝、角膜等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肥胖基因”等成了某些人的专利。如果“克隆人”出现,那 么,整个人都成了可能“订制”的产品。在医患关系中,人也被物化,成了各种检查的指标。 信息科技强化了这一趋势。一方面,网络使人的隐私空间缩小,人的自由受到诸多限制甚至控制。另一方面,智能机器人的发展 表明机器人不仅可以取代许多人的工作,而且可能拥有超过人的某种智能。比如,IBM公司的机器人“深蓝”战胜了国际象棋大师卡 斯帕罗夫。人类的命运如何,会不会被机器人所取代,甚至成为机器人的奴隶?有的科学家明确表示:未来不再需要人。有的则描绘 了这样一幅悲凉的画面:在撒哈拉大沙漠和海岸边,数万万人拿着木铲机械地铲来铲去。原来,人类已成为“多余的动物”,再也无 事可做了。 作为反拨,在伦理层面人的价值却日益受到重视而不断上升。众所周知,二战期间发生了希特勒法西斯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包括 种种灭绝人性的人体试验。在中国,日本细菌部队731等也进行了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活体实验。他们的一个共同借口都是科学。有鉴 于此,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锐利地指出:科技专家的“技术迷恋症”有可能与人道产生矛盾。他说:“他们对技术的专注以及 由此而来的麻木不仁和无知无觉达到那样一种程度,致使他们的精神对人性已完全排斥,他们的心灵对仁慈已毫无感觉。”因此,他 主张科学的人性化,“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新人 文主义“将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 这种新人文主义或科学人文主义战后逐步发展,成为当今重要的社会文化思潮,也是推动科技伦理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 看来,还是指导科技伦理的基本理念。生命伦理学有公认的四大原则,即行善、自主、不伤害和公正。显而易见,这些原则都是针对 人而言,围绕人而展开的,也都是为了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增进人的福祉。不仅如此,还具体落实到各种规范中。早在1947年,纽 伦堡审判之后颁布的《纽伦堡法典》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人类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法典还规定受试者有权退出或终 止实验。1964年,世界医学协会通过的《赫尔辛基宣言》进一步规范和细化了人体实验的伦理准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确立了人 的利益居先原则,当科学利益与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要服从人的利益:“在涉及人的医学研究中,应该将人类受试者的安康放在优 先地位,其次才是科学和社会的利益。”现在,《赫尔辛基宣言》已成为指导人体实验的基本文献。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人类基因组与人权宣言》进一步强调:人类基因组研究“应充分尊重人的尊严、自由与人权,并禁止基于遗传特征的一切形式 的歧视。” 早在18世纪,不朽的康德就曾一再指明人是目的而非工具。他如此动情地写道:“无论对自己或对别人,你始终要把人看成目 的,而不要把他看作工具或手段”,“人在本性上就是作为目的而存在,不能把他当作‘物’看待。”说得多么好多么深刻啊!可 是,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以及市场化的扭曲,这一道德的首要原则却被逐渐淡忘,“技术至上命令”反倒广为流传。人 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科学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国医疗卫生改革之所以基本不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伦理缺失,太不 公平。当今,人的权利意识的重新觉醒,正是为了汲取历史的教训,使科技不忘其根本宗旨,更好地为人类造福。 促进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 人的权利意识的重新觉醒催生出科技伦理。科学家的自律和社会责任,以及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网络伦理等,已成为人们普遍 关注的热门话题。科技伦理是科学技术与伦理道德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重要领域。一方面,它要维护科技的利益,保护和促进科技 的健康发展,而不能成为科技发展的障碍。另一方面,它又要维护人的权利和尊严,使科技更好地为人类造福,而不是危害人类。正 如美国前卫生与福利部部长D·沙拉拉所说:“我们不能创造一个医学科学遥遥领先于医学伦理,抑或医学科学使我们基本的人道 观、公正观及价值观黯然失色的世界。”因此,促进科技与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寻求合理平衡,是科技伦理责无旁贷的任务,也是 它存在的重大理由。 可是,这条路却坎坎坷坷。当伯格主动率先暂停基因重组实验,建议同行制订实验的安全规范时,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他们 表示在科学自由和科学的社会责任之间,宁肯选择科学的自由。在他们看来,伦理要求和规范是束缚科学发展、外部强加的消极因 素。毫无疑问,科学自由的原则应该受到尊重。然而,科学自由是否意味着科学家可以为所欲为,是否与社会责任水火不容?后来的 实践无可争辩地表明,基因重组实验的规范非但没有束缚基因重组的发展,反而是对它的一种有效且有力的保护和支持。 最近,业已退休的伯格又挺身而出,呼吁放宽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限制。他认为,胚胎干细胞研究有利于治病救人,不应该加 以“败坏伦理、摧毁生命”之类的恶名。伯格教授一身而二任:30年前,他为基因重组的伦理规范而奔走呼号;30年后,他则为放宽 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限制而摇旗呐喊。这非常耐人寻味。它告诉我们,促进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需要同时把握两个要点。首 先,千万不能干阻碍科学发展的蠢事。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都存在用“不合伦理”来束缚、压制科学发展的事例。我国的科学 还年轻、还落后,在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当今时代,尤其不能做阻碍科学发展的蠢事,要为科学发展创造良好的伦理环境。其次,坚 持伦理规范。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也都存在借口科学而不顾伦理,从而侵犯人的权利和尊严的事例。这同样有损于科学的声 誉,不利于科学的健康发展。因此,必要的合理的伦理规范必须坚持,马虎不得。 那么,科技与伦理之间能否良性互动、合理平衡?不容易,但并非不可能。既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又加以严格的伦理规范,便 是一个好例。英国沃诺克委员会建议胚胎研究以14天为界限,既给科学家广阔的空间,让他们在这个新舞台上施展聪明才智;又充分 尊重胚胎、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为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事业开拓了新的领域,更说明充分发挥科学家和伦理学家的共同智慧,让他 们充分对话和交流,并与公众对话和交流,良性互动和合理平衡是可以做到的。同时也说明,需要合适的平台和机制(如规范的有效 的伦理委员会)。目前我们所欠缺的,正是这种平台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