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善何以必要 杨国荣 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谈到正义时,曾涉及如下问愿:就其本身而言,正义是否有益于人?换言之,正义本身对人来说何以必 要?[1]在《理想国》中,正义首先与善恶等联系在一起,并相应地具有道德的意义·这样,上述问题如果转换为更普遍的形式,也可 以表述为:为什么要有道德?或者说,善何以必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布拉德雷从个体存在的角度,以更明确的方式,提出了类 似的问恩:为什么我应当是道德的?[2]不难注意到,从古希腊到近代,善何以必要构成了道德皙学沉思的主要问避之一· 从外在的方面看,《理想国》对正义何以必要的时论,似乎主要限于正义对人有益与否之类的问题,亦即所谓利益关系。然而, 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便可发现,在利益关系之后,还蕴含着更深层的问题。即正义与人自身存在的关系。当《理想国》就正义是否 有益于人展开对话时,它所追问的,同时也是道德对人的存在所具有的意义这一更普遍的问避。布拉德雷对此似乎具有更自觉的意 识,在提出”为什么我应当是道德"这一问避之后,布拉德雷便着重将人的自我实现(sef-realization)作为讨论对象,并把自我实现规 定为道德的主要目的。[3]自我实现无疑与人的存在有更切近的关系,这里已进一步从道德与人自身存在的关系上,思考与解决”善何 以必要"这一本源性的问愿。就其内在逻辑而言,”善何以必要”与存在(人的存在)何以可能"两重提问之间显然很难裁然加以分离: 二者的这种相关性,也决定了对前一问愿的思考,无法离开伦理学与本体论相统一的视城。 一道德与存在 道德既是人存在的方式,同时也为这种存在(人本身的存在)提供了某种担保。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马克思曾从人与 动物的比较中强调了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动物没有关系,惟有人才能在其存在过程中建立多方而的关系。(参见《德意志意识形 态》)为了具体地从存在何以可能的角度考察善或道德何以必要的问题,我们不妨从分析人自身存在的关系本性入手。 早在先秦,孔子已指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斯人之徒,也就是和我共在的他人或群 体,“与"则是一种关系。对孔子来说,与他人其在,并由此建立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人的一种基本存在境遇:孔子的仁道学说, 便奠立于对这种关系的确认之上。作为人难以摆脱的存在境遭,关系无疑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当代的一些皙学家便者重从形面上的层 面,对存在的关系之维作了多方而的考察。首先可以一提的是布伯(M.Bub)·在著名的《我与你》一书中,布伯区分了我一你 (I-0u)和我一它(-Ht)两种不同的关系。我一它是对象性或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象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 中,"它"仅仅为我所用而并不与我相互沟通。相反,我一你关系则具有相互性、直接性、开放性:“我”通过与你的关系而成为我” (I and Thou,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1958,pl1,p28)当我与他人的关系尚处于我-它的层而时,尽管关系的双方都是 具体的”人”,但实际上此时的关系者仍停留于对象世界或”它“的世界中,这一世界完全受因果律的支配:惟有在我一你的交往模式 中,人与人之间才建立起真实的关系。 与布伯相近,列维纳斯(E.Levinas)将我与他人(others)的关系视为存在的一个本质的方面.按列维纳斯的看法,他人对我米 说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存在,我总是面对面地与他人在一起,而我与他人的这种关系首先是一种责任关系:”人们通常把责任看作是对 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但我认为责任首先相对于他人而言。我把责任理解为对他人的责任。"T]他人的存在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命 令,当他人注视我时,我便被置于对他人的责任关系中:正是在对他人的责任中,自我的主体性得到了确证。广面言之,每一个体都 是一个”我”,并相应地有自身的他人或他者,从而,每一个人也都可以看作是关系中的存在。 当然,作为对人我关系的形而上解释,布伯所说的我一你关系和列维纳斯所谓我与他者的关系,似乎仍带有某种思辨和抽象的 特点。事实上,在布伯那里,我一你关系往往具有超时空的性质:一旦把你置于时空关系中,”你”便成了它”,而我一你关系也相应 地为对象世界所取代。[⑤]对我一你关系的这种超时空的规定,使关系的现实之维多少有所弱化。同时,布伯还提出了”终极的 你”(eternal Thou)的概念,并将终极的你"视为我一你关系的中心,[6]这种所谓终极的你",已开始引向宗教意义上的超验存在。 [刀同样,按列锥纳斯之见,在我与他者的责任关系背后,总是蕴含者无限者(the infinite):我对他人的责任,同时也确证了无限 者·[⑧]这种无限者,亦具有超验的性质。可以看到,仅仅从形而上的层面考察存在的关系之维,似乎难以全而地展示人的存在及存在 的关系特征,也无法由此对善何以必要作出其体的解释。 对人的存在及作为存在形态的关系的真实理解,在于回到历史本身。人首先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作为生命的存在,生命本身的生 产和再生产是人存在过程所而临的基本问避。正是在生命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形成了最初的人伦形式之一:以配偶、亲子等 为内容的社会关系。从这种最原始的、莫基于自然血缘之上的人伦中,逐渐衔生了宽泛意义上的家庭关系:[9]家庭关系的进一步展 开,则是家族及或近或疏的亲属网络(ishi即):与之相关的尚有邻里间的交往等等。邻里关系尽管并非以血缘为纽带,但却以家庭 为其中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邻里之间并非仅仅呈现为空间位置上的彼此并存,作为一种社会联系的形式,邻里关系乃是通过家庭 成员之间的交往而建立起来的,它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家庭关系的外在延伸:而邻里与家庭、家族、亲属等等相互交融,又构成了 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方而。在这里,广义的家庭关系在人的存在中无疑具有某种本源的意义:作为人的生命生产与再生产借以实现的 基本形式,它从本体论的层而将人规定为关系中的存在。 在皙学史上,儒家似乎已对上述关系有所意识。它对家庭人伦的强调,以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为孝悌的出发点,并进而将孝悌 理解为仁道这一普遍价值伦理原则的根据,等等,已涉及到家庭关系在人的存在过程中的独特地位:而如果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在 人的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看,儒家以家庭人伦为轴心展开其伦理体系,无疑也把握了历史过程的一个方面,并自有其历史的 深意
善何以必要 杨国荣 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谈到正义时,曾涉及如下问题:就其本身而言,正义是否有益于人?换言之,正义本身对人来说何以必 要?[1]在《理想国》中,正义首先与善恶等联系在一起,并相应地具有道德的意义。这样,上述问题如果转换为更普遍的形式,也可 以表述为:为什么要有道德?或者说,善何以必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布拉德雷从个体存在的角度,以更明确的方式,提出了类 似的问题:为什么我应当是道德的?[2]不难注意到,从古希腊到近代,善何以必要构成了道德哲学沉思的主要问题之一。 从外在的方面看,《理想国》对正义何以必要的讨论,似乎主要限于正义对人有益与否之类的问题,亦即所谓利益关系。然而, 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便可发现,在利益关系之后,还蕴含着更深层的问题,即正义与人自身存在的关系。当《理想国》就正义是否 有益于人展开对话时,它所追问的,同时也是道德对人的存在所具有的意义这一更普遍的问题。布拉德雷对此似乎具有更自觉的意 识,在提出“为什么我应当是道德”这一问题之后,布拉德雷便着重将人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作为讨论对象,并把自我实现规 定为道德的主要目的。[3]自我实现无疑与人的存在有更切近的关系,这里已进一步从道德与人自身存在的关系上,思考与解决“善何 以必要”这一本源性的问题。就其内在逻辑而言,“善何以必要”与“存在(人的存在)何以可能”两重提问之间显然很难截然加以分离; 二者的这种相关性,也决定了对前一问题的思考,无法离开伦理学与本体论相统一的视域。 一 道德与存在 道德既是人存在的方式,同时也为这种存在(人本身的存在)提供了某种担保。人本质上是一种关系中的存在,马克思曾从人与 动物的比较中强调了这一点。在马克思看来,动物没有关系,惟有人才能在其存在过程中建立多方面的关系。(参见《德意志意识形 态》)为了具体地从存在何以可能的角度考察善或道德何以必要的问题,我们不妨从分析人自身存在的关系本性入手。 早在先秦,孔子已指出:“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论语·微子》)斯人之徒,也就是和我共在的他人或群 体,“与”则是一种关系。对孔子来说,与他人共在,并由此建立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是人的一种基本存在境遇;孔子的仁道学说, 便奠立于对这种关系的确认之上。作为人难以摆脱的存在境遇,关系无疑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当代的一些哲学家便着重从形而上的层 面,对存在的关系之维作了多方面的考察。首先可以一提的是布伯(M. Buber)。在著名的《我与你》一书中,布伯区分了我-你 (I-Thou)和我-它(I-It)两种不同的关系。我-它是对象性或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对象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 中,“它”仅仅为我所用而并不与我相互沟通。相反,我-你关系则具有相互性、直接性、开放性;“我”通过与你的关系而成为“我”。 (I and Thou, Charles Scribner’s Sons, New York, 1958, p11, p28)当我与他人的关系尚处于我-它的层面时,尽管关系的双方都是 具体的“人”,但实际上此时的关系者仍停留于对象世界或“它”的世界中,这一世界完全受因果律的支配;惟有在我-你的交往模式 中,人与人之间才建立起真实的关系。 与布伯相近,列维纳斯(E. Levinas)将我与他人(others)的关系视为存在的一个本质的方面。按列维纳斯的看法,他人对我来 说是一种无法回避的存在,我总是面对面地与他人在一起,而我与他人的这种关系首先是一种责任关系:“人们通常把责任看作是对 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但我认为责任首先相对于他人而言。”“我把责任理解为对他人的责任。”[4]他人的存在对我而言就是一种命 令,当他人注视我时,我便被置于对他人的责任关系中;正是在对他人的责任中,自我的主体性得到了确证。广而言之,每一个体都 是一个“我”,并相应地有自身的他人或他者,从而,每一个人也都可以看作是关系中的存在。 当然,作为对人我关系的形而上解释,布伯所说的我-你关系和列维纳斯所谓我与他者的关系,似乎仍带有某种思辨和抽象的 特点。事实上,在布伯那里,我-你关系往往具有超时空的性质:一旦把你置于时空关系中,“你”便成了“它”,而我-你关系也相应 地为对象世界所取代。[5]对我-你关系的这种超时空的规定,使关系的现实之维多少有所弱化。同时,布伯还提出了“终极的 你”(eternal Thou)的概念,并将“终极的你”视为我-你关系的中心,[6]这种所谓“终极的你”,已开始引向宗教意义上的超验存在。 [7]同样,按列维纳斯之见,在我与他者的责任关系背后,总是蕴含着无限者(the infinite);我对他人的责任,同时也确证了无限 者。[8]这种无限者,亦具有超验的性质。可以看到,仅仅从形而上的层面考察存在的关系之维,似乎难以全面地展示人的存在及存在 的关系特征,也无法由此对善何以必要作出具体的解释。 对人的存在及作为存在形态的关系的真实理解,在于回到历史本身。人首先是一种生命的存在,作为生命的存在,生命本身的生 产和再生产是人存在过程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正是在生命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形成了最初的人伦形式之一:以配偶、亲子等 为内容的社会关系。从这种最原始的、奠基于自然血缘之上的人伦中,逐渐衍生了宽泛意义上的家庭关系;[9]家庭关系的进一步展 开,则是家族及或近或疏的亲属网络(kinship);与之相关的尚有邻里间的交往等等。邻里关系尽管并非以血缘为纽带,但却以家庭 为其中介:从社会学的角度看,邻里之间并非仅仅呈现为空间位置上的彼此并存,作为一种社会联系的形式,邻里关系乃是通过家庭 成员之间的交往而建立起来的,它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家庭关系的外在延伸;而邻里与家庭、家族、亲属等等相互交融,又构成了 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里,广义的家庭关系在人的存在中无疑具有某种本源的意义:作为人的生命生产与再生产借以实现的 基本形式,它从本体论的层面将人规定为关系中的存在。 在哲学史上,儒家似乎已对上述关系有所意识。它对家庭人伦的强调,以亲子、长幼等家庭关系为孝悌的出发点,并进而将孝悌 理解为仁道这一普遍价值伦理原则的根据,等等,已涉及到家庭关系在人的存在过程中的独特地位;而如果从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在 人的存在过程中所具有的本源意义看,儒家以家庭人伦为轴心展开其伦理体系,无疑也把握了历史过程的一个方面,并自有其历史的 深意

当然,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并没有穷尽人的存在过程的全部内容。与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相辅相成的,是物质资料(包括生活资 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从早期的农耕经济到近代以来的大工业乃至现代的所带信息产业,广义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件随者 人存在的整个历史过程。如前所述,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还往往交错者血缘等生物性规定及自然因素,尽管当这种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以家庭等形式展开时,它已经开始纳入社会的历史过程,而且,随着这一历史过程的展开,它也将越来越带上社会的印记:但作为人 存在的根据,它总是与自然过程难以完全割断联系。相对于此,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显然更多地表现出社会性的特点,这种生产 固然离不开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但它同时又构成了人的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的历史前提:正是这种前提,使人的生命生产区别于动 物的繁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看作是人存在的社会本体。 作为人存在的社会本体,物质资料的生产或广义的劳动过程以分工为其内在的规定。从前现代的自然经济到工业化以后的大生 产,劳动分工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生产过程,并成为生产过程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尽管劳动分工在形式上有简单、复杂等等差别, 但从社会学上看却存在着共同的特征,即它蕴含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某种分化:换言之,劳动分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生产过程内部的不 同环节、工序等等的区分,而且更在于社会成员在存在方式(包括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等等)上的分别。从男耕女织之类的性别分 工,到体力与脑力之间等更具社会意义的劳动分工,社会成员在存在方式上呈现不断分化的趋向。同时,分工又使杜会成员之间形成 了不同形式的联系。首先是一定劳动组织中劳动者之间相互协作这样较为直接的联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劳动的分工为前提,又逐 渐衍生出不同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劳动成果之间的交换关系,往往交错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异,它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不 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在劳动、交换、利益等等的种种分化互动中,已开始蕴含尔后社会结构中的诸种经济、政治、社会的关联。 可以看到,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及物资的生产与再生产,一开始便在终极的、本源的层面上,将人规定为一种关系中的存在。如 果说,作为生命生产与再生产基本形式的家庭关系构成了生活世界中多重社会关联的的出发点,那么,物资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借以 展开的劳动分工,则孕有了更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联系。渗入于人的存在过程各个方而的杜会关系,作为人无法摆脱的存在境 遇,同时又制约者存在过程本身:惟有当奠基于两重生产的诸种关系获得较为适当的定位时,人的存在才是可能的。由此自然发生了 如下问圈:如何赋予本体论意义上的社会关系以合理的形式?这里的合理,当然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首先相对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形 态而言,而以上问恩的解决,也始终以人自身的历史实践为本源,其中既涉及社会(类)的层面的杜会生活秩序,也关联者个体的存 在方式。正是在这里,道德显示了其存在的历史理由。如后文将要详论的,作为人的社会性的一种表征,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与个体 整合所以可能的必要担保。从家庭成员到生活世界中交往各方,从生产组织中的不同工作者到杜会管理系统中的各个角色,如果社会 成员之间未能在仁道、正义等基本伦理原则之下合理地处理和定位彼此的关系,并由此形成某种道德秩序,那么,生命与物资资料的 两重再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上广义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便难以正常展开。 从另一方面看,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和物资资料的生产再生产在将人规定为关系中的存在的同时,也相应地导致了存在本身的分 化。当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衍生出亲子、兄弟等等社会关系时,它同时也将人定位在某种存在状态中:同样,物资资科的生产与 再生产在形成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的同时,也使人成为分工系统中彼此相异的特定一员。随着两重生产的展开,社会关系也愈来愈呈现 多样化的特点,作为关系中的存在,人也往往相应地被定格在这种逐渐分化的关系项中,成为承担某种固定功能的角色。不难看到, 存在的这种分化,同时亦意味者存在的分裂,它在逻辑与历史两重维度上都使人的存在蕴含了导向片面化的可能。当黑格尔、费尔巴 霍、马克思从不同的层而分析异化现象时,他们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的存在的片而化趋向。以分裂、片面化为其规定,存在 显然很难达到真实的的形态。在这里,走向真实的存在与扬弃存在的片面性、回归存在的具体形态构成了同一过程的二个方面。 回归具体的存在,当然并不意味着回到存在的出发点。历史地看,当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作为他者"而与自然相对时,本然意 义上的同一便走向了终结。人自身的存在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的相对同一走向分化的过程。在生命生产与再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 与再生产还处于较为早期的阶段(如生命生产与再生产上的群婚制、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中的采集和渔猎时期)时,劳动分工尚处 于十分简单的形态,此时的社会分化也相应地显得较为有限。就生活世界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尚未出现,就生产领域及其他社会 空间而言,劳动协作、产品交换、利益关系等等也未远未充分展开:事实上,甚至不妨说,此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与非生 活世界之分:日用常行与生产活动等等往往融合为一体。从这种早期的存在形态,到随着两重生产发展面形成多重杜会关系,这一历 史衍化也可以看作是人的存在由原始的相对同一,逐渐走向社会分化的过程。后者在实现历史进步的同时,又蕴含了存在的分裂与片 面化的可能:不断克服分化所蕴含的片面化趋向,是人的存在过程无法回避的问愿。质言之,从原始的同一走向分化、又在既分之后 不断重建统一,构成了人的存在的历史内涵:这种统一,不同于作为出发点的原始的、抽象的同一,而是基于社会分化之后所达到的 具体存在形态:在这里,重建存在的统一与回归具体的存在形态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此处也许有必要对具体与整体作一区分·整体(to妇ty)本质上带有超验或超越的特点,以整体为指向,往往很难避免对个体与 特殊的消解。布伯曾将个人所处的关系区分为三重:他与世界和事物的关系:他与他人(包括个体与众人)的关系:他与绝对 (4 bsolute)或上帝的关系。[1O]人与世界及事物的关系,也就是他所说的我一它(I-t)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则是所谓我一你 (I-0u)关系,如前所述,在布伯看米,较之我一它关系,我一你关系是一种更为完善的主体间关系:然而,后者固然高于前者, 但相对于我与绝对者或上帝的关系,它本身似乎只具有中介的意义,对布伯来说,终极层而的关系总是指向造物主(Creator)或上 帝。(bd.p103)布伯指出我一它关系的彼此对峙性、排斥性,显然已有见于这种关系所蕴含的存在分裂:他要求由我一它关系走 向我一你关系,也就是要求由人我之间的排斥性,达到人我之间的相互性,这里已表现出试图重建存在统一的意向。但是,以面向绝 对者或上帝为终极的目标,却意味者将存在的统一理解为回归抽象的大全或超验的存在,而不是回归具体的存在。与布伯相近,列维 纳斯也把我与他人(others)的关系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他之强调我"对他人的责任意识,也包含着扬弃人我之间的分离性、扩展存 在境域的意向。不过,在通过强化责任而扬弃存在的分离、扩展存在境域的同时,列维钠斯又进而把这种存在境域推向无限者(h Infinite),尽管列维纳斯一再要求将整体(totality)与无限者区分开来,然而,这种超越于一切个体的无限者,本身显然难以视为具 体的、现实的存在,在此基础上达到的存在的统一,只能给人以思辨的满足。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将理性一目的行动与交往行动区分开来,前者指向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后者则涉及主体间的关系。这种 看法与布伯区分我一它关系与我一你关系无疑有相通之处。当然,较之布伯对以上两重关系的形而上的规定,哈贝马斯对主体间关系
当然,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并没有穷尽人的存在过程的全部内容。与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相辅相成的,是物质资料(包括生活资 料)的生产与再生产。从早期的农耕经济到近代以来的大工业乃至现代的所谓信息产业,广义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伴随着 人存在的整个历史过程。如前所述,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还往往交错着血缘等生物性规定及自然因素,尽管当这种生产与再生产过程 以家庭等形式展开时,它已经开始纳入社会的历史过程,而且,随着这一历史过程的展开,它也将越来越带上社会的印记;但作为人 存在的根据,它总是与自然过程难以完全割断联系。相对于此,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显然更多地表现出社会性的特点,这种生产 固然离不开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但它同时又构成了人的生命生产与再生产的的历史前提:正是这种前提,使人的生命生产区别于动 物的繁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看作是人存在的社会本体。 作为人存在的社会本体,物质资料的生产或广义的劳动过程以分工为其内在的规定。从前现代的自然经济到工业化以后的大生 产,劳动分工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生产过程,并成为生产过程所以可能的必要条件。尽管劳动分工在形式上有简单、复杂等等差别, 但从社会学上看却存在着共同的特征,即它蕴含着社会成员之间的某种分化;换言之,劳动分工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生产过程内部的不 同环节、工序等等的区分,而且更在于社会成员在存在方式(包括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等等)上的分别。从男耕女织之类的性别分 工,到体力与脑力之间等更具社会意义的劳动分工,社会成员在存在方式上呈现不断分化的趋向。同时,分工又使社会成员之间形成 了不同形式的联系。首先是一定劳动组织中劳动者之间相互协作这样较为直接的联系,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劳动的分工为前提,又逐 渐衍生出不同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而劳动成果之间的交换关系,往往交错着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差异,它的进一步发展,则是不 同利益集团的形成。在劳动、交换、利益等等的种种分化互动中,已开始蕴含尔后社会结构中的诸种经济、政治、社会的关联。 可以看到,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及物资的生产与再生产,一开始便在终极的、本源的层面上,将人规定为一种关系中的存在。如 果说,作为生命生产与再生产基本形式的家庭关系构成了生活世界中多重社会关联的的出发点,那么,物资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借以 展开的劳动分工,则孕育了更广泛的经济、政治、社会联系。渗入于人的存在过程各个方面的社会关系,作为人无法摆脱的存在境 遇,同时又制约着存在过程本身:惟有当奠基于两重生产的诸种关系获得较为适当的定位时,人的存在才是可能的。由此自然发生了 如下问题:如何赋予本体论意义上的社会关系以合理的形式?这里的合理,当然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首先相对于一定的社会历史形 态而言,而以上问题的解决,也始终以人自身的历史实践为本源,其中既涉及社会(类)的层面的社会生活秩序,也关联着个体的存 在方式。正是在这里,道德显示了其存在的历史理由。如后文将要详论的,作为人的社会性的一种表征,道德构成了社会秩序与个体 整合所以可能的必要担保。从家庭成员到生活世界中交往各方,从生产组织中的不同工作者到社会管理系统中的各个角色,如果社会 成员之间未能在仁道、正义等基本伦理原则之下合理地处理和定位彼此的关系,并由此形成某种道德秩序,那么,生命与物资资料的 两重再生产以及在此基础上广义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便难以正常展开。 从另一方面看,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和物资资料的生产再生产在将人规定为关系中的存在的同时,也相应地导致了存在本身的分 化。当生命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衍生出亲子、兄弟等等社会关系时,它同时也将人定位在某种存在状态中;同样,物资资料的生产与 再生产在形成劳动者之间的联系的同时,也使人成为分工系统中彼此相异的特定一员。随着两重生产的展开,社会关系也愈来愈呈现 多样化的特点,作为关系中的存在,人也往往相应地被定格在这种逐渐分化的关系项中,成为承担某种固定功能的角色。不难看到, 存在的这种分化,同时亦意味着存在的分裂,它在逻辑与历史两重维度上都使人的存在蕴含了导向片面化的可能。当黑格尔、费尔巴 霍、马克思从不同的层面分析异化现象时,他们同时也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人的存在的片面化趋向。以分裂、片面化为其规定,存在 显然很难达到真实的的形态。在这里,走向真实的存在与扬弃存在的片面性、回归存在的具体形态构成了同一过程的二个方面。 回归具体的存在,当然并不意味着回到存在的出发点。历史地看,当人从自然中分化出来、作为“他者”而与自然相对时,本然意 义上的同一便走向了终结。人自身的存在同样经历了一个从原始的相对同一走向分化的过程。在生命生产与再生产和物质资料的生产 与再生产还处于较为早期的阶段(如生命生产与再生产上的群婚制、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中的采集和渔猎时期)时,劳动分工尚处 于十分简单的形态,此时的社会分化也相应地显得较为有限。就生活世界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尚未出现,就生产领域及其他社会 空间而言,劳动协作、产品交换、利益关系等等也未远未充分展开;事实上,甚至不妨说,此时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生活世界与非生 活世界之分:日用常行与生产活动等等往往融合为一体。从这种早期的存在形态,到随着两重生产发展而形成多重社会关系,这一历 史衍化也可以看作是人的存在由原始的相对同一,逐渐走向社会分化的过程,后者在实现历史进步的同时,又蕴含了存在的分裂与片 面化的可能;不断克服分化所蕴含的片面化趋向,是人的存在过程无法回避的问题。质言之,从原始的同一走向分化、又在既分之后 不断重建统一,构成了人的存在的历史内涵;这种统一,不同于作为出发点的原始的、抽象的同一,而是基于社会分化之后所达到的 具体存在形态;在这里,重建存在的统一与回归具体的存在形态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此处也许有必要对具体与整体作一区分。整体(totality)本质上带有超验或超越的特点,以整体为指向,往往很难避免对个体与 特殊的消解。布伯曾将个人所处的关系区分为三重:他与世界和事物的关系;他与他人(包括个体与众人)的关系;他与绝对 (Absolute)或上帝的关系。[10]人与世界及事物的关系,也就是他所说的我-它(I-It)关系;人与他人的关系,则是所谓我-你 (I-Thou)关系,如前所述,在布伯看来,较之我-它关系,我-你关系是一种更为完善的主体间关系;然而,后者固然高于前者, 但相对于我与绝对者或上帝的关系,它本身似乎只具有中介的意义,对布伯来说,终极层面的关系总是指向造物主(Creator)或上 帝。(ibid. p103)布伯指出我-它关系的彼此对峙性、排斥性,显然已有见于这种关系所蕴含的存在分裂;他要求由我-它关系走 向我-你关系,也就是要求由人我之间的排斥性,达到人我之间的相互性,这里已表现出试图重建存在统一的意向。但是,以面向绝 对者或上帝为终极的目标,却意味着将存在的统一理解为回归抽象的大全或超验的存在,而不是回归具体的存在。与布伯相近,列维 纳斯也把我与他人(others)的关系提到了重要的地位,他之强调“我”对他人的责任意识,也包含着扬弃人我之间的分离性、扩展存 在境域的意向。不过,在通过强化责任而扬弃存在的分离、扩展存在境域的同时,列维纳斯又进而把这种存在境域推向无限者(the Infinite),尽管列维纳斯一再要求将整体(totality)与无限者区分开来,然而,这种超越于一切个体的无限者,本身显然难以视为具 体的、现实的存在,在此基础上达到的存在的统一,只能给人以思辨的满足。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将理性-目的行动与交往行动区分开来,前者指向主体与对象的关系,后者则涉及主体间的关系。这种 看法与布伯区分我-它关系与我-你关系无疑有相通之处。当然,较之布伯对以上两重关系的形而上的规定,哈贝马斯对主体间关系

的理解似平具有更”形而下"的社会、历史内容。以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为轴心,哈贝马斯对如何重建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作了深入的探 讨,其中既包含文化的再生产,也涉及社会的整合、个体的社会化等等。作为生活世界理性化重建的前提,合理的主体间交往关系显 然也关联着回归存在的统一这一向度,事实上,当哈贝马斯将社会的整合、个体的社会化等规定为生活世界的内容时,已多少蕴含了 这一点。不过,在以主体间关系整合生活世界的同时,哈贝马斯似乎多少表现出强化普遍、一致、整体等趋向,在其伦理学理论中,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尽管哈贝马斯背定了每一主体参加时论、发表意见的权利(这种设定本身也是一种理想化的前提),但同 时又强调伦理的讨论以达到一致(consensus)为目标,这种目标显然假定了某种超越个体的普遍观念的存在,而在所谓”一致"中, 共同体或整体中的普避决定多少消解了主体的意见和自主选择。 作为扬弃存在的分裂、达到真实的存在的形式,回归具体不同于回归抽象的整体。在抽象的形态下,整体带有超越和超验的特 点:超验趋向于和经验世界的分离,超越则意味着凌驾于个体之上。同时,在一致、普遍等等要求下,抽象的整体往往略去了多样、 特殊而导向单一化,这种抽象、单一的形态,很难视为真实的存在。相对于抽象的整体,具体的存在达到了个体性与普遍性、多样性 与一致性的统一,并相应地包含了存在的全部丰富性。总之,重建存在的统一,回归具体的存在,不应当以牺牲存在的多样性、丰富 性为代价。 向具体存在的回归,当然并非一蹴而就,它在本质上展开为一个历史过程,并涉及多重因素,面道德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而, 如前所述,道德生活或伦理生活首先是一种本体论的事实,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往往有者不同的历史内容,但在社会的演进过 程中,伦理生活或道德生活总是构成了存在本身的一重规定。杜威曾强调,道德与生活不可分离,生活之中本身就包含者道德的内 容。[11]维特根斯坦也曾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只有首先教人伦理地生活,才能进而对他讲伦理的学说。[12]换言之,伦理 和道德原则的意义,惟有在生活过程中才能真正把握。 然而,这只是道德的一个方面。道德的特点在于,作为存在的一重规定,它同时又参与了存在本身的实现和完善。当布伯、列维 纳斯、哈贝马斯等从我一你、我与他者、主体间等角度探讨重建存在的统一时,他们同时也在道德的层面上涉及了如何完善存在的问 题。在生活实践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共同的伦理理想、价值原则、行为规范、评价准则等等,道德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将社会成员凝聚 起来的内在力量:为角色、地位、利益等等所分化的牡会成员,常常是在共同的道德理想与原则影响与制约下,才以一种不同于紧 张、排斥、对峙等等的方式,走到一起,共同生活。这里,道德的作用不仅仅表现为使人在自然层而的生物规定及社会层面的经济、 政治等等规定之外,另外获得伦理的规定,它的更深刻的本体论意义在于:从一个方面为分化的存在走向统一提供根据和担保。就个 体而言,”伦理地"生活使人既超越了食色等片面的天性(自然性或生物性),也扬弃了特定社会角色所赋予的单向度性,而在这一过 程中,道德同时也为个体走向具体存在提供了某种前提。 可以看到,善何以必要并不仅仅是一个狭义的伦理学问题,惟有从人的存在这一本体论的角度入手,才能理解这一问圈的真正内 涵并给予理论上的阐释,作为人存在的方式及生活实践过程中的本体论规定,道德同时也为存在所以可能及回归具体、真实的存在提 供了担保,正是在这里,道德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根据。 二道德意识与社会整合 从社会的层面看,存在的具体性往往体现于杜会的整合过程。社会的整合涉及多重雏度。首先是社会认同,包括广义的文化认 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团体(gOup)或组织认同,以及个体自身的角色认同等等,认同意味着接受某种社会的文化形态、生活 方式、杜会组织系统,承认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并归属于其中。 与社会认同相联系的是社会的凝聚(solidarity),在缺乏社会认同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往往趋向于从参与走向隐退,以远离杜会 生活为理想的追求:道家对礼法社会的拒斥,便表明了这一点。对社会离心趋向的克服,以承认某种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并获得相应 地社会归属感为前提之一。杜会凝聚的另一种形式,是对社会冲突的控制。社会的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差异等等,往往容易引发 不同形式的社会冲突,避免社会成员间的这种冲突或避免这种冲突的激化,离不开共同接受的社会规范系统:通过肯定公共或普遍的 社会价值以及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规定,等等,社会的规范系统同时也对可能的社会冲突作了某种限定。 控制冲突当然还带有消极的意义,从积极的方面看,社会凝聚更多地表现为杜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以及在不问的社会 实践领域中彼此协作。在这里,社会的认同和社会凝聚既是避免社会在刷烈的振荡中解体的条件,也是广义的社会生活生产与再生产 所以可能的前提。 如前所述,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同时关联者社会体制及杜会秩序的合法性问题,杜会实践过程中的相互协作,首先指向社会成员 之间的关系,相对于此,合法性则更多地以涉及社会成员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合法性本身当然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它往往有不同的历史内容,然而,惟有在社会体制及秩序的合法性获得确认时,这种社会系统及社会的秩序才可能获得其成员 的支持,并由此取得稳定的形态, 不同意义上的社会整合,既从类的层面或公共的空间展示了存在具体性的相关内容,又为走向这种具体存在提供了社会前提。如 果进一步考察社会整合本身所以可能的条件,则道德便成为不能不加以考察的一个方面。首先应当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意识或 道德观念。道德意识或道德观念作为历史的产物,无疑具有相对性、历史性的一而,但历史本身并不是如新康德主义所认定的那样, 仅仅由特殊的、个别的现象所构成:它总是同时漆入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联系。与历史过程的这一向度相应。道德意识及道德观念往往 也包含着普遍的内容。从共时性之维看,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体中,通常存在着对该共同体的成员具有普遍制钓作用的道德意识和道 德观念:就历时性之维而言,某些道德的意识和道德观念往往在不同的或较长的历史时期产生影响和作用,而不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 阶段。 具有普遍内容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通过教育、评价、奥论等等的提组、引导,逐渐成为一定时期社会成员的心理定势 (disposition),后者也就是杜尔凯姆所谓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它从杜会心理等层面,为社会的整合提供了某种支 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亲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等曾被视为基本的社会伦理、政治关系,与之相应的则是”父子有亲,君臣
的理解似乎具有更“形而下”的社会、历史内容。以主体间的交往关系为轴心,哈贝马斯对如何重建生活世界的理性化作了深入的探 讨,其中既包含文化的再生产,也涉及社会的整合、个体的社会化等等。作为生活世界理性化重建的前提,合理的主体间交往关系显 然也关联着回归存在的统一这一向度,事实上,当哈贝马斯将社会的整合、个体的社会化等规定为生活世界的内容时,已多少蕴含了 这一点。不过,在以主体间关系整合生活世界的同时,哈贝马斯似乎多少表现出强化普遍、一致、整体等趋向,在其伦理学理论中,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尽管哈贝马斯肯定了每一主体参加讨论、发表意见的权利(这种设定本身也是一种理想化的前提),但同 时又强调伦理的讨论以达到一致(consensus)为目标,这种目标显然假定了某种超越个体的普遍观念的存在,而在所谓“一致”中, 共同体或整体中的普遍决定多少消解了主体的意见和自主选择。 作为扬弃存在的分裂、达到真实的存在的形式,回归具体不同于回归抽象的整体。在抽象的形态下,整体带有超越和超验的特 点;超验趋向于和经验世界的分离,超越则意味着凌驾于个体之上。同时,在一致、普遍等等要求下,抽象的整体往往略去了多样、 特殊而导向单一化,这种抽象、单一的形态,很难视为真实的存在。相对于抽象的整体,具体的存在达到了个体性与普遍性、多样性 与一致性的统一,并相应地包含了存在的全部丰富性。总之,重建存在的统一,回归具体的存在,不应当以牺牲存在的多样性、丰富 性为代价。 向具体存在的回归,当然并非一蹴而就,它在本质上展开为一个历史过程,并涉及多重因素,而道德则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 如前所述,道德生活或伦理生活首先是一种本体论的事实,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往往有着不同的历史内容,但在社会的演进过 程中,伦理生活或道德生活总是构成了存在本身的一重规定。杜威曾强调,道德与生活不可分离,生活之中本身就包含着道德的内 容。[11]维特根斯坦也曾表述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只有首先教人伦理地生活,才能进而对他讲伦理的学说。[12]换言之,伦理 和道德原则的意义,惟有在生活过程中才能真正把握。 然而,这只是道德的一个方面。道德的特点在于,作为存在的一重规定,它同时又参与了存在本身的实现和完善。当布伯、列维 纳斯、哈贝马斯等从我-你、我与他者、主体间等角度探讨重建存在的统一时,他们同时也在道德的层面上涉及了如何完善存在的问 题。在生活实践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共同的伦理理想、价值原则、行为规范、评价准则等等,道德从一个侧面提供了将社会成员凝聚 起来的内在力量:为角色、地位、利益等等所分化的社会成员,常常是在共同的道德理想与原则影响与制约下,才以一种不同于紧 张、排斥、对峙等等的方式,走到一起,共同生活。这里,道德的作用不仅仅表现为使人在自然层面的生物规定及社会层面的经济、 政治等等规定之外,另外获得伦理的规定,它的更深刻的本体论意义在于:从一个方面为分化的存在走向统一提供根据和担保。就个 体而言,“伦理地”生活使人既超越了食色等片面的天性(自然性或生物性),也扬弃了特定社会角色所赋予的单向度性,而在这一过 程中,道德同时也为个体走向具体存在提供了某种前提。 可以看到,善何以必要并不仅仅是一个狭义的伦理学问题,惟有从人的存在这一本体论的角度入手,才能理解这一问题的真正内 涵并给予理论上的阐释。作为人存在的方式及生活实践过程中的本体论规定,道德同时也为存在所以可能及回归具体、真实的存在提 供了担保,正是在这里,道德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根据。 二 道德意识与社会整合 从社会的层面看,存在的具体性往往体现于社会的整合过程。社会的整合涉及多重维度。首先是社会认同,包括广义的文化认 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团体(group)或组织认同,以及个体自身的角色认同等等,认同意味着接受某种社会的文化形态、生活 方式、社会组织系统,承认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并归属于其中。 与社会认同相联系的是社会的凝聚(solidarity),在缺乏社会认同的情况下,社会成员往往趋向于从参与走向隐退,以远离社会 生活为理想的追求;道家对礼法社会的拒斥,便表明了这一点。对社会离心趋向的克服,以承认某种社会文化价值系统、并获得相应 地社会归属感为前提之一。社会凝聚的另一种形式,是对社会冲突的控制。社会的分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利益差异等等,往往容易引发 不同形式的社会冲突,避免社会成员间的这种冲突或避免这种冲突的激化,离不开共同接受的社会规范系统:通过肯定公共或普遍的 社会价值以及对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规定,等等,社会的规范系统同时也对可能的社会冲突作了某种限定。 控制冲突当然还带有消极的意义,从积极的方面看,社会凝聚更多地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以及在不同的社会 实践领域中彼此协作。在这里,社会的认同和社会凝聚既是避免社会在剧烈的振荡中解体的条件,也是广义的社会生活生产与再生产 所以可能的前提。 如前所述,社会认同和社会凝聚同时关联着社会体制及社会秩序的合法性问题,社会实践过程中的相互协作,首先指向社会成员 之间的关系,相对于此,合法性则更多地以涉及社会成员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合法性本身当然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在不同的历史 时期,它往往有不同的历史内容,然而,惟有在社会体制及秩序的合法性获得确认时,这种社会系统及社会的秩序才可能获得其成员 的支持,并由此取得稳定的形态。 不同意义上的社会整合,既从类的层面或公共的空间展示了存在具体性的相关内容,又为走向这种具体存在提供了社会前提。如 果进一步考察社会整合本身所以可能的条件,则道德便成为不能不加以考察的一个方面。首先应当关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意识或 道德观念。道德意识或道德观念作为历史的产物,无疑具有相对性、历史性的一面,但历史本身并不是如新康德主义所认定的那样, 仅仅由特殊的、个别的现象所构成:它总是同时渗入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联系。与历史过程的这一向度相应,道德意识及道德观念往往 也包含着普遍的内容。从共时性之维看,一定历史时期的共同体中,通常存在着对该共同体的成员具有普遍制约作用的道德意识和道 德观念;就历时性之维而言,某些道德的意识和道德观念往往在不同的或较长的历史时期产生影响和作用,而不限于某一特定的历史 阶段。 具有普遍内容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通过教育、评价、舆论等等的提倡、引导,逐渐成为一定时期社会成员的心理定势 (disposition),后者也就是杜尔凯姆所谓集体良知(collective conscience),它从社会心理等层面,为社会的整合提供了某种支 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亲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等曾被视为基本的社会伦理、政治关系,与之相应的则是“父子有亲,君臣

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膝文公上》)等主流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明显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印记,其 历史局限是毋庙讳言的。不过,它们同时又总是被涵盖在仁道等普遍的原则之下,而在社会结构奠基于宗法关系的历史时期,这些主 流的道德意识和信念对实现社会认同、维系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又无疑提供了某种观念的担保。 相对于中国传统道德对仁道以及仁道的特定历史形态的关注,西方的伦理传统往往更多地强调公正或正义。西塞罗(CcO)在 《论义务》中,已把公正列为四种基本的道德意识之一,并认为这种道德意识的功能在于”将社会组合在一起"(holds society together)[13],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观念,公正在社会冲突的抑制、杜会秩序的建立等方而。无疑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西塞罗 的以上看法,多少也折射了这种历史现象。公正观念与社会整合之间的联系。当然并不仅仅限于西塞罗所处的罗马时代,在近代社 会,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联系。班哈毕伯(S.Benhabib)已指出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的的个体需要为自己建立社会秩序的合法基 础,当它们面临这一任务时,公正就成为道德理论的中心。T14]简言之,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换过程中,合法社会秩序的建 立同样离不开公正等道德规念. 如前文所论及的,社会的整合关联着社会认同,从个体的锥度看,社会认同除了对现有秩序合法性的确认、对共同体价值的肯定 等等之外,还涉及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理想、人生信念等等:个体对社会的接受和参与程度,往往受到这种观念的制钓。当个人处于所 谓存在的孤独状态时,他常常倾向于从社会回到自我的封闭世界:对社会的这种隔绝,并不仅仅是由于交往的障碍等等而导致的与他 人的分离,在更深的层而上,它亦与道德资源的缺乏相联系,这种资源包括积极的人生信念、对生命意义的正而理解、对存在价值的 背定态度,等等。对没有道德理想并以否定的态度对待人生过程的人来说,消沉、绝望、无意义感等等往往成为其难以排造的情感体 验,而对他人的冷漠以及对社会的疏远乃至挂拒,则是由此导致的逻辑归宿。 从一般的社会交往这一层面看,对他人利益的的肯定、关心等等,是社会成员能够和谐相处、社会共同体能够维系的前提之一: 面这种与自我中心相对的行为趋向,在道德上又与利他的意识相联系。杜尔凯姆曾指出:”利他主义并不是如斯宾塞所理解的那样, 注定将成为社会生活某种悦人的装饰物,相反,它水远将是社会的基础。我们怎么能真的离开利他主义?如果人们不被此承诺并相互 作出牺牲,不以某种强而持久的纽带相互维系,他们就无法生活在一起。”T15]这里所说的利他主义,并不一定取得抽象的理论、原 则、规范等形式,而往往是以日常意识的形式存在,这种意识本身源于历史过程,如苟子所说,人只能在”群”(被此结成一定的生活 联系)的条件才能生存,对利益的相互肯定,无疑折射了这一历史事实:但它在形成以后,又构成了社会存在的观念条件。正是在后 一意义上,杜尔凯姆认为:”每一社会都是道德的社会。"T16) 道德的意识、观念、定势等等,并不仅仅以精神的形态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生活实践的不断重复,道德的意识往往进一步转 换为制度化的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1刀以社会生活中常常通到的借贷现象而言,在信用关系得到普遍确认的杜会条件下,向人 借贷便蕴含着如期归还的承诺。此处的向人借贷,首先是一个事实,但它又不同于自然条件下的事实,因为其中已渗入了”应当如期 归还"这样一种义务的观念,而义务则涉及道德的领域。在这里,道德上的义务观念,已融合于社会交往中的制度化事实。广而言 之,在社会结构中,当个人承担了某种社会角色时,他同时也就承诺了履行该角色所规定的义务:承担角色是一种事实,但这一事实 同样蕴含了义务观念。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便可以看作是对他那个时代特定的角色与义务关系的 种概括。在此,义务的观念已渗入伦理政治的事实。 伦理观念向事实的渗入或制度化,从一个方而展示了道德与存在的联系:在制度化的事实中,道德已具体化为存在的实际内容, 同时,通过融合于制度事实,道德观念和道德意识也获得了制钓杜会整合的一种现实机制。首先可以从行为秩序或行为的优先序列作 一分析。个体在社会系统中往往承担多重角色、涉及多重关系,与不同角色相联系的行为,往往难以在同一时间中相互兼容。为了避 免由此可能导致的冲突,便需要在义务及行为之间建立一定的秩序。帕森斯在谈到医生的义务时,曾涉及了这一问题。在职业这一层 面,医生承担着医治、照料病人的责任,但作为家庭的成员,他又对其他的家庭成员负有义务。然而,在数治一位危重病人与陪伴家 人这两者之间,前者无疑处于更优先的地位,正是这种优先性,使医生不会因为前去医院而放弃陪伴家人,与家人发生冲突。[18]在 义务与行为的这种秩序之后,不难看到道德观念的制钧:数治病人的优先性,同时亦体现了人道观念的优先:这里同样可以看到道德 意识向社会系统的渗入。而一般的道德意识和观念通过制度化,也进一步成为参与社会整合、避免社会神突的现实力量, 在制度化事实的形式下,道德意识更多地以自觉的形式融入了社会系统。除了这种自觉的制度形式之外,道德意识和道德现念往 往取得习惯的形式,并以此影响社会生活。相对于自觉形态的理论、原则、规范、制度,习惯与人的日用常行有更切近的联系,它常 常以合乎自然的方式制钓者社会成员的行为。作为社会化的第二自然,习惯无疑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总是同时凝结了历史地形成 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理学家所带洒扫应对”,便属于日常习惯性活动的领域,而在这种行为中,己渗入了履行基本道德义务(如 尊重师长等)的内容。从道德实践的层面看,习惯也可以看作是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在思维定势、行为方式等方面所形成的自然趋 向。就其与杜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习惯本身又构成了以自然的方式组织日常生活的重要方而:它使日常的社会生活无需法规、原则的 人为钓束和引导,也能够保持有序状态。正是通过凝结和融合于日常习惯,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为杜会整合的实 现及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延续提供了担保。[19] 道德意识内含者价值的确认,事实上,道德意义上的”善”、”恶”,与好”、”坏"等广义的价值规定便存在者历史的联系。[20]作为 存在及其关系的肯定和确证,价值观念和原则构成了道德意识更为核心的内容。在其现实形态上,道德意识与价值观念往往相互交 错,很难截然加以分离。以儒家的仁道而言,它既是一种道德规念(要求将人祝为目的面加以尊重),同时又是一种价值原则(肯定 每一个人都有其内在的存在价值)。与道德意识与价值观念的这种交错相应,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往往也和价值观念的制钓联系在 一起。共同的价值原则,往往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不同成员相互交往的基础,而社会的共识以及由此达到的行为协调,也同样离不 开对意义、价值的共同承诺。帕森新曾谈及基础科学研究的合法性以及对科学研究的社会支持问愿。基础科学由于缺乏当下可见的效 用,其存在的合法性(这种研究是香必要),及是香应给予支持,等等,往往成为间愿。这里已涉及到价值上认同:确认基础科学的 价值,并使这种确认成为社会共同体中的共识,这是基础科学得以存在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21]这一事实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价值 观念对实现文化认同和社会共识(包括共同体内立场和行为之协调)的深刻影响
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等主流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明显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印记,其 历史局限是毋庸讳言的。不过,它们同时又总是被涵盖在仁道等普遍的原则之下,而在社会结构奠基于宗法关系的历史时期,这些主 流的道德意识和信念对实现社会认同、维系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又无疑提供了某种观念的担保。 相对于中国传统道德对仁道以及仁道的特定历史形态的关注,西方的伦理传统往往更多地强调公正或正义。西塞罗(Cicero)在 《论义务》中,已把公正列为四种基本的道德意识之一,并认为这种道德意识的功能在于“将社会组合在一起”(holds society together)[13],作为一种普遍的道德观念,公正在社会冲突的抑制、社会秩序的建立等方面,无疑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西塞罗 的以上看法,多少也折射了这种历史现象。公正观念与社会整合之间的联系,当然并不仅仅限于西塞罗所处的罗马时代,在近代社 会,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种联系。班哈毕伯(S. Benhabib)已指出了这一点:“资产阶级的的个体需要为自己建立社会秩序的合法基 础,当它们面临这一任务时,公正就成为道德理论的中心。”[14]简言之,在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换过程中,合法社会秩序的建 立同样离不开公正等道德观念。 如前文所论及的,社会的整合关联着社会认同,从个体的维度看,社会认同除了对现有秩序合法性的确认、对共同体价值的肯定 等等之外,还涉及一般意义上的道德理想、人生信念等等;个体对社会的接受和参与程度,往往受到这种观念的制约。当个人处于所 谓存在的孤独状态时,他常常倾向于从社会回到自我的封闭世界;对社会的这种隔绝,并不仅仅是由于交往的障碍等等而导致的与他 人的分离,在更深的层面上,它亦与道德资源的缺乏相联系,这种资源包括积极的人生信念、对生命意义的正面理解、对存在价值的 肯定态度,等等。对没有道德理想并以否定的态度对待人生过程的人来说,消沉、绝望、无意义感等等往往成为其难以排遣的情感体 验,而对他人的冷漠以及对社会的疏远乃至排拒,则是由此导致的逻辑归宿。 从一般的社会交往这一层面看,对他人利益的的肯定、关心等等,是社会成员能够和谐相处、社会共同体能够维系的前提之一; 而这种与自我中心相对的行为趋向,在道德上又与利他的意识相联系。杜尔凯姆曾指出:“利他主义并不是如斯宾塞所理解的那样, 注定将成为社会生活某种悦人的装饰物,相反,它永远将是社会的基础。我们怎么能真的离开利他主义?如果人们不彼此承诺并相互 作出牺牲,不以某种强而持久的纽带相互维系,他们就无法生活在一起。”[15]这里所说的利他主义,并不一定取得抽象的理论、原 则、规范等形式,而往往是以日常意识的形式存在,这种意识本身源于历史过程,如荀子所说,人只能在“群”(彼此结成一定的生活 联系)的条件才能生存,对利益的相互肯定,无疑折射了这一历史事实;但它在形成以后,又构成了社会存在的观念条件。正是在后 一意义上,杜尔凯姆认为:“每一社会都是道德的社会。”[16] 道德的意识、观念、定势等等,并不仅仅以精神的形态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生活实践的不断重复,道德的意识往往进一步转 换为制度化的事实(institutional facts)。[17]以社会生活中常常遇到的借贷现象而言,在信用关系得到普遍确认的社会条件下,向人 借贷便蕴含着如期归还的承诺。此处的向人借贷,首先是一个事实,但它又不同于自然条件下的事实,因为其中已渗入了“应当如期 归还”这样一种义务的观念,而义务则涉及道德的领域。在这里,道德上的义务观念,已融合于社会交往中的制度化事实。广而言 之,在社会结构中,当个人承担了某种社会角色时,他同时也就承诺了履行该角色所规定的义务;承担角色是一种事实,但这一事实 同样蕴含了义务观念。孔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便可以看作是对他那个时代特定的角色与义务关系的 一种概括。在此,义务的观念已渗入伦理政治的事实。 伦理观念向事实的渗入或制度化,从一个方面展示了道德与存在的联系:在制度化的事实中,道德已具体化为存在的实际内容。 同时,通过融合于制度事实,道德观念和道德意识也获得了制约社会整合的一种现实机制。首先可以从行为秩序或行为的优先序列作 一分析。个体在社会系统中往往承担多重角色、涉及多重关系,与不同角色相联系的行为,往往难以在同一时间中相互兼容。为了避 免由此可能导致的冲突,便需要在义务及行为之间建立一定的秩序。帕森斯在谈到医生的义务时,曾涉及了这一问题。在职业这一层 面,医生承担着医治、照料病人的责任,但作为家庭的成员,他又对其他的家庭成员负有义务。然而,在救治一位危重病人与陪伴家 人这两者之间,前者无疑处于更优先的地位,正是这种优先性,使医生不会因为前去医院而放弃陪伴家人,与家人发生冲突。[18]在 义务与行为的这种秩序之后,不难看到道德观念的制约:救治病人的优先性,同时亦体现了人道观念的优先;这里同样可以看到道德 意识向社会系统的渗入。而一般的道德意识和观念通过制度化,也进一步成为参与社会整合、避免社会冲突的现实力量。 在制度化事实的形式下,道德意识更多地以自觉的形式融入了社会系统。除了这种自觉的制度形式之外,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往 往取得习惯的形式,并以此影响社会生活。相对于自觉形态的理论、原则、规范、制度,习惯与人的日用常行有更切近的联系,它常 常以合乎自然的方式制约着社会成员的行为。作为社会化的第二自然,习惯无疑有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总是同时凝结了历史地形成 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理学家所谓“洒扫应对”,便属于日常习惯性活动的领域,而在这种行为中,已渗入了履行基本道德义务(如 尊重师长等)的内容。从道德实践的层面看,习惯也可以看作是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在思维定势、行为方式等方面所形成的自然趋 向。就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而言,习惯本身又构成了以自然的方式组织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它使日常的社会生活无需法规、原则的 人为约束和引导,也能够保持有序状态。正是通过凝结和融合于日常习惯,道德意识和道德观念从日常生活的层面,为社会整合的实 现及社会秩序的建构和延续提供了担保。[19] 道德意识内含着价值的确认,事实上,道德意义上的“善”、“恶”,与“好”、“坏”等广义的价值规定便存在着历史的联系。[20]作为 存在及其关系的肯定和确证,价值观念和原则构成了道德意识更为核心的内容。在其现实形态上,道德意识与价值观念往往相互交 错,很难截然加以分离。以儒家的仁道而言,它既是一种道德观念(要求将人视为目的而加以尊重),同时又是一种价值原则(肯定 每一个人都有其内在的存在价值)。与道德意识与价值观念的这种交错相应,道德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往往也和价值观念的制约联系在 一起。共同的价值原则,往往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中不同成员相互交往的基础,而社会的共识以及由此达到的行为协调,也同样离不 开对意义、价值的共同承诺。帕森斯曾谈及基础科学研究的合法性以及对科学研究的社会支持问题。基础科学由于缺乏当下可见的效 用,其存在的合法性(这种研究是否必要),及是否应给予支持,等等,往往成为问题。这里已涉及到价值上认同:确认基础科学的 价值,并使这种确认成为社会共同体中的共识,这是基础科学得以存在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21]这一事实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价值 观念对实现文化认同和社会共识(包括共同体内立场和行为之协调)的深刻影响

共同体内的文化认同和立场协调,主要从价值导向等方而推进了社会的整合。基本价值原则与道德理想相互融合,同时又构成了 合法性确认的根据。一定社会或时代的社会成员,往往是从该时代普遍接受的价值原则出发,对所处社会形态或秩序的合理性及合法 性作出评判.合理(rationality)与合法(legitimacy)当然有其不同的意义域,但二者亦非截然相对,当我们在实质的或价值的,而 非仅仅是形式的或工具的层面运用合理"这一概念时,它与”合法”往往呈现某种相通之处,合乎一定时代的基本价值原则,诚然并不 是合法性确认的唯一前提,但它却为确认既成社会形态合法性提供了一种支持,当缺乏这种支持时,社会系统的合法性便容易面临危 机。在传统杜会,权威主义的价值原则曾为这一时期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根据:近代以来,自由、平等、正义等等逐渐成为主流的价值 原则,它们同时也成为社会体制合法性评判的依据:当某种体制被认为合乎这些原则时,其合法性便获得了辩护:而当二者被视为相 互冲突时,这种社会的合法性往往便会受到质疑。合法性的确认是对该社会加以认同的逻辑前提之一,不难看到,在为合法性确认提 供支持的同时,作为道德意识深层内容的价值原则也作用于社会整合的过程。 从动态的角度看,社会系统既以结构的形式存在,又同时展开为一个过程。当某种社会系统依然有其存在根据时,社会的认同无 疑有助于该社会系统充分实现其围有价值。然而,当一种社会结构已失去存在理由时,向新的形态转换便成为更合理的历史趋向。与 社会衍化的这一过程相应,广义的社会整合也展开为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对既成社会秩序的维护,后者则体现 于社会转换的过程之中。道德意识与价值原则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同样展示了两重向度。除了前文所论及的为既成社会秩序提供支 持这一而外,道德意识与价值原则在社会变动时期也表现为社会整合的某种力量。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个性解放、自由平等、民主 正义等道德现念和价值原则,往往成为凝聚、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的旗帜,并激励人们为打破传统束簿、实现社会的历史转换而务力。 在这里,道德观念和价值原则无疑以特定方式表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整合作用。 基于如上看法,我们很难同意杜咸对道德理想、道德目标等的看法。从强调当前(the present)在道德生活中的意义这一前提出 发,杜威将一切道德理想及道德目标都视为一种梦想和空中楼阁,认为其”作用只是对现实作浪漫的修饰,至多只能成为写诗和小说 的材料。"T22]杜威在这里似乎将道德理想与生活实际不适当的分离开来。他围然有见于道德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解决实际问愿的作 用,但却未能注意:解决生活中实际问愿的日常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本身已渗入了普遍的道德理想:如果仅仅停留于此时此地的经 验情景而拒斥一切道德理想,则生活世界往往将被分解于互不关联的特殊时之中,而难以实现其内在的整合。 三规范、德性与秩序 相对于道德意识、道德理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更多地表现出形式的、系统的特点。A.吉滕斯曾把规则(Us)理解为社会 结构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之一·[23]道德规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广义的社会规则系统的一个方面。[24灯 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构成之一,道德规范的功能首先体现于社会的整合过程。杜尔凯姆已注意到这一点,在谈到道德规范的作用 时,他曾指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般而言,道德规范的特点在于它们明示了社会凝案(social solidarity)的基本条件。"T25]与 其他形式的当然之则一样,道德规范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它规定了社会共同体成员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尽管社会成员也许不一定 作出形式的承诺,但一旦成为某一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便往往以蕴含的方式承诺了规范所规定的义务,正是这种共同承担的义务, 从一个方而将社会成员维系在一起。在规定义务和责任的同时,道德规范也提供了对行为加以评判的一般准则,当行为合平规范时, 便会因其”对”或”正当"而获得肯定、赞扬和鼓励:一旦偏离规范,则这种行为就会因其“错"或不正当而受到谴责。以规范为依据的道 德评价,往往形成为一种普遍的杜会奥论,而对共同体中的社会成员来说,它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普遍的钓束机制。 从另一方而看,规范意味者为行为规定某种”度”。苟子已注意到这一点。在谈到礼"的起源时,苟子指出:“礼起于何也?日:人 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 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生,是礼之所以起也。”(《荀子·礼论》)这里的礼”泛指伦理政治的 制度及与之相应的规范系统,它不限于道德规范,但又包含道德规范。在荀子看来,礼的特点在于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规定一定的权利 和义务,这种规定同时构成了行为的度”或界限:在其度"或界限内,其行为(包括利益追求)是合理并容许的,超出了此度,则行 为将受到制止。从现代社会理论看,所谓度或界限,实际上蕴含了一种秩序的观念:正是不同的权利界限和行为界限,使社会形成为 一种有序的结构,从而避免了苟子所说的社会纷争。在这里,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一起,构成了社会秩序所以可能的一种担保。 与秩序的维护相辅相成的,是对失序或失范的抑制。在社会生活中,失序常常与反常或越轨相联系,如果反常或越轨行为蔓延 到一定的程度,社会系统中的有序状态便往往向无序状态衍化。而反常与越轨的控制,则离不开规范(包括道德规范)的制钓。在反 常与越轨未发生时,道德规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展示道德责任和义务以及提供行为选择的准则,以抑制可能的越轨动机:在越轨 和反常发生之后,规范则作为行为评价的根据,参与了外在的奥论造责和内在的良心责备等道德制裁的过程,并由此促使和推动行为 在越轨之后重新入轨。 从秩序的担保,到失序的控制,道德规范通过对社会行为的制约同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由此,我们不能不对 杜威的有关论点表示异议。如前所述,杜威将一般的道德理想视为没有实际意义的空幻意念,对他来说,惟有人所处的具体情景,才 对人的行为具有决定作用:"我们应当做这做那,只是因为我们处于某种既成的实际情景,只是因为我们处于某种具体的关系。"T26 在杜咸来看来,规范至多只能帮助我们了解环境的要求2刀,对于规范,我们根本无需问”要不要遵循“之类的间圈[28】.杜威的这些 看法注意到了具体情景对行为的制约,但由此对道德规范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则似平表现了过强的经验论立场。从逻辑上看,当情 景的特殊性消解了规范的普遍性时,一切越轨或反常的行为便都可以获得合法的依据并得到辩护,后者无疑将使社会的有序进程面临 危机,它对杜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规范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具有无人格的、外在于个体的特点,相对于此,德性则无法与具体人格相分离。然面,与人格的这种 联系,并不意味着德性游离于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之外。这里首先似乎应当对作为德性承担者的个人(p爬rs0n)所具有规定的作一分 析.布伯曾对个人(person)与个性(individuality)作了区分。在他看来,个人(person)已意识到他与他人的共在,而个性 (individuality)则仅仅意识到它自身的特殊性。"个性在与其他存在区分和分离的同时,也远离了真实的存在."T29布伯这一看法的
共同体内的文化认同和立场协调,主要从价值导向等方面推进了社会的整合。基本价值原则与道德理想相互融合,同时又构成了 合法性确认的根据。一定社会或时代的社会成员,往往是从该时代普遍接受的价值原则出发,对所处社会形态或秩序的合理性及合法 性作出评判。合理(rationality)与合法(legitimacy)当然有其不同的意义域,但二者亦非截然相对,当我们在实质的或价值的,而 非仅仅是形式的或工具的层面运用“合理”这一概念时,它与“合法”往往呈现某种相通之处。合乎一定时代的基本价值原则,诚然并不 是合法性确认的唯一前提,但它却为确认既成社会形态合法性提供了一种支持,当缺乏这种支持时,社会系统的合法性便容易面临危 机。在传统社会,权威主义的价值原则曾为这一时期的社会秩序提供了根据;近代以来,自由、平等、正义等等逐渐成为主流的价值 原则,它们同时也成为社会体制合法性评判的依据:当某种体制被认为合乎这些原则时,其合法性便获得了辩护;而当二者被视为相 互冲突时,这种社会的合法性往往便会受到质疑。合法性的确认是对该社会加以认同的逻辑前提之一,不难看到,在为合法性确认提 供支持的同时,作为道德意识深层内容的价值原则也作用于社会整合的过程。 从动态的角度看,社会系统既以结构的形式存在,又同时展开为一个过程。当某种社会系统依然有其存在根据时,社会的认同无 疑有助于该社会系统充分实现其固有价值。然而,当一种社会结构已失去存在理由时,向新的形态转换便成为更合理的历史趋向。与 社会衍化的这一过程相应,广义的社会整合也展开为共时形态和历时形态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对既成社会秩序的维护,后者则体现 于社会转换的过程之中。道德意识与价值原则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同样展示了两重向度。除了前文所论及的为既成社会秩序提供支 持这一面外,道德意识与价值原则在社会变动时期也表现为社会整合的某种力量。在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个性解放、自由平等、民主 正义等道德观念和价值原则,往往成为凝聚、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的旗帜,并激励人们为打破传统束缚、实现社会的历史转换而努力。 在这里,道德观念和价值原则无疑以特定方式表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整合作用。 基于如上看法,我们很难同意杜威对道德理想、道德目标等的看法。从强调当前(the present)在道德生活中的意义这一前提出 发,杜威将一切道德理想及道德目标都视为一种梦想和空中楼阁,认为其“作用只是对现实作浪漫的修饰,至多只能成为写诗和小说 的材料。”[22]杜威在这里似乎将道德理想与生活实际不适当的分离开来。他固然有见于道德在具体的生活情景中解决实际问题的作 用,但却未能注意:解决生活中实际问题的日常道德意识和道德规范,本身已渗入了普遍的道德理想;如果仅仅停留于此时此地的经 验情景而拒斥一切道德理想,则生活世界往往将被分解于互不关联的特殊时之中,而难以实现其内在的整合。 三 规范、德性与秩序 相对于道德意识、道德理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更多地表现出形式的、系统的特点。A. 吉滕斯曾把规则(rules)理解为社会 结构中的两个基本要素之一。[23]道德规范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为广义的社会规则系统的一个方面。[24] 作为社会系统的基本构成之一,道德规范的功能首先体现于社会的整合过程。杜尔凯姆已注意到这一点,在谈到道德规范的作用 时,他曾指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般而言,道德规范的特点在于它们明示了社会凝聚(social solidarity)的基本条件。”[25]与 其他形式的当然之则一样,道德规范具有普遍性的品格,它规定了社会共同体成员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尽管社会成员也许不一定 作出形式的承诺,但一旦成为某一社会共同体中的成员,便往往以蕴含的方式承诺了规范所规定的义务,正是这种共同承担的义务, 从一个方面将社会成员维系在一起。在规定义务和责任的同时,道德规范也提供了对行为加以评判的一般准则,当行为合乎规范时, 便会因其“对”或“正当”而获得肯定、赞扬和鼓励;一旦偏离规范,则这种行为就会因其“错”或不正当而受到谴责。以规范为依据的道 德评价,往往形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舆论,而对共同体中的社会成员来说,它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普遍的约束机制。 从另一方面看,规范意味着为行为规定某种“度”。荀子已注意到这一点,在谈到“礼”的起源时,荀子指出:“礼起于何也?曰:人 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 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生,是礼之所以起也。”(《荀子·礼论》)这里的“礼”泛指伦理政治的 制度及与之相应的规范系统,它不限于道德规范,但又包含道德规范。在荀子看来,礼的特点在于为每一个社会成员规定一定的权利 和义务,这种规定同时构成了行为的“度”或界限:在其“度”或界限内,其行为(包括利益追求)是合理并容许的,超出了此度,则行 为将受到制止。从现代社会理论看,所谓度或界限,实际上蕴含了一种秩序的观念;正是不同的权利界限和行为界限,使社会形成为 一种有序的结构,从而避免了荀子所说的社会纷争。在这里,道德规范与其他社会规范一起,构成了社会秩序所以可能的一种担保。 与秩序的维护相辅相成的,是对失序或失范的抑制。在社会生活中,失序常常与反常或越轨相联系,如果反常或越轨行为蔓延 到一定的程度,社会系统中的有序状态便往往向无序状态衍化。而反常与越轨的控制,则离不开规范(包括道德规范)的制约。在反 常与越轨未发生时,道德规范的作用主要表现在通过展示道德责任和义务以及提供行为选择的准则,以抑制可能的越轨动机;在越轨 和反常发生之后,规范则作为行为评价的根据,参与了外在的舆论谴责和内在的良心责备等道德制裁的过程,并由此促使和推动行为 在越轨之后重新入轨。 从秩序的担保,到失序的控制,道德规范通过对社会行为的制约同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由此,我们不能不对 杜威的有关论点表示异议。如前所述,杜威将一般的道德理想视为没有实际意义的空幻意念,对他来说,惟有人所处的具体情景,才 对人的行为具有决定作用:“我们应当做这做那,只是因为我们处于某种既成的实际情景,只是因为我们处于某种具体的关系。”[26] 在杜威来看来,规范至多只能帮助我们了解环境的要求[27], 对于规范,我们根本无需问“要不要遵循”之类的问题[28]。杜威的这些 看法注意到了具体情景对行为的制约,但由此对道德规范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则似乎表现了过强的经验论立场。从逻辑上看,当情 景的特殊性消解了规范的普遍性时,一切越轨或反常的行为便都可以获得合法的依据并得到辩护,后者无疑将使社会的有序进程面临 危机,它对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规范作为普遍的行为准则,具有无人格的、外在于个体的特点,相对于此,德性则无法与具体人格相分离。然而,与人格的这种 联系,并不意味着德性游离于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之外。这里首先似乎应当对作为德性承担者的个人(person)所具有规定的作一分 析。布伯曾对个人(person)与个性(individuality)作了区分。在他看来,个人(person)已意识到他与他人的共在,而个性 (individuality)则仅仅意识到它自身的特殊性。“个性在与其他存在区分和分离的同时,也远离了真实的存在。”[29]布伯这一看法的

位得注意之点,在于肯定了个人的共在之维:它从形而上的角度,把个人理解为社会系统中与他人共在的的一员,而不是与社会分离 的存在。 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个人总是要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此所谓杜会化,首先与自然的存在相对而言。当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时,他在相当意义上还只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存在,其自然的规定或天性往往构成了更主要的方而。与这一存在状态相应,个体的社会 化意味着超越自然的规定,使个体成为杜会学意义上的存在,这一过程同时包括社会对个体的按纳及对其成员资格的确认,而对个体 而言,则意味著逐渐形成对社会认同,并把自己视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与之相辅相成,社会化的过程往往涉及普遍规范与个体意 识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社会生活的参与以及教有、学习等等,社会的普遍规范(包括道德规范)逐渐为个体所接受,并内化和融合 与个体意识,这一过程同时以天性向德性的转换为其内容。德性作为社会化过程的产物,无疑具有普遍的规定,但作为社会规范与个 体意识的交融,它又内含个体之维,并与自我的观念相联系。当人还没有超越自然(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状态时,他同时也处于和 世界的原始”同一"中,此时个体既没有对象的观念,也缺乏真正的自我意识,因而尚谈不上社会的认同。个体对社会的认同,在逻辑 上以”我”的自觉为前提:对社会的认同,是由“我"来实现的。这样,社会的认同与自我观念的形成事实上构成了同一过程的两个方 面,它意味着扬弃个体与世界的原始同一,达到个体与社会的辩证互动。 这种互动具体展开于德性对社会行为的制钓过程。相对于个体所处情景的变动性及行为的多样性,德性具有相对统一、稳定的品 格,它并不因特定情景的每一变迁而变迁,而是在个体存在过程中保持相对的绵延统一:处于不同时空情景中的“我”,其真实的德性 并不逐物而动、随境而迁。王阳明已注意到这一点,他曾对意与良知作了区分:”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 意则有是有非,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依得良知,则无有不是矣。T30]此处之意,是指在经验活动中形成的偶发的意念或 意识:良知则构成了德性的具体内容。意念作为应物而起者,带有自发和偶然的特点。所谓应物而起,也就是因境(对象)而生,随 物而转,完全为外部对象所左右,缺乏内在的确定性。与意念不同,作为真实德性的良知并非偶然生成于某种外部境语,也并不随对 象的生灭而生灭。它乃是在行著习察的过程中凝化为内在的人格,因而具有专一恒定的品格,并能对对意念的是非加以判定。[31]王 阳明的这一看法已有见于德性与人格在时间之维上的绵延性及行为过程中的稳定性。[32] 如前所述,道德规范对社会行为具有普遍的制约作用,然而,规范在尚未为个体接受时,总是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律令,它与个体 的具体行为之间往往存在者一种距离。化规范为个体的具体行为,既需要理性的认知(对规范的理解),也涉及意志的选择和情感的 认同,而在这一系列环节中,理性、意志以及情感乃是作为统一的德性结构的不同方面影响者规范的接受过程。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 交互作用:德性的形成过程包含者规范的内化:德性在形成之后又构成了规范的现实作用所以可能的前提之一·而通过为规范的现实 作用提供支持,德性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参与了社会系统中行为的有序化过程。 个体作为作为特定的历史存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所面对的环境往往各异:就行为过程而言,其由以展开的具体情景也常常变 动不居:要选择合理的行为方式,仅仅依赖一般的行为规范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规范无法穷尽行为与情景的全部多样性与变动性。在 这里,情景的具体分析,便显得尤为重要。实用主义者(如杜威)、存在主义者(如萨特)对此已有所注意:杜威将具体情景中的探 素与解题提到突出地位,萨特强调个体在行为迭择中的决定作用,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在关注情景的 特殊性及个体作用的同时,往往将情景的特殊性与规范普遍性视为相互排斥的两个方面,并常常倾向于以前者消解后者,这种立场在 逻辑上很难避免相对主义。以此反观德性的作用,便不难看到它对克服上述偏向的意义。如前文所说,德性既包含着作为规范内含的 普遍内容,又展开为理性、意志和情感等相统一的个体意识结构,这种二重性,为德性将特定情景的分析与普遍规范的引用这二者加 以结合提供了可能。作为稳定、统一的人格,德性使个体在身处各种特定境遇时,既避免走向无视情景特殊性的独断论,又超越蔑祝 普遍规范制钓的相对主义。儒家所提出的经与权相统一的理论,已有见于此。经”泛指原则的普遍性,“权"则涉及情景的分析,经与 权的互补,意味着原则的范导与情景的处理之间的相容,而对儒家来说,这种统一又是通过人格和德性的作用过程而实现。[33]这 看法无疑注意到了在道德实践中,德性对普遍沟通规范与特定情景所其有的意义。从现实的行为过程看,规范的引用与情景的分析、 判断,以及特定情景中可能的行为方式的权衡、选择,等等,都受制于行为主体统一的人格结构(包括德性),不妨说,人格、德性 的统摄,为社会行为走向以权应变与稳定有序的统一,提供了内在机制。 前文曾论及,社会生活过程的有序运行,离不开对越轨、反常行为的控制。就失范与失序的抑制而言,规范的功能较多地展现于 外在的公共空间之域,相形之下,德性在这方面的作用则更多地体现于个体的内在意识层而。作为统一的意识结构,德性既以自觉的 理性及康德所谓善良意志为内容,也包含情感之维。在道德意识的层面上,情感往往取得同情、耻感、内疚等形式。休谟曾对同情 (Sym即athy)作了细致的分析,并将其视为整个道德系统的基础,这种看法表现了其经验论的立场,无疑有其局限,但同情在道德行 为中的作用却是伦理的事实:从最一般的论域看,同情的意义首先在于为仁道原则的实现(在行为中的实际遵循)提供了情感的基 础:而通过对他人、群体的尊重、关心,同情意识同时也拒斥了各种敌视社会(反社会)、危害群体的行为向度,并促进了社会成员 之间的凝聚 耻感与内疚具有不同的情感维度。作为道德意识,耻感似乎更多地与自我尊严的维护相联系,其产生和形成总是件随着对自我尊 严的关注。这种尊严主要并不基于个体感性的、生物性的规定,而是以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为根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儒家对耻感 予以高度的重视。孔子已要求"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孟子进面将耻感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耻之于人大矣。m人不可以无 耻。”(《孟子·尽心上》)直到后来的王夫之、顾炎武,依然一再强调知耻的意义:“世教衰,民不兴行,`见不贤而内自省”,知耻之 功大矣。”(王夫之:《思问录内篇》)”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停林文集》畚三)人作 为社会存在具有内在的尊严,有耻、知耻是在心理情感的层而对这种尊严的锥护,无耻则表明完全漠视这种尊严(甘愿丧失人之为人 的尊严)。 从道德情感与社会行为的关系看,耻感的缺乏意味者解除所有内、外的道德约束,在无耻的心理情感下,一个人既不会感受到内 在良心的责备,也难以对外在奥论的谴责有所触动:一切丧失尊严、桃战社会、越出秩序的行为,对他来说都是可能的。反之,耻感 的确立,则使个体在行为过程中时时关注人之为人的尊严,防范与拒斥一切可能对内在尊严带来负而后果的动机和行为。就社会系统 而言,自我尊严的维护,总是引向自觉的履行作为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将自我的行为纳入规范所规定的界域内,并使个体以越轨为
值得注意之点,在于肯定了个人的共在之维:它从形而上的角度,把个人理解为社会系统中与他人共在的的一员,而不是与社会分离 的存在。 作为社会中的一员,个人总是要经历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此所谓社会化,首先与自然的存在相对而言。当人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时,他在相当意义上还只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存在,其自然的规定或天性往往构成了更主要的方面。与这一存在状态相应,个体的社会 化意味着超越自然的规定,使个体成为社会学意义上的存在,这一过程同时包括社会对个体的接纳及对其成员资格的确认,而对个体 而言,则意味着逐渐形成对社会认同,并把自己视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与之相辅相成,社会化的过程往往涉及普遍规范与个体意 识之间的相互作用。通过社会生活的参与以及教育、学习等等,社会的普遍规范(包括道德规范)逐渐为个体所接受,并内化和融合 与个体意识,这一过程同时以天性向德性的转换为其内容。德性作为社会化过程的产物,无疑具有普遍的规定,但作为社会规范与个 体意识的交融,它又内含个体之维,并与自我的观念相联系。当人还没有超越自然(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状态时,他同时也处于和 世界的原始“同一”中,此时个体既没有对象的观念,也缺乏真正的自我意识,因而尚谈不上社会的认同。个体对社会的认同,在逻辑 上以“我”的自觉为前提:对社会的认同,是由“我”来实现的。这样,社会的认同与自我观念的形成事实上构成了同一过程的两个方 面,它意味着扬弃个体与世界的原始同一,达到个体与社会的辩证互动。 这种互动具体展开于德性对社会行为的制约过程。相对于个体所处情景的变动性及行为的多样性,德性具有相对统一、稳定的品 格,它并不因特定情景的每一变迁而变迁,而是在个体存在过程中保持相对的绵延统一:处于不同时空情景中的“我”,其真实的德性 并不逐物而动、随境而迁。王阳明已注意到这一点,他曾对意与良知作了区分:“意与良知当分别明白。凡应物起念处,皆谓之意。 意则有是有非,知得意之是与非者,则谓之良知。依得良知,则无有不是矣。”[30]此处之意,是指在经验活动中形成的偶发的意念或 意识;良知则构成了德性的具体内容。意念作为应物而起者,带有自发和偶然的特点。所谓应物而起,也就是因境(对象)而生,随 物而转,完全为外部对象所左右,缺乏内在的确定性。与意念不同,作为真实德性的良知并非偶然生成于某种外部境遇,也并不随对 象的生灭而生灭。它乃是在行著习察的过程中凝化为内在的人格,因而具有专一恒定的品格,并能对对意念的是非加以判定。[31]王 阳明的这一看法已有见于德性与人格在时间之维上的绵延性及行为过程中的稳定性。[32] 如前所述,道德规范对社会行为具有普遍的制约作用,然而,规范在尚未为个体接受时,总是表现为一种外在的律令,它与个体 的具体行为之间往往存在着一种距离。化规范为个体的具体行为,既需要理性的认知(对规范的理解),也涉及意志的选择和情感的 认同,而在这一系列环节中,理性、意志以及情感乃是作为统一的德性结构的不同方面影响着规范的接受过程。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 交互作用:德性的形成过程包含着规范的内化;德性在形成之后又构成了规范的现实作用所以可能的前提之一。而通过为规范的现实 作用提供支持,德性同时也从一个方面参与了社会系统中行为的有序化过程。 个体作为作为特定的历史存在,其所处的社会关系、所面对的环境往往各异;就行为过程而言,其由以展开的具体情景也常常变 动不居;要选择合理的行为方式,仅仅依赖一般的行为规范显然是不够的,因为规范无法穷尽行为与情景的全部多样性与变动性。在 这里,情景的具体分析,便显得尤为重要。实用主义者(如杜威)、存在主义者(如萨特)对此已有所注意;杜威将具体情景中的探 索与解题提到突出地位,萨特强调个体在行为选择中的决定作用,等等,都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实用主义和存在主义在关注情景的 特殊性及个体作用的同时,往往将情景的特殊性与规范普遍性视为相互排斥的两个方面,并常常倾向于以前者消解后者,这种立场在 逻辑上很难避免相对主义。以此反观德性的作用,便不难看到它对克服上述偏向的意义。如前文所说,德性既包含着作为规范内含的 普遍内容,又展开为理性、意志和情感等相统一的个体意识结构,这种二重性,为德性将特定情景的分析与普遍规范的引用这二者加 以结合提供了可能。作为稳定、统一的人格,德性使个体在身处各种特定境遇时,既避免走向无视情景特殊性的独断论,又超越蔑视 普遍规范制约的相对主义。儒家所提出的经与权相统一的理论,已有见于此。“经”泛指原则的普遍性,“权”则涉及情景的分析,经与 权的互补,意味着原则的范导与情景的处理之间的相容,而对儒家来说,这种统一又是通过人格和德性的作用过程而实现。[33]这一 看法无疑注意到了在道德实践中,德性对普遍沟通规范与特定情景所具有的意义。从现实的行为过程看,规范的引用与情景的分析、 判断,以及特定情景中可能的行为方式的权衡、选择,等等,都受制于行为主体统一的人格结构(包括德性),不妨说,人格、德性 的统摄,为社会行为走向以权应变与稳定有序的统一,提供了内在机制。 前文曾论及,社会生活过程的有序运行,离不开对越轨、反常行为的控制。就失范与失序的抑制而言,规范的功能较多地展现于 外在的公共空间之域,相形之下,德性在这方面的作用则更多地体现于个体的内在意识层面。作为统一的意识结构,德性既以自觉的 理性及康德所谓善良意志为内容,也包含情感之维。在道德意识的层面上,情感往往取得同情、耻感、内疚等形式。休谟曾对同情 (sympathy)作了细致的分析,并将其视为整个道德系统的基础,这种看法表现了其经验论的立场,无疑有其局限,但同情在道德行 为中的作用却是伦理的事实;从最一般的论域看,同情的意义首先在于为仁道原则的实现(在行为中的实际遵循)提供了情感的基 础;而通过对他人、群体的尊重、关心,同情意识同时也拒斥了各种敌视社会(反社会)、危害群体的行为向度,并促进了社会成员 之间的凝聚 耻感与内疚具有不同的情感维度。作为道德意识,耻感似乎更多地与自我尊严的维护相联系,其产生和形成总是伴随着对自我尊 严的关注。这种尊严主要并不基于个体感性的、生物性的规定,而是以人之为人的内在价值为根据。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儒家对耻感 予以高度的重视。孔子已要求“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孟子进而将耻感提到了更突出的地位:“耻之于人大矣。”“人不可以无 耻。”(《孟子·尽心上》)直到后来的王夫之、顾炎武,依然一再强调知耻的意义:“世教衰,民不兴行,‘见不贤而内自省’,知耻之 功大矣。”(王夫之:《思问录·内篇》)“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人作 为社会存在具有内在的尊严,有耻、知耻是在心理情感的层面对这种尊严的维护,无耻则表明完全漠视这种尊严(甘愿丧失人之为人 的尊严)。 从道德情感与社会行为的关系看,耻感的缺乏意味着解除所有内、外的道德约束,在无耻的心理情感下,一个人既不会感受到内 在良心的责备,也难以对外在舆论的谴责有所触动;一切丧失尊严、挑战社会、越出秩序的行为,对他来说都是可能的。反之,耻感 的确立,则使个体在行为过程中时时关注人之为人的尊严,防范与拒斥一切可能对内在尊严带来负面后果的动机和行为。就社会系统 而言,自我尊严的维护,总是引向自觉的履行作为社会成员应尽的义务,将自我的行为纳入规范所规定的界域内,并使个体以越轨为

耻。可以看到,通过将反社会的越轨行为抑制于未然或潜在状态,作为德性内容的耻感构成了维护杜会秩序的内在心理机制之一。 [34个 与耻感相近并构成德性另一重内容的道德情感是内疚。较之耻感对尊严的确认,内疚更直接地与是否履行道德义务相联系:”当 我们没有做道德原则要求做的事或做了道德原则不容许做的事时,我们通常便会对此感到内疚.“T3]海德格尔在考察内疚(guty) 时,曾追湖了其日常用法的原始涵义,认为它最初与负债意识(欠别人什么)相联系,由此又进一步产生了责任观念[36]。作为道德 情感的内疚,同样以责任和义务的承诺为共前提。责任与义务首先相对于群体和他人而言,因此,尽管内疚最初表现为一种心理体 验,但它总是涉及主体间和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3刀因未尽义务而感到内汽,不仅仅使个体的内在精神和意识通过反省而得到洗 礼和升华,而且同时直接地影响个体的社会行为:它从内在意识的层面,促使主体抑制与道德义务和责任相冲突的行为动机。在这 意义上,内孩与耻感一样,为社会生活的有序展开提供了内在心理机制上的担保。 概而言之,普遍的规范与内在的德性作为道德系统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构成了社会秩序所以可能的条件之一,并从不同的维度 制韵者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在这里,道德与存在的本源关系,也得到了更具体的确证。 四礼之用和为贵 作为存在的背景,社会的有序结构有多重表现形式。如前文所论及的,首先是与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相联系的生活世界,它源于 家庭关系,展开于生活过程的各个方面,为日常存在提供了切近的空间。社会结构的另一方而,是广义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的存 在.从团体(group),如学术团体、艺术团体、宗教团体等等),到组织(organization),如经济领域的企业组织、政治领域的政 党组织等等:从公共的科学、教有、文化机构,如学校、科研机构以及其他公共教育文化设施的管理机构。到国家政权机构,包括各 级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等等,广义的体制化的系统或体制结构展开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而。相对于生活世界中日用常行的自发性, 体制化的存在更多地带有组织化的特点,其运行表现为一个有组织的、相对自觉的过程。 统一的社会系统从总体上看既包含生活世界,又以体制组织为其内容。如前所述,生活世界与体制组织无疑具有不同规定及存在 面向,但作为统一的社会系统的两个方面,二者又并非被此隔绝、截然相分。从现实的存在形态看,生活世界与体制组织之间,往往 具有互滤互融的特点。家庭是日常生活的基本载体之一,然而,它同时又与不同类型的婚烟制度相联系,后者(婚烟制度)则是广义 的体制组织的形式之一:同时,家庭会成员往往参与各种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等活动,从而,家庭也相应地涉及政治、经济、宗 教、教有等领城的体制与组织。[38]同样,政治权力也不仅仅限于国家政权等机构,在经济组织(如企业)、教有机构(如学校)、 以及家庭等等之中,都可以看到权力的影响与作用。即使宗教团体和组织,也往往同时横贯于生活世界与体制组织之间,如西方的教 会组织,便既包括展开于生活世界的日常宗教活动(如析祷)等,也兼及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活动(如对世俗权力的影响、教会财产 的运作等)·[39]总之,作为统一的社会系统中的相关方面,生活世界与体制化的结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 当然,生活世界与体制组织在广义社会系统中的相关互融,并不妨碍我们在相对独立的意义上,对二者分别加以考察。就体制组 织而言,其存在形态首先带有无人格性的特点。在生活世界中,家庭、邻里、朋友等社会关系通常以人为直接的关系项,也就是说, 在日常的交往活动中,我们所面对的对象,都是具体的人。相对于此,体制化的存在往往表现为超然于人的结构,在各种以效率为目 标的管理机构中,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常常构成了其组织原则:后者有别于关注人的存在意义的价值理性。以不同程度的形式化为特 征,体制组织形成了自身的运行机制。 然而,这只是问避的一个方面。在体制组织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总是处处包含着人的参与:,它的功能和作用,也惟有通过人的活 动才能实现。制度本身是无生命的存在,它的活力必须由人赋予。当我们与不同形式的团体、组织、机构、制度发生联系时,我们与 之打交道的,并不仅仅是无人格的物,而且同时是赋予体制以生命的人。作为体制的运作者,这种人具有两重性:他既是体制的代 表,又是具体的个人:与之相应,我们所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形式化的结构,而同时是他人的存在:主体间的交往不仅是生活世界中 的存在境遇,而且也是体制运作过程中的本体论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体制组织的核心是人。【40 由此,我们不难注意到体制化存在的两重品格:它既是一种超然于人的形式化结构,又与人的作用过程息息相关(无人的参与则 无生命)。作为体制运作的条件,人的参与过程始终伴随着道德的作用。儒家很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在谈到礼的作用方式时,《论 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如前所述,儒家所说的”礼”,既指普遍的规范体系,又包括社会 政治的制度,孔子推崇备至的周礼,便兼指周代的社会玫治体制:”和“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现于交往过程的伦理原则:从消极的方 面看,它要求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以化解繁张、抑制冲突:从积极的方面看,“和"则意味着主体之间同心同德、协力合 作,礼本来首先涉及制度层而的运作(包括一般仪式的举行、等级结构的规定、政令的颜布执行、君臣上下之间的相处等等),但儒 家却将这种制度的运作与和"这样的伦理原则联系起来,强调礼的作用过程,贵在遵循、体现”和"的原则,这里已有见于体制组织的 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制的的运行过程,离不开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和"的原则达到彼此的相互理解与沟通, 从而消除冲突、同心协力):质言之,制度(礼)的作用过程,需要道德原则(和)的担保。 作为体制组织合理运作的条件,道德的担保涉及多重原则,其中基本或核心的主要是两条,即正义原则与仁道原则。正义首先意 味着对权利的尊重,具体而言,它要求公正地对待和确保一定社会内每一个人的应有权利.体制组织带有公共的性质,它所面对的是 一定社会范围内的不同社会成员,公正地对待社会成员,是体制获得合理性的前提。所谓一定社会范围本身当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在不同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近代以来,在形式化的结构这一层而,以上要求似平已成为恩中应有之意,因为体制组织的建构本 身已被赋予如.上职能。这里已体现了道德原则对社会体制的制钓,当杜尔凯姆肯定法律以道德为基础时,他显然已从一个方面注意到 了这一点。[41]当然,在体制的运行过程中,这种原则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体现,又涉及体制的运作者(制度、机构等等的代表)与 体制所而对者(体制的服务或作用对象)之间的相互交往。正义原则能否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得到实现,直接关系着体制本身的职能能 否合理地落实
耻。可以看到,通过将反社会的越轨行为抑制于未然或潜在状态,作为德性内容的耻感构成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内在心理机制之一。 [34] 与耻感相近并构成德性另一重内容的道德情感是内疚。较之耻感对尊严的确认,内疚更直接地与是否履行道德义务相联系:“当 我们没有做道德原则要求做的事或做了道德原则不容许做的事时,我们通常便会对此感到内疚。”[35]海德格尔在考察内疚(guilty) 时,曾追溯了其日常用法的原始涵义,认为它最初与负债意识(欠别人什么)相联系,由此又进一步产生了责任观念[36]。作为道德 情感的内疚,同样以责任和义务的承诺为其前提。责任与义务首先相对于群体和他人而言,因此,尽管内疚最初表现为一种心理体 验,但它总是涉及主体间和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37]因未尽义务而感到内疚,不仅仅使个体的内在精神和意识通过反省而得到洗 礼和升华,而且同时直接地影响个体的社会行为:它从内在意识的层面,促使主体抑制与道德义务和责任相冲突的行为动机。在这一 意义上,内疚与耻感一样,为社会生活的有序展开提供了内在心理机制上的担保。 概而言之,普遍的规范与内在的德性作为道德系统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构成了社会秩序所以可能的条件之一,并从不同的维度 制约着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在这里,道德与存在的本源关系,也得到了更具体的确证。 四 礼之用 和为贵 作为存在的背景,社会的有序结构有多重表现形式。如前文所论及的,首先是与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相联系的生活世界,它源于 家庭关系,展开于生活过程的各个方面,为日常存在提供了切近的空间。社会结构的另一方面,是广义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的存 在。从团体(group),如学术团体、艺术团体、宗教团体等等),到组织(organization),如经济领域的企业组织、政治领域的政 党组织等等;从公共的科学、教育、文化机构,如学校、科研机构以及其他公共教育文化设施的管理机构,到国家政权机构,包括各 级立法、行政、司法机构等等,广义的体制化的系统或体制结构展开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相对于生活世界中日用常行的自发性, 体制化的存在更多地带有组织化的特点,其运行表现为一个有组织的、相对自觉的过程。 统一的社会系统从总体上看既包含生活世界,又以体制组织为其内容。如前所述,生活世界与体制组织无疑具有不同规定及存在 面向,但作为统一的社会系统的两个方面,二者又并非彼此隔绝、截然相分。从现实的存在形态看,生活世界与体制组织之间,往往 具有互渗互融的特点。家庭是日常生活的基本载体之一,然而,它同时又与不同类型的婚姻制度相联系,后者(婚姻制度)则是广义 的体制组织的形式之一;同时,家庭会成员往往参与各种经济、政治、宗教、教育等活动,从而,家庭也相应地涉及政治、经济、宗 教、教育等领域的体制与组织。[38]同样,政治权力也不仅仅限于国家政权等机构,在经济组织(如企业)、教育机构(如学校)、 以及家庭等等之中,都可以看到权力的影响与作用。即使宗教团体和组织,也往往同时横贯于生活世界与体制组织之间,如西方的教 会组织,便既包括展开于生活世界的日常宗教活动(如祈祷)等,也兼及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活动(如对世俗权力的影响、教会财产 的运作等)。[39]总之,作为统一的社会系统中的相关方面,生活世界与体制化的结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 当然,生活世界与体制组织在广义社会系统中的相关互融,并不妨碍我们在相对独立的意义上,对二者分别加以考察。就体制组 织而言,其存在形态首先带有无人格性的特点。在生活世界中,家庭、邻里、朋友等社会关系通常以人为直接的关系项,也就是说, 在日常的交往活动中,我们所面对的对象,都是具体的人。相对于此,体制化的存在往往表现为超然于人的结构,在各种以效率为目 标的管理机构中,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常常构成了其组织原则;后者有别于关注人的存在意义的价值理性。以不同程度的形式化为特 征,体制组织形成了自身的运行机制。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体制组织实际的运作过程中,总是处处包含着人的参与;它的功能和作用,也惟有通过人的活 动才能实现。制度本身是无生命的存在,它的活力必须由人赋予。当我们与不同形式的团体、组织、机构、制度发生联系时,我们与 之打交道的,并不仅仅是无人格的物,而且同时是赋予体制以生命的人。作为体制的运作者,这种人具有两重性:他既是体制的代 表,又是具体的个人;与之相应,我们所面对的,也不仅仅是形式化的结构,而同时是他人的存在;主体间的交往不仅是生活世界中 的存在境遇,而且也是体制运作过程中的本体论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体制组织的核心是人。[40] 由此,我们不难注意到体制化存在的两重品格:它既是一种超然于人的形式化结构,又与人的作用过程息息相关(无人的参与则 无生命)。作为体制运作的条件,人的参与过程始终伴随着道德的作用。儒家很早已注意到这一点,在谈到礼的作用方式时,《论 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点:“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如前所述,儒家所说的“礼”,既指普遍的规范体系,又包括社会 政治的制度,孔子推崇备至的周礼,便兼指周代的社会政治体制;“和”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体现于交往过程的伦理原则:从消极的方 面看,它要求通过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沟通,以化解紧张、抑制冲突;从积极的方面看,“和”则意味着主体之间同心同德、协力合 作。礼本来首先涉及制度层面的运作(包括一般仪式的举行、等级结构的规定、政令的颁布执行、君臣上下之间的相处等等),但儒 家却将这种制度的运作与“和”这样的伦理原则联系起来,强调礼的作用过程,贵在遵循、体现“和”的原则,这里已有见于体制组织的 背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体制的的运行过程,离不开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和”的原则达到彼此的相互理解与沟通, 从而消除冲突、同心协力);质言之,制度(礼)的作用过程,需要道德原则(和)的担保。 作为体制组织合理运作的条件,道德的担保涉及多重原则,其中基本或核心的主要是两条,即正义原则与仁道原则。正义首先意 味着对权利的尊重,具体而言,它要求公正地对待和确保一定社会内每一个人的应有权利。体制组织带有公共的性质,它所面对的是 一定社会范围内的不同社会成员,公正地对待社会成员,是体制获得合理性的前提。所谓一定社会范围本身当然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在不同社会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近代以来,在形式化的结构这一层面,以上要求似乎已成为题中应有之意,因为体制组织的建构本 身已被赋予如上职能。这里已体现了道德原则对社会体制的制约,当杜尔凯姆肯定法律以道德为基础时,他显然已从一个方面注意到 了这一点。[41]当然,在体制的运行过程中,这种原则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体现,又涉及体制的运作者(制度、机构等等的代表)与 体制所面对者(体制的服务或作用对象)之间的相互交往。正义原则能否在这一过程中真正得到实现,直接关系着体制本身的职能能 否合理地落实

较之正义原则,仁道原则更多地指向人自身的存在价值。早在先秦,儒学的开创者孔子已提出了仁的学说,并以”爱人”界定仁· 孟子进而将性善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与仁政主张联系起来,从内在的心理情感与外在的社会关系上展开了孔子所奠定的仁道现观 念。在汉儒的先之以博爱,数之以仁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宋儒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等 看法中,仁道的原则得到了更具体的闸发。事实上,作为”礼”作用方式的和"”,已体现了仁道的原则。仁道的基本精神在于尊重和确 认每一主体的内在价值,它既肯定主体自我实现的意愿,又要求主体间真诚地承认彼此的存在意义。孔子以爱人规定仁,孟子以侧隐 之心为仁之端,等等,无不表现了对主体内在价值的注重。不妨说,相对于正义原则同时趋向于形式的合理性,1仁道原则所指向的 首先是实质的合理性。体制组织所具有的超然于人的这一面,使之在运作过程中常常表现出冷峻的、无人格的特点,这种存在形式很 容易给人以异己之感:在体制的运作者与体制所服务或作用对象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如果以仁道原则为导向,则将有助于限制或消解 体制对人的异己性。 以经济领城面言,经济的体制组织(如企业、公司等)主要以利益为追求的目标,而市场本身也以功利和效率为原则:它仅仅根 据竞争者的实际效率来给予相应的回报。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种经济组织常常容易趋向于不顾环境、生态、职工的工作条件以及社会 的长远发展而从事开发、生产等经营活动,它往往以牺性人的生存环境、外部生态、生产者的健康等等为其经济效益的代价。经济组 织作为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形式,本来是人存在的条件,但在失控的状态下,它却反过来威胁人自身的存在:这种现象可以看作 是特定意义上的异化。如何避免与克服经济组织体制(economic institution)可能导致的异化趋向?在这里,包括仁道原则在内的道 德制衡便显得十分重要。如前所述,仁道原则要求时时关注人自身的存在价值与存在意义,后者也意味着为人的存在提供合理、完 善、持久的发展空间,避免以片面的利益追求危及人自身的存在,这种道德定势对于规范经济组织体制作用方式、抑制过度的功利冲 动,等等,无疑可以从价值观念上提供支持。 作为社会分化的产物,经济、政治、法律等不同形式的体制组织构成了人存在的背景与前提:社会的秩序及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 生产,都离不开体制的保证。以非人格的形式化结构与运作过程中人的参与为双重规定,体制组织的合理运作既有其形式化的、程序 性的前提,也离不开道德的担保和制衡:而通过参与和制钓体制组织的运作过程,道德同时也立足于历史过程本身,从一个方面回应 了真实的存在何以可能这一问愿.[42] 五境界与个体整合 社会的整合、秩序的确立、生活世界与杜会体制的合理运行,等等,主要从类的层而,展示了人的存在所以可能的条件:道德作 为上述各个方面的内在担保,同时也在一个维度上,使自身的存在获得了根据。在这里,对道德何以必要或善何以必要这一本源性的 问题的考察,首先基于社会本体论。 人的存在既以类的形式展开,又有其个体的向度:向具体存在或真实存在的回归,同样也有类与个体两重维度。二者当然并非彼 此悬隔,但确乎又有不同的侧重之点,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考察。如前所述,布拉德雷曾主要从个体存在之维,提出了如下问避 为什么我应当是道德的(why I should be moral)?在布拉德雷看来,这一问愿应当在自我实现这一层而上来思考,换言之,道德之 所以必要,主要便在于它有助于人的自我实现(sef-realization)。不过,布拉德雷同时又将自我理解为与实在(reality)相对的现 象,认为自我"除了现象,什么也不是."T43]与这一观点相应,布拉德雷将自我实现主要理解为”自觉地与无限的大全(infinite woe)融合为一"T44]。这一看法似乎多少将自我消解在整体中。不难看到,尽管布拉德雷将"我为什么应是道德的与自我实现联系 起来,但对大全、整体的强调,使他并未能真正解决”道德何以必要"与个体存在的关系间题。 以个体的存在为视域,我们似乎应对境界予以必要的关注。从广义上看,境界首先与个体或自我的存在状态相联系:具体而言, 可以从个体存的在统一或自我的整合这一侧而来理解境界。康德曾从认识论的角度,将我思(Ihk)规定为意识的综合统一,如果 不限于认识论,面从本体论之维考察自我或个体的存在,那么,境界便表现为个体存在的综合统一形态。如后文将进一步论述的,这 里的境界固然与精神领域相联系,但又不限于精神的领域,【45它形成和展开于历史实践过程,并在实践过程中得到确证:【4简言 之,境界凝结了个体的全部生活,是基于整个实践过程而达到的个体整合与统一。个体的这种综合统一,从一个方而展示了存在的具 体性:而境界的提升,则相应地意味着不断走向或回归具体的存在。 存在的具体性包含者存在规定的多样性或多方面性,在个体存在这一向度上,亦体现了这一点。作为自我整合与个体统一的形 态,广义的境界同样涉及存在的多方面规定,并以存在规定的多方面实现和完成为其内容。从本体论的层面看,需要的满足是个体存 在的基本前提:存在的多方面性首先也体现在需要的多重性上。大致而言,与身心两重向度相应,个体的需要也主要分别体现于感性 的生命层面和理性的精神层而。在伦理学史上,经验论及各种形式的功利主义较多地关注于人的感性、生命需要,理性主义及道义论 则将理性的精神需要放在更为优先的地位:这种不同的侧重,从一个方面表明,个体的需要并不仅仅限于一端:经验论(以及功利主 义)和理性主义(及道义论)各自把挥了需要的一个方而,而他们的问避则在于未能注意需要的多样性。片面注重感性需要,往往很 难使人真正超越自然的规定:在”生之谓性"这一层而,人与自然的存在的区别显然是有限的:理性的需要的过度强调,则容易导致对 感性生命的虚无主义态度,在理学家所谓馈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道德评判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生死涉及的是生命的存在, 守节则表现为一种理性精神的追求,片面突出精神完关的需要,在此引向了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可以看到,需要的合理确认与满足, 离不开道德系统的调节:合理的道德系统内在地包含着对人的感性生命和理性本质的双重确认,惟有从这种感性与理性统一的伦理原 则出发,生命的肯定与精神的追求才能达到和谐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同时也表征着存在本身多方而规定的实现 在个体的存在过程中,需要的满足离不开能力的发展。能力与秉赋不同,秉赋可以成为能力的潜在出发点,但不同于现实的能 力,能力也有别于一般的技艺,技艺主要服务于外在目的,是达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能力形成于人的存在过程,它既是个体存在 所以可能的条件,又标志者存在所达到的形态或境界:能力的发展状态,同时确证着个体规定的实现程度。个体的能力可以彼此不 同:我们无法强求每一个体都兵有同样的能力:但是,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背景发展个体秉赋所提供的潜能,在自足其性的意义 上使之形成为现实的能力,则是个体自我完成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所谓自足其性,既表明能力的发展不应当无视个体的差异 (不能勉强每一个体都达到划一的目标),也意味着能力是存在的内在规定,不是工具意义上的外在要素:以最基本的劳动的能力而
较之正义原则,仁道原则更多地指向人自身的存在价值。早在先秦,儒学的开创者孔子已提出了仁的学说,并以“爱人”界定仁。 孟子进而将性善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与仁政主张联系起来,从内在的心理情感与外在的社会关系上展开了孔子所奠定的仁道观 念。在汉儒的“先之以博爱,教之以仁也”(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宋儒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等 看法中,仁道的原则得到了更具体的阐发。事实上,作为“礼”作用方式的“和”,已体现了仁道的原则。仁道的基本精神在于尊重和确 认每一主体的内在价值,它既肯定主体自我实现的意愿,又要求主体间真诚地承认彼此的存在意义。孔子以爱人规定仁,孟子以恻隐 之心为仁之端,等等,无不表现了对主体内在价值的注重。不妨说,相对于正义原则同时趋向于形式的合理性,1仁道原则所指向的 首先是实质的合理性。体制组织所具有的超然于人的这一面,使之在运作过程中常常表现出冷峻的、无人格的特点,这种存在形式很 容易给人以异己之感;在体制的运作者与体制所服务或作用对象之间的交往过程中,如果以仁道原则为导向,则将有助于限制或消解 体制对人的异己性。 以经济领域而言,经济的体制组织(如企业、公司等)主要以利益为追求的目标,而市场本身也以功利和效率为原则:它仅仅根 据竞争者的实际效率来给予相应的回报。在利益的驱使下,各种经济组织常常容易趋向于不顾环境、生态、职工的工作条件以及社会 的长远发展而从事开发、生产等经营活动,它往往以牺牲人的生存环境、外部生态、生产者的健康等等为其经济效益的代价。经济组 织作为物质资料生产与再生产的形式,本来是人存在的条件,但在失控的状态下,它却反过来威胁人自身的存在;这种现象可以看作 是特定意义上的异化。如何避免与克服经济组织体制(economic institution)可能导致的异化趋向?在这里,包括仁道原则在内的道 德制衡便显得十分重要。如前所述,仁道原则要求时时关注人自身的存在价值与存在意义,后者也意味着为人的存在提供合理、完 善、持久的发展空间,避免以片面的利益追求危及人自身的存在,这种道德定势对于规范经济组织体制作用方式、抑制过度的功利冲 动,等等,无疑可以从价值观念上提供支持。 作为社会分化的产物,经济、政治、法律等不同形式的体制组织构成了人存在的背景与前提:社会的秩序及社会生活的生产与再 生产,都离不开体制的保证。以非人格的形式化结构与运作过程中人的参与为双重规定,体制组织的合理运作既有其形式化的、程序 性的前提,也离不开道德的担保和制衡;而通过参与和制约体制组织的运作过程,道德同时也立足于历史过程本身,从一个方面回应 了真实的存在何以可能这一问题。[42] 五 境界与个体整合 社会的整合、秩序的确立、生活世界与社会体制的合理运行,等等,主要从类的层面,展示了人的存在所以可能的条件;道德作 为上述各个方面的内在担保,同时也在一个维度上,使自身的存在获得了根据。在这里,对道德何以必要或善何以必要这一本源性的 问题的考察,首先基于社会本体论。 人的存在既以类的形式展开,又有其个体的向度;向具体存在或真实存在的回归,同样也有类与个体两重维度。二者当然并非彼 此悬隔,但确乎又有不同的侧重之点,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加以考察。如前所述,布拉德雷曾主要从个体存在之维,提出了如下问题: 为什么我应当是道德的(why I should be moral)?在布拉德雷看来,这一问题应当在自我实现这一层面上来思考,换言之,道德之 所以必要,主要便在于它有助于人的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不过,布拉德雷同时又将自我理解为与实在(reality)相对的现 象,认为自我“除了现象,什么也不是。”[43]与这一观点相应,布拉德雷将自我实现主要理解为“自觉地与无限的大全(infinite whole)融合为一”[44]。这一看法似乎多少将自我消解在整体中。不难看到,尽管布拉德雷将“我为什么应是道德的”与自我实现联系 起来,但对大全、整体的强调,使他并未能真正解决“道德何以必要”与个体存在的关系问题。 以个体的存在为视域,我们似乎应对境界予以必要的关注。从广义上看,境界首先与个体或自我的存在状态相联系;具体而言, 可以从个体存的在统一或自我的整合这一侧面来理解境界。康德曾从认识论的角度,将我思(I think)规定为意识的综合统一,如果 不限于认识论,而从本体论之维考察自我或个体的存在,那么,境界便表现为个体存在的综合统一形态。如后文将进一步论述的,这 里的境界固然与精神领域相联系,但又不限于精神的领域, [45]它形成和展开于历史实践过程,并在实践过程中得到确证;[46]简言 之,境界凝结了个体的全部生活,是基于整个实践过程而达到的个体整合与统一。个体的这种综合统一,从一个方面展示了存在的具 体性;而境界的提升,则相应地意味着不断走向或回归具体的存在。 存在的具体性包含着存在规定的多样性或多方面性,在个体存在这一向度上,亦体现了这一点。作为自我整合与个体统一的形 态,广义的境界同样涉及存在的多方面规定,并以存在规定的多方面实现和完成为其内容。从本体论的层面看,需要的满足是个体存 在的基本前提;存在的多方面性首先也体现在需要的多重性上。大致而言,与身心两重向度相应,个体的需要也主要分别体现于感性 的生命层面和理性的精神层面。在伦理学史上,经验论及各种形式的功利主义较多地关注于人的感性、生命需要,理性主义及道义论 则将理性的精神需要放在更为优先的地位;这种不同的侧重,从一个方面表明,个体的需要并不仅仅限于一端:经验论(以及功利主 义)和理性主义(及道义论)各自把握了需要的一个方面,而他们的问题则在于未能注意需要的多样性。片面注重感性需要,往往很 难使人真正超越自然的规定:在“生之谓性”这一层面,人与自然的存在的区别显然是有限的;理性的需要的过度强调,则容易导致对 感性生命的虚无主义态度,在理学家所谓“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道德评判中,便不难看到这一点:生死涉及的是生命的存在, 守节则表现为一种理性精神的追求,片面突出精神完美的需要,在此引向了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可以看到,需要的合理确认与满足, 离不开道德系统的调节:合理的道德系统内在地包含着对人的感性生命和理性本质的双重确认,惟有从这种感性与理性统一的伦理原 则出发,生命的肯定与精神的追求才能达到和谐的境界,而这种境界同时也表征着存在本身多方面规定的实现。 在个体的存在过程中,需要的满足离不开能力的发展。能力与秉赋不同,秉赋可以成为能力的潜在出发点,但不同于现实的能 力。能力也有别于一般的技艺,技艺主要服务于外在目的,是达到某种外在目的的手段。能力形成于人的存在过程,它既是个体存在 所以可能的条件,又标志着存在所达到的形态或境界;能力的发展状态,同时确证着个体规定的实现程度。个体的能力可以彼此不 同:我们无法强求每一个体都具有同样的能力;但是,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背景发展个体秉赋所提供的潜能,在自足其性的意义 上使之形成为现实的能力,则是个体自我完成的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所谓自足其性,既表明能力的发展不应当无视个体的差异 (不能勉强每一个体都达到划一的目标),也意味着能力是存在的内在规定,不是工具意义上的外在要素:以最基本的劳动的能力而

言,它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作为存在的一种方式,道德与个体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即表现为: 在肯定能力对实践过程(包括作用于外部对象)的意义的同时,又不断超越工其理性的视域,从实质的的层面,确认能力发展对个体 存在的内在价值。 由实质的或价值的视域进一步反观存在的规定,便不能不对人格予以必要的关注。儒家很早就已提出”成己”之学,所谓成己,主 要即指向自我在人格上的完善。作为精神层而相对稳定的结构,人格有多方面的规定和向度,诸如括理性之维、情感之维、意志之维 等等。如果仅仅偏重于其中的某一方面,往往容易引向片面的存在。当理性被界定为人格的至上或唯一规定时,人同时也就被理解为 概念化的的存在或逻辑的化身。朱熹主张以”道心纯一”为人格的理想,而道心则与包含情意的人心相对,表现为纯粹的伦理理性,这 种看法已蕴含者以理性净化存在的要求:康德将道德主体理解为超感性的、完全由实践理性支配的存在,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反 之,以情、意为人格的全部规定,则意味者将人视为非理性的存在,休谟强调”理性是并应该是情感的奴求"T4刀、叔本华对意志及意 欲的突出,即从不同的侧面强化了存在的非理性之维。对人格规定的这种片面侧重,在实践上常常对应于存在的单向度化:扬弃存在 的片面性,则以确认人格的多重性为其前提之一。可以看到,人的多方面发展体现于人格之城,具体便表现为理性、情感、意志等规 定的多向度展开。从早期儒学的人格学说,到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尽管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存在重要差异(马克思的全而发展理 论包含着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洒),但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涉及精神世界的多方而发展:而这种多方而的发展同时也是合理的道德体系 的基本原则所要求的。在这里,同样展示了道德对走向具体存在的意义· 作为精神世界的一个方面,人格已同时涉及境界的另一重内通。如前所述,广义的境界可以理解为在实践中形成的自我整合或个 体的综合统一:境界也可以从狭义的层而加以考察,在这一层面上,境界主要表现为一种意义的世界或意义的视城(meaning o20n)·获义的境界既蕴含了对存在的理解,又凝结者人对自身生存价值的确认,并寄托着人的”在"世理想。与存在与在"的探寻 相联系,境界表现了对世界与人自身的一种精神的把辉,这种把探体现了意识结构不同方而(包括理性与情意等等)的综合统一,又 以实践精神的方式展开。在求真、向善、趋美的过程中,境界展示了人所理解的世界图景,又表征者自我所达到的意义祝域并标志者 其精神升华的不同层面。[48] 以意义世界或意义视域为内容,境界的形成与提升过程总是渗入了广义的人生理想和道德理想的作用。如前所述,个体的在"世 同时也是一个与他人共在的过程,与这一本体论的存在形态相联系,对他人的责任构成了个体存在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方而。儒家将成 己(成就自我)与成人(成就他人)联系起来,要求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成就自己,其中已蕴含了深沉的责任意识:在当代哲学中, 同样可以看到对责任的关注,列维纳斯以责任意识为达到主体性的前提,便表明了这一点。.[49在对他人的尊重、关心、尽责中,我 不再团于”小我”,而获得了更广的存在意义。从境界的层面看,随者责任意识的形成,对他人、对群体、对这个世界履行职责,逐渐 成了我的”分内事”:我的存在之域超出了自身的边界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是意义世界和意义视域的丰富和充实,也是存在境域的 扩展,而意义世界的丰富、充实和存在境域的扩展,又总是件随者境界的提升。责任意识可以看作是以天下为己任等道德理想的具体 体现,在境界的以上提升过程中,不难注意到人生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制钓与范导。 意义世界的更深沉的内通,展开于真、善、美的追求过程之中。这里的真,首先指向对世界与自我的认识,其中既涉及经验领域 的事实,也包括对性与天道等形而上原理的把握。经验领域以达到真实的知识为目标,性与天道则关联者作为具体真理的智慧。[50] 在经验领域的知识与形而上智慧的不断互动中,人们也逐渐地达到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把握:而由此达到的真实世界,同时也表现为本 体论意义上的真实存在(具体存在)。真不仅与广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相联系,而且包含着价值观内酒。从价值观的角度看,真与伪 相对,它既以自我在德性、品格上的实有诸己为内容,又涉及主体间交往过程中的真诚性。以真为面向,对象之真与自我之真彼此交 融,世界的存在(being)与人的在"(existence)统一于真实的意义视域. 相对于真,善更多地涉及价值和评价的领域,究其本源,善首先与人的需要相联系。中国古代哲学曾对善作了如下界说:“可欲 之谓善”(《孟子·尽心下》)·可欲既指值得追求的,也指人的存在所实际需要的:在后一意义上,善意味者通过化自在之物(本然 的对象)为为我之物(合乎人多方面需要的对象),在合理需要的满足过程中,逐渐达到具体的存在。这一过程既包含着人与自然 (或天与人)的关系,又涉及人与人(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等等)的关系,而善的实现,也相应地意味着以动态的形式,不断 达到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统一·从狭义的行为过程看,善则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为内容,“不逾矩是对普遍规范 的自觉遵循,”从心所欲则表明行为出于内在意愿并合平自然,二者的结合具体表现为在自觉、自恩、与自然的统一中,超越强制与 勉强,达到从容中道的境界。 与真、善相互关联的美,在广义上表现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审美意境。合目的性的内在意蕴在于对人的存在价值的确 认(作用于外部对象的过程与社会发展、自我实现的一致),合规律性则意味着对普遍之道的尊重:前者伴随着自然的人化,后者则 蕴含着人的自然化。在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一中,人的本质力量与天地之美相互交融,内化为主体的市类境界,后者又为关 的创造和美的观照提供了内在之源。从另一方面看,美又与人格相联系,所谓人格美,便涉及美的这一向度。孟子在谈到理想人格 时,曾指出:”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苟子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不全不粹不足以为关。”(《苟子·劝学》)“充 实"和“全而粹”,都含有具体性、全面性之意:在此,达到关的境界与走向具体的、全面的存在表现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以真善关的统一为而向,意义世界同时展开为一个价值的体系。在广义的价值创作过程中,真善关的追求与人的存在融合在一 起,并指向人自身的完善。以价值创作和人自身的完善为背景,作为意义世界内容的真善关与自我实现的道德理想形成了互动呼应的 关系。不仅狭义的善,而且真与美,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道德的理想:在知识与智慧的统一中把挥真实的世界、交往中的真诚性原 则、全而粹的完关人格,等等,无不展示了这一点。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上述的人生理想又始终关联着对自由之境的追求。通过知识 与智慧的互动把握真实的世界,为达到自由境界提供了广义的认识论前提:价值创造与自觉、自愿、自然的统一,从不同的侧而表现 了行为的的自由向度:合目的与合规律的一致以及人格上的充实之美,从审美意境与理想人格的角度,展示了在美的创造、美的观照 及培养健全人格中的自由走向。在这里,境界的提升与自由的追求呈现为相关的两个方面
言,它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作为存在的一种方式,道德与个体能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即表现为: 在肯定能力对实践过程(包括作用于外部对象)的意义的同时,又不断超越工具理性的视域,从实质的的层面,确认能力发展对个体 存在的内在价值。 由实质的或价值的视域进一步反观存在的规定,便不能不对人格予以必要的关注。儒家很早就已提出“成己”之学,所谓成己,主 要即指向自我在人格上的完善。作为精神层面相对稳定的结构,人格有多方面的规定和向度,诸如括理性之维、情感之维、意志之维 等等。如果仅仅偏重于其中的某一方面,往往容易引向片面的存在。当理性被界定为人格的至上或唯一规定时,人同时也就被理解为 概念化的的存在或逻辑的化身。朱熹主张以“道心纯一”为人格的理想,而道心则与包含情意的人心相对,表现为纯粹的伦理理性,这 种看法已蕴含着以理性净化存在的要求;康德将道德主体理解为超感性的、完全由实践理性支配的存在,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反 之,以情、意为人格的全部规定,则意味着将人视为非理性的存在,休谟强调“理性是并应该是情感的奴隶”[47]、叔本华对意志及意 欲的突出,即从不同的侧面强化了存在的非理性之维。对人格规定的这种片面侧重,在实践上常常对应于存在的单向度化;扬弃存在 的片面性,则以确认人格的多重性为其前提之一。可以看到,人的多方面发展体现于人格之域,具体便表现为理性、情感、意志等规 定的多向度展开。从早期儒学的人格学说,到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尽管历史的深度和广度存在重要差异(马克思的全面发展理 论包含着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但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涉及精神世界的多方面发展;而这种多方面的发展同时也是合理的道德体系 的基本原则所要求的。在这里,同样展示了道德对走向具体存在的意义。 作为精神世界的一个方面,人格已同时涉及境界的另一重内涵。如前所述,广义的境界可以理解为在实践中形成的自我整合或个 体的综合统一;境界也可以从狭义的层面加以考察,在这一层面上,境界主要表现为一种意义的世界或意义的视域(meaning horizon)。狭义的境界既蕴含了对存在的理解,又凝结着人对自身生存价值的确认,并寄托着人的“在”世理想。与存在与“在”的探寻 相联系,境界表现了对世界与人自身的一种精神的把握,这种把握体现了意识结构不同方面(包括理性与情意等等)的综合统一,又 以实践精神的方式展开。在求真、向善、趋美的过程中,境界展示了人所理解的世界图景,又表征着自我所达到的意义视域并标志着 其精神升华的不同层面。[48] 以意义世界或意义视域为内容,境界的形成与提升过程总是渗入了广义的人生理想和道德理想的作用。如前所述,个体的“在”世 同时也是一个与他人共在的过程,与这一本体论的存在形态相联系,对他人的责任构成了个体存在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方面。儒家将成 己(成就自我)与成人(成就他人)联系起来,要求在成就他人的过程中成就自己,其中已蕴含了深沉的责任意识;在当代哲学中, 同样可以看到对责任的关注,列维纳斯以责任意识为达到主体性的前提,便表明了这一点。[49]在对他人的尊重、关心、尽责中,我 不再囿于“小我”,而获得了更广的存在意义。从境界的层面看,随着责任意识的形成,对他人、对群体、对这个世界履行职责,逐渐 成了我的“分内事”:我的存在之域超出了自身的边界而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是意义世界和意义视域的丰富和充实,也是存在境域的 扩展,而意义世界的丰富、充实和存在境域的扩展,又总是伴随着境界的提升。责任意识可以看作是以天下为己任等道德理想的具体 体现,在境界的以上提升过程中,不难注意到人生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制约与范导。 意义世界的更深沉的内涵,展开于真、善、美的追求过程之中。这里的真,首先指向对世界与自我的认识,其中既涉及经验领域 的事实,也包括对性与天道等形而上原理的把握。经验领域以达到真实的知识为目标,性与天道则关联着作为具体真理的智慧。[50] 在经验领域的知识与形而上智慧的不断互动中,人们也逐渐地达到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把握;而由此达到的真实世界,同时也表现为本 体论意义上的真实存在(具体存在)。真不仅与广义的认识论和本体论相联系,而且包含着价值观内涵。从价值观的角度看,真与伪 相对,它既以自我在德性、品格上的实有诸己为内容,又涉及主体间交往过程中的真诚性。以真为面向,对象之真与自我之真彼此交 融,世界的存在(being)与人的“在”(existence)统一于真实的意义视域。 相对于真,善更多地涉及价值和评价的领域。究其本源,善首先与人的需要相联系。中国古代哲学曾对善作了如下界说:“可欲 之谓善”(《孟子·尽心下》)。可欲既指值得追求的,也指人的存在所实际需要的;在后一意义上,善意味着通过化自在之物(本然 的对象)为为我之物(合乎人多方面需要的对象),在合理需要的满足过程中,逐渐达到具体的存在。这一过程既包含着人与自然 (或天与人)的关系,又涉及人与人(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等等)的关系,而善的实现,也相应地意味着以动态的形式,不断 达到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统一。从狭义的行为过程看,善则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为内容,“不逾矩”是对普遍规范 的自觉遵循,“从心所欲”则表明行为出于内在意愿并合乎自然,二者的结合具体表现为在自觉、自愿、与自然的统一中,超越强制与 勉强,达到从容中道的境界。 与真、善相互关联的美,在广义上表现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审美意境。合目的性的内在意蕴在于对人的存在价值的确 认(作用于外部对象的过程与社会发展、自我实现的一致),合规律性则意味着对普遍之道的尊重;前者伴随着自然的人化,后者则 蕴含着人的自然化。在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统一中,人的本质力量与天地之美相互交融,内化为主体的审美境界,后者又为美 的创造和美的观照提供了内在之源。从另一方面看,美又与人格相联系,所谓人格美,便涉及美的这一向度。孟子在谈到理想人格 时,曾指出:“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下》)荀子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不全不粹不足以为美。”(《荀子·劝学》)“充 实”和“全而粹”,都含有具体性、全面性之意;在此,达到美的境界与走向具体的、全面的存在表现为一个统一的过程。 以真善美的统一为面向,意义世界同时展开为一个价值的体系。在广义的价值创作过程中,真善美的追求与人的存在融合在一 起,并指向人自身的完善。以价值创作和人自身的完善为背景,作为意义世界内容的真善美与自我实现的道德理想形成了互动呼应的 关系。不仅狭义的善,而且真与美,都从不同的方面体现了道德的理想:在知识与智慧的统一中把握真实的世界、交往中的真诚性原 则、全而粹的完美人格,等等,无不展示了这一点。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上述的人生理想又始终关联着对自由之境的追求。通过知识 与智慧的互动把握真实的世界,为达到自由境界提供了广义的认识论前提;价值创造与自觉、自愿、自然的统一,从不同的侧面表现 了行为的的自由向度;合目的与合规律的一致以及人格上的充实之美,从审美意境与理想人格的角度,展示了在美的创造、美的观照 及培养健全人格中的自由走向。在这里,境界的提升与自由的追求呈现为相关的两个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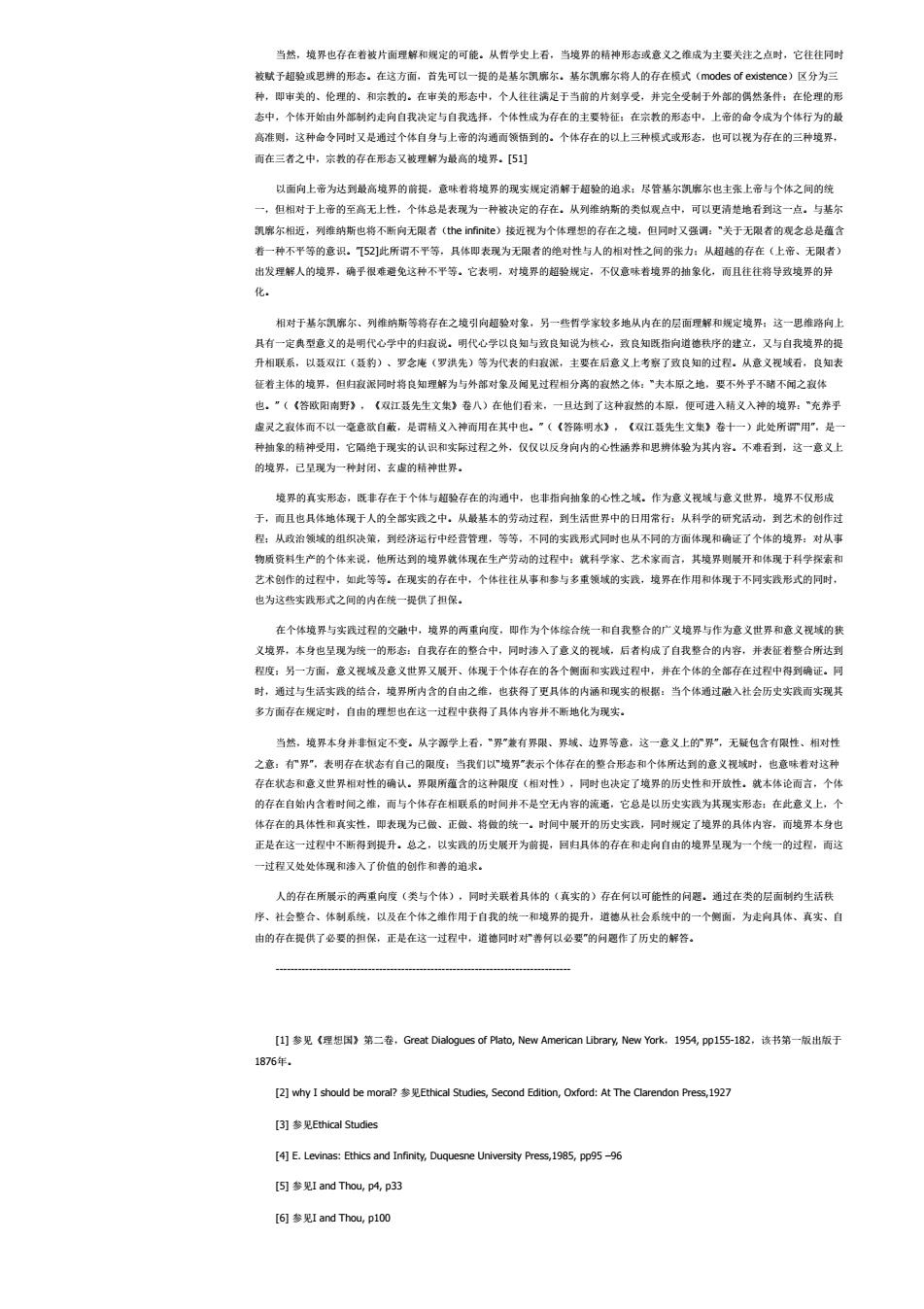
当然,境界也存在着被片面理解和规定的可能。从哲学史上看,当境界的精神形态或意义之维成为主要关注之点时,它往往同时 被赋予超验或思辨的形态。在这方面,首先可以一提的是基尔凯廓尔.基尔凯廓尔将人的存在慎式(modes of existence)区分为三 种,即审美的、伦理的、和宗教的。在审美的形态中,个人往往满足于当前的片刻享受,并完全受制于外部的偶然条件:在伦理的形 态中,个体开始由外部制钓走向自我决定与自我选择,个体性成为存在的主要特征:在宗教的形态中,上帝的命令成为个体行为的最 高准则,这种命令同时又是通过个体自身与上帝的沟通而领悟到的。个体存在的以上三种模式或形态,也可以视为存在的三种境界, 而在三者之中,宗教数的存在形态又被理解为最高的境界。[51] 以而向上帝为达到最高境界的前提,意味者将境界的现实规定消解于超验的追求:尽管基尔凯廓尔也主张上帝与个体之间的统 一,但相对于上帝的至高无上性,个体总是表现为一种被决定的存在,从列维纳斯的类似观点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与基尔 凯廓尔相近,列维纳斯也将不断向无限者(the infinite)接近视为个体理想的存在之境,但同时又强调:"关于无限者的观念总是蕴含 着一种不平等的意识。"T52]此所谓不平等,具体即表现为无限者的绝对性与人的相对性之间的张力:从超越的存在(上帝、无限者) 出发理解人的境界,确乎很难避免这种不平等。它表明,对境界的超验规定,不仅意味者境界的抽象化,而且往往将导致境界的异 化 相对于基尔凯廓尔、列维纳斯等将存在之境引向超验对象,另一些皙学家较多地从内在的层面理解和规定境界:这一思维路向上 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是明代心学中的归寂说。明代心学以良知与致良知说为核心,致良知既指向道德秩序的建立,又与自我境界的提 升相联系,以聂双江(聂豹)、罗念庵(罗洪先)等为代表的归寂派,主要在后意义上考察了致良知的过程。从意义视城看,良知表 征者主体的境界,但归寂派同时将良知理解为与外部对象及闻见过程相分离的寂然之体:”夫本原之地,要不外平不睹不闻之寂体 也。”(《答欧阳南野》,《双江聂先生文集》苍八)在他们看来,一旦达到了这种寂然的本原,便可进入精义入神的境界:"充养乎 虚灵之寂体而不以一毫意放自蔽,是谓精义入神而用在其中也。”(《答陈明水》,《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一)此处所谓用”。是 种抽象的精神受用,它隔绝于现实的认识和实际过程之外,仅仅以反身向内的心性涵养和思辨体验为其内容。不难看到,这一意义上 的境界,已呈现为一种封闭、玄虚的精神世界。 境界的真实形态,既非存在于个体与超验存在的沟通中,也非指向抽象的心性之域。作为意义视域与意义世界,境界不仅形成 于,而且也具体地体现于人的全部实践之中。从最基本的劳动过程,到生活世界中的日用常行:从科学的研究活动,到艺术的创作过 程:从政治领域的组织决策,到经济运行中经营管理,等等,不同的实践形式同时也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和确证了个体的境界:对从事 物质资料生产的个体来说,他所达到的境界就体现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就科学家、艺术家而言,其境界则展开和体现于科学探索和 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如此等等。在现实的存在中,个体往往从事和参与多重领城的实践,境界在作用和体现于不同实骏形式的同时, 也为这些实践形式之间的内在统一提供了担保。 在个体境界与实践过程的交融中,境界的两重向度,即作为个体综合统一和自我整合的广义境界与作为意义世界和意义视域的获 义境界,本身也呈现为统一的形态:自我存在的整合中,同时渗入了意义的视域,后者构成了自我整合的内容,并表征着整合所达到 程度:另一方面,意义视城及意义世界又展开、体现于个体存在的各个侧而和实践过程中,并在个体的全部存在过程中得到确证。同 时,通过与生活实践的结合,境界所内含的自由之维,也获得了更具体的内酒和现实的根据:当个体通过融入社会历史实践而实现其 多方面存在规定时,自由的理想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具体内容并不断地化为现实。 当然,境界本身并非恒定不变。从字源学上看,“界”兼有界限、界域、边界等意,这一意义上的界”,无疑包含有限性、相对性 之意:们界”,表明存在状态有自己的限度:当我们以”境界”表示个体存在的整合形态和个体所达到的意义视城时,也意味着对这种 存在状态和意义世界相对性的确认。界限所蕴含的这种限度(相对性),同时也决定了境界的历史性和开放性。就本体论而言,个体 的存在自始内含着时间之维,而与个体存在相联系的时间并不是空无内容的流适,它总是以历史实践为其现实形态:在此意义上,个 体存在的具体性和真实性,即表现为已做、正做、将做的统一。时间中展开的历史实践,同时规定了境界的具体内容,而境界本身也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提升·总之,以实践的历史展开为前提,回归具体的存在和走向自由的境界呈现为一个统一的过程,而这 一过程又处处体现和渗入了价值的创作和善的追求。 人的存在所展示的两重向度(类与个体),同时关联着具体的(真实的)存在何以可能性的问避。通过在类的层面制钓生活秩 序、社会整合、体制系统,以及在个体之维作用于自我的统一和境界的提升。道德从社会系统中的一个侧面,为走向具体、真实、自 由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担保,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道德同时对”善何以必要"的问题作了历史的解答。 [1]参见《理想国》第二卷,Great Dialogues of Plato,New American Library%New York,1954,Pp155-182,该书第一版出版于 1876年. [2]why I should be moral?Ethical Studies,Second Edition,Oxford:At The Clarendon Press,1927 [3]参见Ethical Studies [4]E.Levinas:Ethics and Infinity,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85,pp95-96 [5参见I and Thou,p4,p33 [6)参见and Thou,pl00
当然,境界也存在着被片面理解和规定的可能。从哲学史上看,当境界的精神形态或意义之维成为主要关注之点时,它往往同时 被赋予超验或思辨的形态。在这方面,首先可以一提的是基尔凯廓尔。基尔凯廓尔将人的存在模式(modes of existence)区分为三 种,即审美的、伦理的、和宗教的。在审美的形态中,个人往往满足于当前的片刻享受,并完全受制于外部的偶然条件;在伦理的形 态中,个体开始由外部制约走向自我决定与自我选择,个体性成为存在的主要特征;在宗教的形态中,上帝的命令成为个体行为的最 高准则,这种命令同时又是通过个体自身与上帝的沟通而领悟到的。个体存在的以上三种模式或形态,也可以视为存在的三种境界, 而在三者之中,宗教的存在形态又被理解为最高的境界。[51] 以面向上帝为达到最高境界的前提,意味着将境界的现实规定消解于超验的追求;尽管基尔凯廓尔也主张上帝与个体之间的统 一,但相对于上帝的至高无上性,个体总是表现为一种被决定的存在。从列维纳斯的类似观点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与基尔 凯廓尔相近,列维纳斯也将不断向无限者(the infinite)接近视为个体理想的存在之境,但同时又强调:“关于无限者的观念总是蕴含 着一种不平等的意识。”[52]此所谓不平等,具体即表现为无限者的绝对性与人的相对性之间的张力;从超越的存在(上帝、无限者) 出发理解人的境界,确乎很难避免这种不平等。它表明,对境界的超验规定,不仅意味着境界的抽象化,而且往往将导致境界的异 化。 相对于基尔凯廓尔、列维纳斯等将存在之境引向超验对象,另一些哲学家较多地从内在的层面理解和规定境界;这一思维路向上 具有一定典型意义的是明代心学中的归寂说。明代心学以良知与致良知说为核心,致良知既指向道德秩序的建立,又与自我境界的提 升相联系,以聂双江(聂豹)、罗念庵(罗洪先)等为代表的归寂派,主要在后意义上考察了致良知的过程。从意义视域看,良知表 征着主体的境界,但归寂派同时将良知理解为与外部对象及闻见过程相分离的寂然之体:“夫本原之地,要不外乎不睹不闻之寂体 也。”(《答欧阳南野》,《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八)在他们看来,一旦达到了这种寂然的本原,便可进入精义入神的境界:“充养乎 虚灵之寂体而不以一毫意欲自蔽,是谓精义入神而用在其中也。”(《答陈明水》,《双江聂先生文集》卷十一)此处所谓“用”,是一 种抽象的精神受用,它隔绝于现实的认识和实际过程之外,仅仅以反身向内的心性涵养和思辨体验为其内容。不难看到,这一意义上 的境界,已呈现为一种封闭、玄虚的精神世界。 境界的真实形态,既非存在于个体与超验存在的沟通中,也非指向抽象的心性之域。作为意义视域与意义世界,境界不仅形成 于,而且也具体地体现于人的全部实践之中。从最基本的劳动过程,到生活世界中的日用常行;从科学的研究活动,到艺术的创作过 程;从政治领域的组织决策,到经济运行中经营管理,等等,不同的实践形式同时也从不同的方面体现和确证了个体的境界:对从事 物质资料生产的个体来说,他所达到的境界就体现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就科学家、艺术家而言,其境界则展开和体现于科学探索和 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如此等等。在现实的存在中,个体往往从事和参与多重领域的实践,境界在作用和体现于不同实践形式的同时, 也为这些实践形式之间的内在统一提供了担保。 在个体境界与实践过程的交融中,境界的两重向度,即作为个体综合统一和自我整合的广义境界与作为意义世界和意义视域的狭 义境界,本身也呈现为统一的形态:自我存在的整合中,同时渗入了意义的视域,后者构成了自我整合的内容,并表征着整合所达到 程度;另一方面,意义视域及意义世界又展开、体现于个体存在的各个侧面和实践过程中,并在个体的全部存在过程中得到确证。同 时,通过与生活实践的结合,境界所内含的自由之维,也获得了更具体的内涵和现实的根据:当个体通过融入社会历史实践而实现其 多方面存在规定时,自由的理想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具体内容并不断地化为现实。 当然,境界本身并非恒定不变。从字源学上看,“界”兼有界限、界域、边界等意,这一意义上的“界”,无疑包含有限性、相对性 之意:有“界”,表明存在状态有自己的限度;当我们以“境界”表示个体存在的整合形态和个体所达到的意义视域时,也意味着对这种 存在状态和意义世界相对性的确认。界限所蕴含的这种限度(相对性),同时也决定了境界的历史性和开放性。就本体论而言,个体 的存在自始内含着时间之维,而与个体存在相联系的时间并不是空无内容的流逝,它总是以历史实践为其现实形态;在此意义上,个 体存在的具体性和真实性,即表现为已做、正做、将做的统一。时间中展开的历史实践,同时规定了境界的具体内容,而境界本身也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得到提升。总之,以实践的历史展开为前提,回归具体的存在和走向自由的境界呈现为一个统一的过程,而这 一过程又处处体现和渗入了价值的创作和善的追求。 人的存在所展示的两重向度(类与个体),同时关联着具体的(真实的)存在何以可能性的问题。通过在类的层面制约生活秩 序、社会整合、体制系统,以及在个体之维作用于自我的统一和境界的提升,道德从社会系统中的一个侧面,为走向具体、真实、自 由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担保,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道德同时对“善何以必要”的问题作了历史的解答。 -------------------------------------------------------------------------------- [1] 参见《理想国》第二卷,Great Dialogues of Plato, New American Library, New York,1954, pp155-182,该书第一版出版于 1876年。 [2] why I should be moral? 参见Ethical Studies, Second Edition,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1927 [3] 参见Ethical Studies [4] E. Levinas: Ethics and Infinity,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1985, pp95 –96 [5] 参见I and Thou, p4, p33 [6] 参见I and Thou, p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