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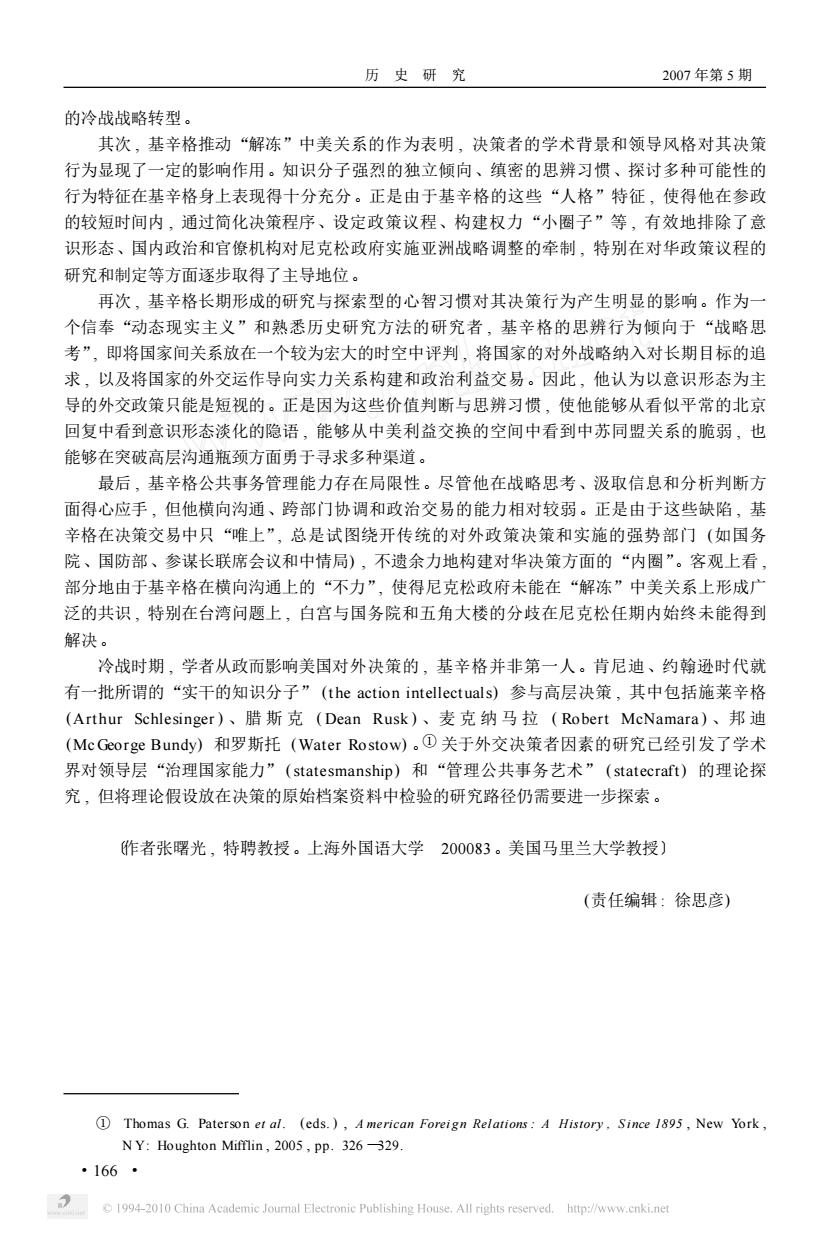
历史研究 2007年第5期 的冷战战略转型。 其次,基辛格推动“解冻”中美关系的作为表明,决策者的学术背景和领导风格对其决策 行为显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知识分子强烈的独立倾向、缜密的思辨习惯、探讨多种可能性的 行为特征在基辛格身上表现得十分充分。正是由于基辛格的这些“人格”特征,使得他在参政 的较短时间内,通过简化决策程序、设定政策议程、构建权力“小圈子”等,有效地排除了意 识形态、国内政治和官僚机构对尼克松政府实施亚洲战略调整的牵制,特别在对华政策议程的 研究和制定等方面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 再次,基辛格长期形成的研究与探索型的心智习惯对其决策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作为一 个信奉“动态现实主义”和熟悉历史研究方法的研究者,基辛格的思辨行为倾向于“战略思 考”,即将国家间关系放在一个较为宏大的时空中评判,将国家的对外战略纳入对长期目标的追 求,以及将国家的外交运作导向实力关系构建和政治利益交易。因此,他认为以意识形态为主 导的外交政策只能是短视的。正是因为这些价值判断与思辨习惯,使他能够从看似平常的北京 回复中看到意识形态淡化的隐语,能够从中美利益交换的空间中看到中苏同盟关系的脆弱,也 能够在突破高层沟通瓶颈方面勇于寻求多种渠道。 最后,基辛格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存在局限性。尽管他在战略思考、汲取信息和分析判断方 面得心应手,但他横向沟通、跨部门协调和政治交易的能力相对较弱。正是由于这些缺陷,基 辛格在决策交易中只“唯上”,总是试图绕开传统的对外政策决策和实施的强势部门(如国务 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情局),不遗余力地构建对华决策方面的“内圈”。客观上看, 部分地由于基辛格在横向沟通上的“不力”,使得尼克松政府未能在“解冻”中美关系上形成广 泛的共识,特别在台湾问题上,白宫与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分歧在尼克松任期内始终未能得到 解决。 冷战时期,学者从政而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基辛格并非第一人。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就 有一批所谓的“实干的知识分子”(the action intellectuals))参与高层决策,其中包括施莱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腊斯克(Dean Rusk)、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邦迪 (Mc George Bundy))和罗斯托(Water Rostow)。①关于外交决策者因素的研究己经引发了学术 界对领导层“治理国家能力”(statesmanship)和“管理公共事务艺术”(statecraft)的理论探 究,但将理论假设放在决策的原始档案资料中检验的研究路径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作者张曙光,特聘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200083。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徐思彦) 1 Thomas G.Paterson et al.(eds.),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A History.Since 1895,New York, NY:Houghton Mifflin,2005,pp.326-329. ·166=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的冷战战略转型。 其次 , 基辛格推动“解冻”中美关系的作为表明 , 决策者的学术背景和领导风格对其决策 行为显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知识分子强烈的独立倾向、缜密的思辨习惯、探讨多种可能性的 行为特征在基辛格身上表现得十分充分。正是由于基辛格的这些“人格”特征 , 使得他在参政 的较短时间内 , 通过简化决策程序、设定政策议程、构建权力“小圈子”等 , 有效地排除了意 识形态、国内政治和官僚机构对尼克松政府实施亚洲战略调整的牵制 , 特别在对华政策议程的 研究和制定等方面逐步取得了主导地位。 再次 , 基辛格长期形成的研究与探索型的心智习惯对其决策行为产生明显的影响。作为一 个信奉“动态现实主义”和熟悉历史研究方法的研究者 , 基辛格的思辨行为倾向于 “战略思 考”, 即将国家间关系放在一个较为宏大的时空中评判 , 将国家的对外战略纳入对长期目标的追 求 , 以及将国家的外交运作导向实力关系构建和政治利益交易。因此 , 他认为以意识形态为主 导的外交政策只能是短视的。正是因为这些价值判断与思辨习惯 , 使他能够从看似平常的北京 回复中看到意识形态淡化的隐语 , 能够从中美利益交换的空间中看到中苏同盟关系的脆弱 , 也 能够在突破高层沟通瓶颈方面勇于寻求多种渠道。 最后 , 基辛格公共事务管理能力存在局限性。尽管他在战略思考、汲取信息和分析判断方 面得心应手 , 但他横向沟通、跨部门协调和政治交易的能力相对较弱。正是由于这些缺陷 , 基 辛格在决策交易中只“唯上”, 总是试图绕开传统的对外政策决策和实施的强势部门 (如国务 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中情局) , 不遗余力地构建对华决策方面的“内圈”。客观上看 , 部分地由于基辛格在横向沟通上的“不力”, 使得尼克松政府未能在“解冻”中美关系上形成广 泛的共识 , 特别在台湾问题上 , 白宫与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分歧在尼克松任期内始终未能得到 解决。 冷战时期 , 学者从政而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 , 基辛格并非第一人。肯尼迪、约翰逊时代就 有一批所谓的“实干的知识分子” (t he action intellectuals) 参与高层决策 , 其中包括施莱辛格 (Art hur Schlesinger ) 、腊 斯 克 ( Dean Rusk ) 、麦 克 纳 马 拉 ( Robert McNamara ) 、邦 迪 (Mc George Bundy) 和罗斯托 (Water Rostow) 。① 关于外交决策者因素的研究已经引发了学术 界对领导层“治理国家能力” (statesmanship) 和“管理公共事务艺术” (statecraft) 的理论探 究 , 但将理论假设放在决策的原始档案资料中检验的研究路径仍需要进一步探索。 〔作者张曙光 , 特聘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083。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 : 徐思彦) ·166 · 历 史 研 究 2007 年第 5 期 ① Thomas G. Paterson et al. (eds. ) , A merican Forei gn Relations : A History , S ince 1895 , New York , N Y: Houghton Mifflin , 2005 , pp. 326 —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