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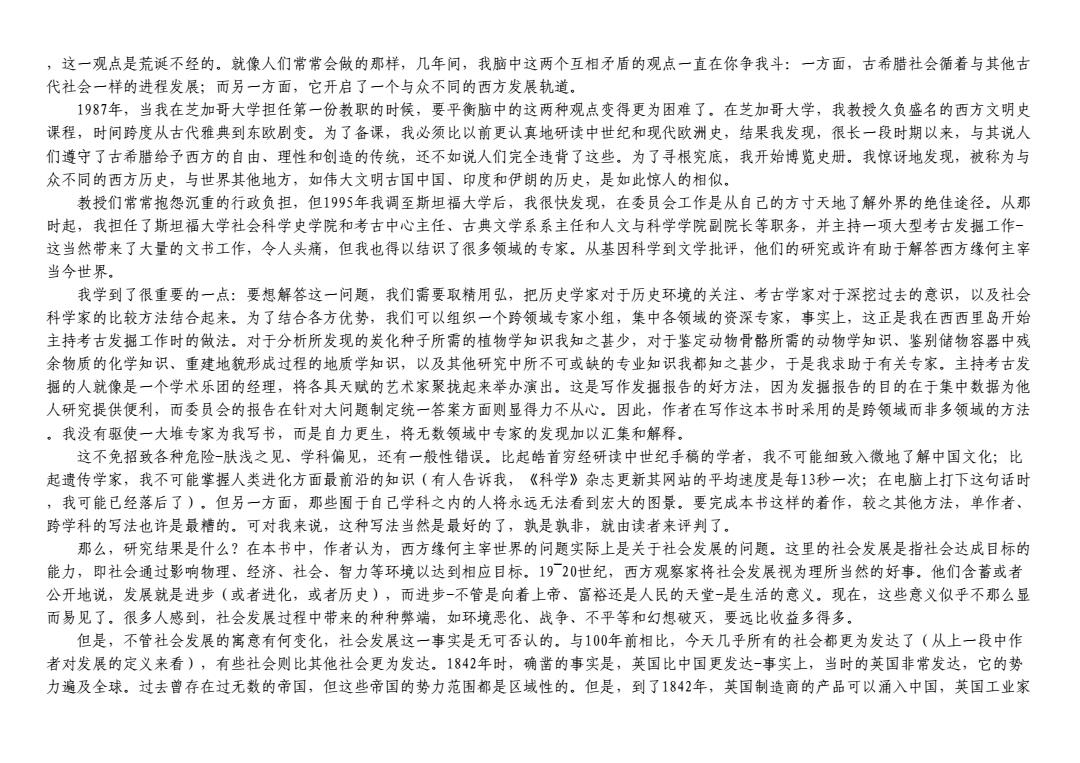
,这一观点是荒诞不经的。就像人们常常会做的那样,几年间,我脑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一直在你争我斗:一方面,古希腊社会循着与其他古 代社会一样的进程发展;而另一方面,它开启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西方发展轨道。 1987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第一份教职的时侯,要平衡脑中的这两种观点变得更为困难了。在芝加哥大学,我教授久负盛名的西方文明史 课程,时间跨度从古代雅典到东欧剧变。为了备课,我必须比以前更认真地研读中世纪和现代欧洲史,结果我发现,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与其说人 们遵守了古希腊给予西方的自由、理性和创造的传统,还不如说人们完全违背了这些。为了寻根究底,我开始博览史册。我惊讶地发现,被称为与 众不同的西方历史,与世界其他地方,如伟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教授们常常抱怨沉重的行政负担,但1995年我调至斯坦福大学后,我很快发现,在委员会工作是从自己的方寸天地了解外界的绝佳途径。从那 时起,我担任了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史学院和考古中心主任、古典文学系系主任和人文与科学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并主持一项大型考古发掘工作- 这当然带来了大量的文书工作,令人头痛,但我也得以结识了很多领域的专家。从基因科学到文学批评,他们的研究或许有助于解答西方缘何主宰 当今世界。 我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要想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取精用弘,把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环境的关注、考古学家对于深挖过去的意识,以及社会 科学家的比较方法结合起来。为了结合各方优势,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跨领域专家小组,集中各领域的资深专家,事实上,这正是我在西西里岛开始 主持考古发掘工作时的做法。对于分析所发现的炭化种子所需的植物学知识我知之甚少,对于鉴定动物骨骼所需的动物学知识、鉴别储物容器中残 余物质的化学知识、重建地貌形成过程的地质学知识,以及其他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我都知之甚少,于是我求助于有关专家。主持考古发 掘的人就像是一个学术乐团的经理,将各具天赋的艺术家聚拢起来举办演出。这是写作发掘报告的好方法,因为发掘报告的目的在于集中数据为他 人研究提供便利,而委员会的报告在针对大问题制定统一答案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采用的是跨领域而非多领域的方法 。我没有驱使一大堆专家为我写书,而是自力更生,将无数领域中专家的发现加以汇集和解释。 这不免招致各种危险-肤浅之见、学科偏见,还有一般性错误。比起皓首穷经研读中世纪手稿的学者,我不可能细致入微地了解中国文化;比 起遗传学家,我不可能掌握人类进化方面最前沿的知识(有人告诉我,《科学》杂志更新其网站的平均速度是每13秒一次;在电脑上打下这句话时 ,我可能已经落后了)。但另一方面,那些囿于自己学科之内的人将永远无法看到宏大的图景。要完成本书这样的着作,较之其他方法,单作者、 跨学科的写法也许是最槽的。可对我来说,这种写法当然是最好的了,孰是孰非,就由读者来评判了。 那么,研究结果是什么?在本书中,作者认为,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这里的社会发展是指社会达成目标的 能力,即社会通过影响物理、经济、社会、智力等环境以达到相应目标。19ˉ20世纪,西方观察家将社会发展视为理所当然的好事。他们含蓄或者 公开地说,发展就是进步(或者进化,或者历史),而进步-不管是向着上帝、富裕还是人民的天堂-是生活的意义。现在,这些意义似乎不那么显 而易见了。很多人感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弊端,如环境恶化、战争、不平等和幻想破灭,要远比收益多得多。 但是,不管社会发展的寓意有何变化,社会发展这一事实是无可否认的。与100年前相比,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更为发达了(从上一段中作 者对发展的定义来看),有些社会则比其他社会更为发达。1842年时,确凿的事实是,英国比中国更发达-事实上,当时的英国非常发达,它的势 力遍及全球。过去曾存在过无数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势力范围都是区域性的。但是,到了1842年,英国制造商的产品可以涌入中国,英国工业家,这一观点是荒诞不经的。就像人们常常会做的那样,几年间,我脑中这两个互相矛盾的观点一直在你争我斗:一方面,古希腊社会循着与其他古 代社会一样的进程发展;而另一方面,它开启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西方发展轨道。 1987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第一份教职的时候,要平衡脑中的这两种观点变得更为困难了。在芝加哥大学,我教授久负盛名的西方文明史 课程,时间跨度从古代雅典到东欧剧变。为了备课,我必须比以前更认真地研读中世纪和现代欧洲史,结果我发现,很长一段时期以来,与其说人 们遵守了古希腊给予西方的自由、理性和创造的传统,还不如说人们完全违背了这些。为了寻根究底,我开始博览史册。我惊讶地发现,被称为与 众不同的西方历史,与世界其他地方,如伟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和伊朗的历史,是如此惊人的相似。 教授们常常抱怨沉重的行政负担,但1995年我调至斯坦福大学后,我很快发现,在委员会工作是从自己的方寸天地了解外界的绝佳途径。从那 时起,我担任了斯坦福大学社会科学史学院和考古中心主任、古典文学系系主任和人文与科学学院副院长等职务,并主持一项大型考古发掘工作- 这当然带来了大量的文书工作,令人头痛,但我也得以结识了很多领域的专家。从基因科学到文学批评,他们的研究或许有助于解答西方缘何主宰 当今世界。 我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要想解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取精用弘,把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环境的关注、考古学家对于深挖过去的意识,以及社会 科学家的比较方法结合起来。为了结合各方优势,我们可以组织一个跨领域专家小组,集中各领域的资深专家,事实上,这正是我在西西里岛开始 主持考古发掘工作时的做法。对于分析所发现的炭化种子所需的植物学知识我知之甚少,对于鉴定动物骨骼所需的动物学知识、鉴别储物容器中残 余物质的化学知识、重建地貌形成过程的地质学知识,以及其他研究中所不可或缺的专业知识我都知之甚少,于是我求助于有关专家。主持考古发 掘的人就像是一个学术乐团的经理,将各具天赋的艺术家聚拢起来举办演出。这是写作发掘报告的好方法,因为发掘报告的目的在于集中数据为他 人研究提供便利,而委员会的报告在针对大问题制定统一答案方面则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作者在写作这本书时采用的是跨领域而非多领域的方法 。我没有驱使一大堆专家为我写书,而是自力更生,将无数领域中专家的发现加以汇集和解释。 这不免招致各种危险-肤浅之见、学科偏见,还有一般性错误。比起皓首穷经研读中世纪手稿的学者,我不可能细致入微地了解中国文化;比 起遗传学家,我不可能掌握人类进化方面最前沿的知识(有人告诉我,《科学》杂志更新其网站的平均速度是每13秒一次;在电脑上打下这句话时 ,我可能已经落后了)。但另一方面,那些囿于自己学科之内的人将永远无法看到宏大的图景。要完成本书这样的着作,较之其他方法,单作者、 跨学科的写法也许是最糟的。可对我来说,这种写法当然是最好的了,孰是孰非,就由读者来评判了。 那么,研究结果是什么?在本书中,作者认为,西方缘何主宰世界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社会发展的问题。这里的社会发展是指社会达成目标的 能力,即社会通过影响物理、经济、社会、智力等环境以达到相应目标。19~20世纪,西方观察家将社会发展视为理所当然的好事。他们含蓄或者 公开地说,发展就是进步(或者进化,或者历史),而进步-不管是向着上帝、富裕还是人民的天堂-是生活的意义。现在,这些意义似乎不那么显 而易见了。很多人感到,社会发展过程中带来的种种弊端,如环境恶化、战争、不平等和幻想破灭,要远比收益多得多。 但是,不管社会发展的寓意有何变化,社会发展这一事实是无可否认的。与100年前相比,今天几乎所有的社会都更为发达了(从上一段中作 者对发展的定义来看),有些社会则比其他社会更为发达。1842年时,确凿的事实是,英国比中国更发达-事实上,当时的英国非常发达,它的势 力遍及全球。过去曾存在过无数的帝国,但这些帝国的势力范围都是区域性的。但是,到了1842年,英国制造商的产品可以涌入中国,英国工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