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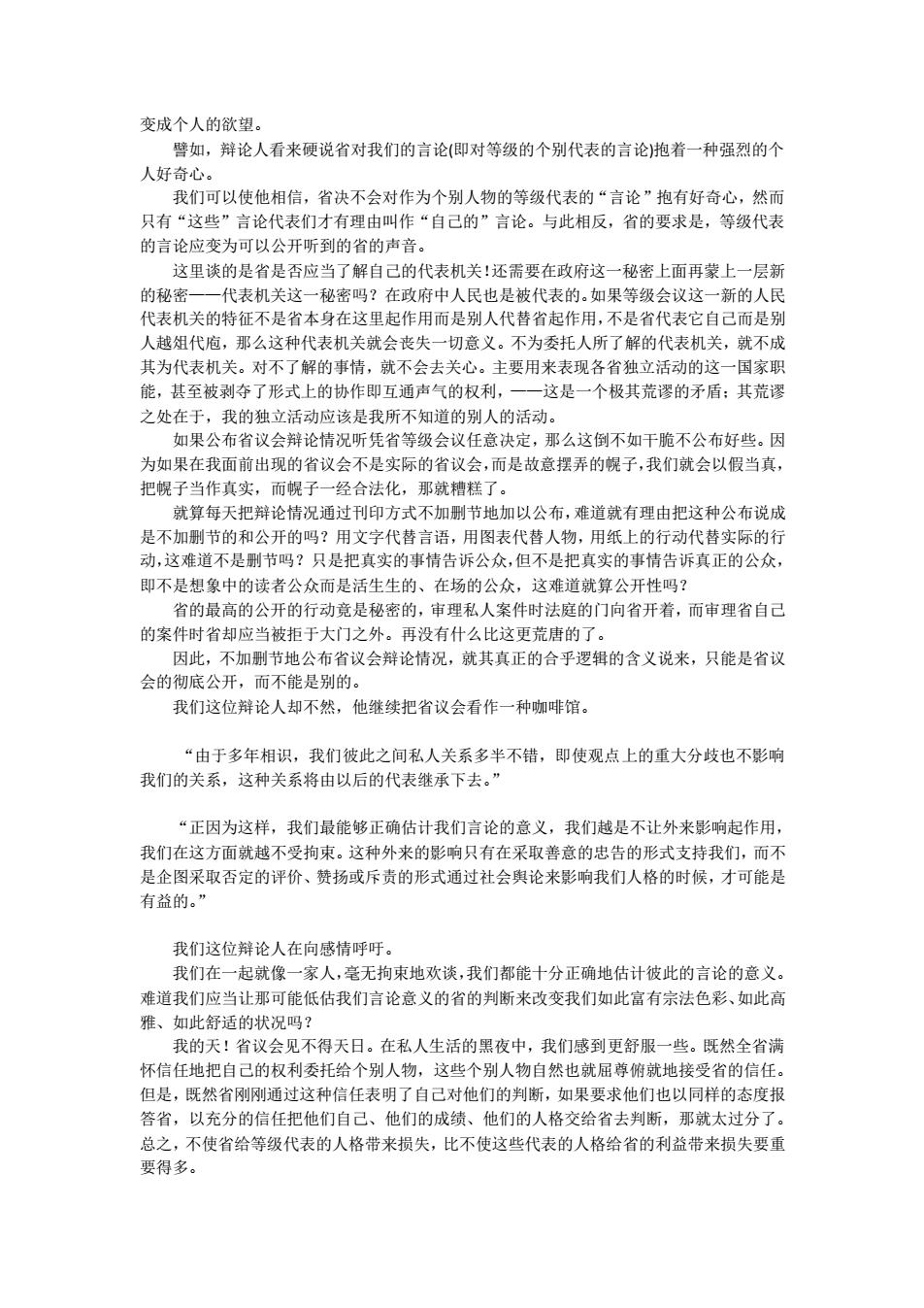
变成个人的欲望。 譬如,辩论人看来硬说省对我们的言论(即对等级的个别代表的言论)抱着一种强烈的个 人好奇心。 我们可以使他相信,省决不会对作为个别人物的等级代表的“言论”抱有好奇心,然而 只有“这些”言论代表们才有理由叫作“自己的”言论。与此相反,省的要求是,等级代表 的言论应变为可以公开听到的省的声音。 这里谈的是省是否应当了解自己的代表机关!还需要在政府这一秘密上面再蒙上一层新 的秘密一一代表机关这一秘密吗?在政府中人民也是被代表的。如果等级会议这一新的人民 代表机关的特征不是省本身在这里起作用而是别人代替省起作用,不是省代表它自己而是别 人越俎代庖,那么这种代表机关就会丧失一切意义。不为委托人所了解的代表机关,就不成 其为代表机关。对不了解的事情,就不会去关心。主要用来表现各省独立活动的这一国家职 能,甚至被剥夺了形式上的协作即互通声气的权利,一一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矛盾:其荒谬 之处在于,我的独立活动应该是我所不知道的别人的活动。 如果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听凭省等级会议任意决定,那么这倒不如干脆不公布好些。因 为如果在我面前出现的省议会不是实际的省议会,而是故意摆弄的幌子,我们就会以假当真, 把幌子当作真实,而幌子一经合法化,那就糟糕了。 就算每天把辩论情况通过刊印方式不加删节地加以公布,难道就有理由把这种公布说成 是不加删节的和公开的吗?用文字代替言语,用图表代替人物,用纸上的行动代替实际的行 动,这难道不是删节吗?只是把真实的事情告诉公众,但不是把真实的事情告诉真正的公众, 即不是想象中的读者公众而是活生生的、在场的公众,这难道就算公开性吗? 省的最高的公开的行动竟是秘密的,审理私人案件时法庭的门向省开着,而审理省自己 的案件时省却应当被拒于大门之外。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了。 因此,不加删节地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就其真正的合乎逻辑的含义说来,只能是省议 会的彻底公开,而不能是别的。 我们这位辩论人却不然,他继续把省议会看作一种咖啡馆。 “由于多年相识,我们彼此之间私人关系多半不错,即使观点上的重大分歧也不影响 我们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由以后的代表继承下去。” “正因为这样,我们最能够正确估计我们言论的意义,我们越是不让外来影响起作用, 我们在这方面就越不受拘束。这种外来的影响只有在采取善意的忠告的形式支持我们,而不 是企图采取否定的评价、赞扬或斥责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来影响我们人格的时候,才可能是 有益的。” 我们这位辩论人在向感情呼吁。 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毫无拘束地欢谈,我们都能十分正确地估计彼此的言论的意义。 难道我们应当让那可能低估我们言论意义的省的判断来改变我们如此富有宗法色彩、如此高 雅、如此舒适的状况吗? 我的天!省议会见不得天日。在私人生活的黑夜中,我们感到更舒服一些。既然全省满 怀信任地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个别人物,这些个别人物自然也就屈尊俯就地接受省的信任。 但是,既然省刚刚通过这种信任表明了自己对他们的判断,如果要求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报 答省,以充分的信任把他们自己、他们的成绩、他们的人格交给省去判断,那就太过分了。 总之,不使省给等级代表的人格带来损失,比不使这些代表的人格给省的利益带来损失要重 要得多。变成个人的欲望。 譬如,辩论人看来硬说省对我们的言论(即对等级的个别代表的言论)抱着一种强烈的个 人好奇心。 我们可以使他相信,省决不会对作为个别人物的等级代表的“言论”抱有好奇心,然而 只有“这些”言论代表们才有理由叫作“自己的”言论。与此相反,省的要求是,等级代表 的言论应变为可以公开听到的省的声音。 这里谈的是省是否应当了解自己的代表机关!还需要在政府这一秘密上面再蒙上一层新 的秘密——代表机关这一秘密吗?在政府中人民也是被代表的。如果等级会议这一新的人民 代表机关的特征不是省本身在这里起作用而是别人代替省起作用,不是省代表它自己而是别 人越俎代庖,那么这种代表机关就会丧失一切意义。不为委托人所了解的代表机关,就不成 其为代表机关。对不了解的事情,就不会去关心。主要用来表现各省独立活动的这一国家职 能,甚至被剥夺了形式上的协作即互通声气的权利,——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矛盾;其荒谬 之处在于,我的独立活动应该是我所不知道的别人的活动。 如果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听凭省等级会议任意决定,那么这倒不如干脆不公布好些。因 为如果在我面前出现的省议会不是实际的省议会,而是故意摆弄的幌子,我们就会以假当真, 把幌子当作真实,而幌子一经合法化,那就糟糕了。 就算每天把辩论情况通过刊印方式不加删节地加以公布,难道就有理由把这种公布说成 是不加删节的和公开的吗?用文字代替言语,用图表代替人物,用纸上的行动代替实际的行 动,这难道不是删节吗?只是把真实的事情告诉公众,但不是把真实的事情告诉真正的公众, 即不是想象中的读者公众而是活生生的、在场的公众,这难道就算公开性吗? 省的最高的公开的行动竟是秘密的,审理私人案件时法庭的门向省开着,而审理省自己 的案件时省却应当被拒于大门之外。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了。 因此,不加删节地公布省议会辩论情况,就其真正的合乎逻辑的含义说来,只能是省议 会的彻底公开,而不能是别的。 我们这位辩论人却不然,他继续把省议会看作一种咖啡馆。 “由于多年相识,我们彼此之间私人关系多半不错,即使观点上的重大分歧也不影响 我们的关系,这种关系将由以后的代表继承下去。” “正因为这样,我们最能够正确估计我们言论的意义,我们越是不让外来影响起作用, 我们在这方面就越不受拘束。这种外来的影响只有在采取善意的忠告的形式支持我们,而不 是企图采取否定的评价、赞扬或斥责的形式通过社会舆论来影响我们人格的时候,才可能是 有益的。” 我们这位辩论人在向感情呼吁。 我们在一起就像一家人,毫无拘束地欢谈,我们都能十分正确地估计彼此的言论的意义。 难道我们应当让那可能低估我们言论意义的省的判断来改变我们如此富有宗法色彩、如此高 雅、如此舒适的状况吗? 我的天!省议会见不得天日。在私人生活的黑夜中,我们感到更舒服一些。既然全省满 怀信任地把自己的权利委托给个别人物,这些个别人物自然也就屈尊俯就地接受省的信任。 但是,既然省刚刚通过这种信任表明了自己对他们的判断,如果要求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报 答省,以充分的信任把他们自己、他们的成绩、他们的人格交给省去判断,那就太过分了。 总之,不使省给等级代表的人格带来损失,比不使这些代表的人格给省的利益带来损失要重 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