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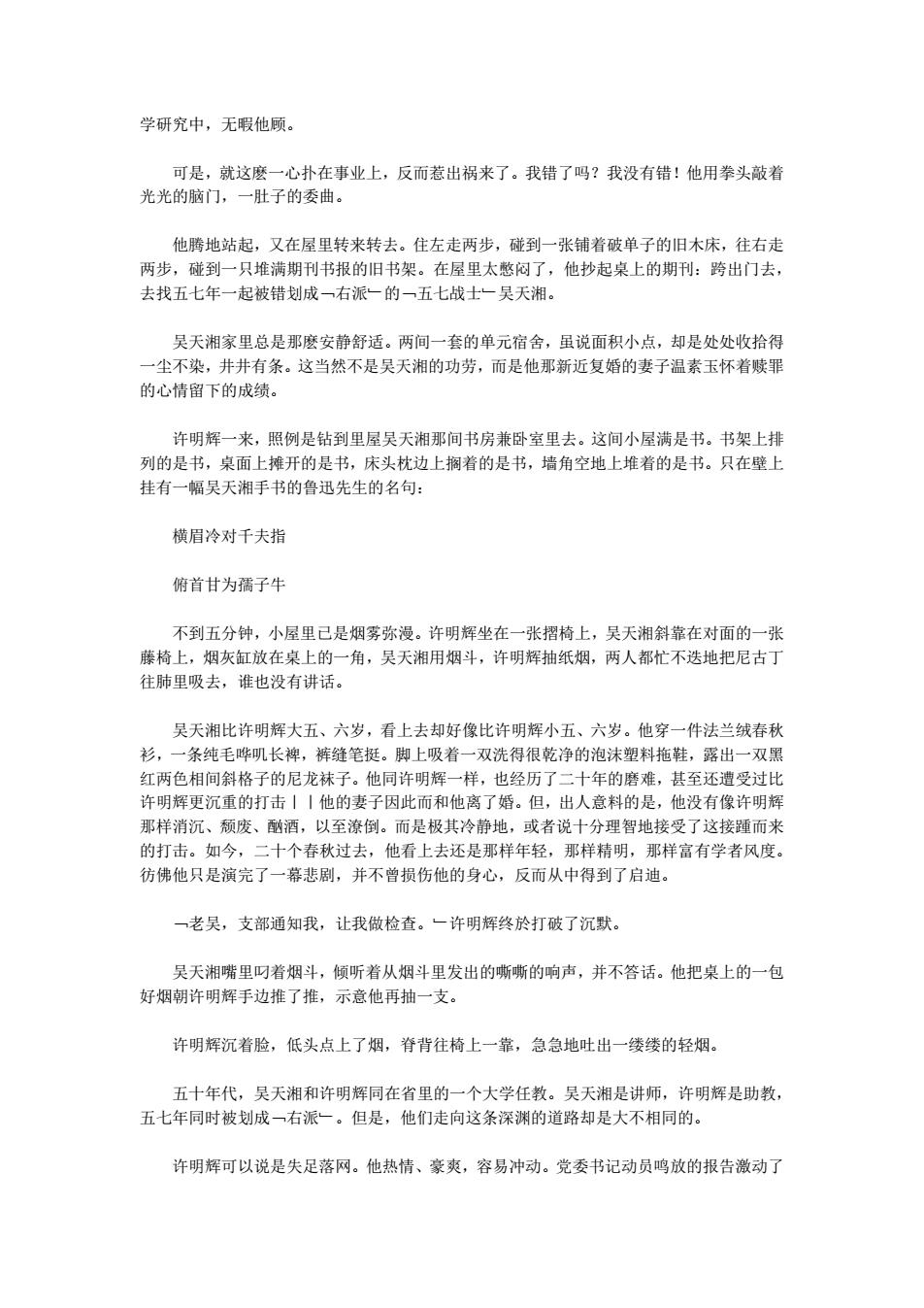
学研究中,无暇他顾。 可是,就这麽一心扑在事业上,反而惹出祸来了。我错了吗?我没有错!他用拳头敲着 光光的脑门,一肚子的委曲。 他腾地站起,又在屋里转来转去。住左走两步,碰到一张铺着破单子的旧木床,往右走 两步,碰到一只堆满期刊书报的旧书架。在屋里太憋闷了,他抄起桌上的期刊:跨出门去, 去找五七年一起被错划成一右派一的一五七战士一吴天湘。 吴天湘家里总是那麽安静舒适。两间一套的单元宿舍,虽说面积小点,却是处处收拾得 尘不染,井井有条。这当然不是吴天湘的功劳,而是他那新近复婚的妻子温素玉怀着赎罪 的心情留下的成绩。 许明辉一来,照例是钻到里屋吴天湘那间书房兼卧室里去。这间小屋满是书。书架上排 列的是书,桌面上摊开的是书,床头枕边上搁着的是书,墙角空地上堆着的是书。只在壁上 挂有一幅吴天湘手书的鲁迅先生的名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不到五分钟,小屋里已是烟雾弥漫。许明辉坐在一张摺椅上,吴天湘斜靠在对面的一张 藤椅上,烟灰缸放在桌上的一角,吴天湘用烟斗,许明辉抽纸烟,两人都忙不迭地把尼古丁 往肺里吸去,谁也没有讲话。 吴天湘比许明辉大五、六岁,看上去却好像比许明辉小五、六岁。他穿一件法兰绒春秋 衫,一条纯毛哗叽长裨,裤缝笔挺。脚上吸着一双洗得很乾净的泡沫塑料拖鞋,露出一双黑 红两色相间斜格子的尼龙袜子。他同许明辉一样,也经历了二十年的磨难,甚至还遭受过比 许明辉更沉重的打击丨他的妻子因此而和他离了婚。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像许明辉 那样消沉、颓废、酗酒,以至潦倒。而是极其冷静地,或者说十分理智地接受了这接踵而来 的打击。如今,二十个春秋过去,他看上去还是那样年轻,那样精明,那样富有学者风度。 彷佛他只是演完了一幕悲剧,并不曾损伤他的身心,反而从中得到了启迪。 一老吴,支部通知我,让我做检查。一许明辉终於打破了沉默。 吴天湘嘴里叼着烟斗,倾听着从烟斗里发出的嘶嘶的响声,并不答话。他把桌上的一包 好烟朝许明辉手边推了推,示意他再抽一支。 许明辉沉着脸,低头点上了烟,脊背往椅上一靠,急急地吐出一缕缕的轻烟。 五十年代,吴天湘和许明辉同在省里的一个大学任教。吴天湘是讲师,许明辉是助教, 五七年同时被划成一右派一。但是,他们走向这条深渊的道路却是大不相同的。 许明辉可以说是失足落网。他热情、豪爽,容易冲动。党委书记动员鸣放的报告激动了学研究中,无暇他顾。 可是,就这麽一心扑在事业上,反而惹出祸来了。我错了吗?我没有错!他用拳头敲着 光光的脑门,一肚子的委曲。 他腾地站起,又在屋里转来转去。住左走两步,碰到一张铺着破单子的旧木床,往右走 两步,碰到一只堆满期刊书报的旧书架。在屋里太憋闷了,他抄起桌上的期刊:跨出门去, 去找五七年一起被错划成﹁右派﹂的﹁五七战士﹂吴天湘。 吴天湘家里总是那麽安静舒适。两间一套的单元宿舍,虽说面积小点,却是处处收拾得 一尘不染,井井有条。这当然不是吴天湘的功劳,而是他那新近复婚的妻子温素玉怀着赎罪 的心情留下的成绩。 许明辉一来,照例是钻到里屋吴天湘那间书房兼卧室里去。这间小屋满是书。书架上排 列的是书,桌面上摊开的是书,床头枕边上搁着的是书,墙角空地上堆着的是书。只在壁上 挂有一幅吴天湘手书的鲁迅先生的名句: 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 不到五分钟,小屋里已是烟雾弥漫。许明辉坐在一张摺椅上,吴天湘斜靠在对面的一张 藤椅上,烟灰缸放在桌上的一角,吴天湘用烟斗,许明辉抽纸烟,两人都忙不迭地把尼古丁 往肺里吸去,谁也没有讲话。 吴天湘比许明辉大五、六岁,看上去却好像比许明辉小五、六岁。他穿一件法兰绒春秋 衫,一条纯毛哗叽长裨,裤缝笔挺。脚上吸着一双洗得很乾净的泡沫塑料拖鞋,露出一双黑 红两色相间斜格子的尼龙袜子。他同许明辉一样,也经历了二十年的磨难,甚至还遭受过比 许明辉更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因此而和他离了婚。但,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像许明辉 那样消沉、颓废、酗酒,以至潦倒。而是极其冷静地,或者说十分理智地接受了这接踵而来 的打击。如今,二十个春秋过去,他看上去还是那样年轻,那样精明,那样富有学者风度。 彷佛他只是演完了一幕悲剧,并不曾损伤他的身心,反而从中得到了启迪。 ﹁老吴,支部通知我,让我做检查。﹂许明辉终於打破了沉默。 吴天湘嘴里叼着烟斗,倾听着从烟斗里发出的嘶嘶的响声,并不答话。他把桌上的一包 好烟朝许明辉手边推了推,示意他再抽一支。 许明辉沉着脸,低头点上了烟,脊背往椅上一靠,急急地吐出一缕缕的轻烟。 五十年代,吴天湘和许明辉同在省里的一个大学任教。吴天湘是讲师,许明辉是助教, 五七年同时被划成﹁右派﹂。但是,他们走向这条深渊的道路却是大不相同的。 许明辉可以说是失足落网。他热情、豪爽,容易冲动。党委书记动员鸣放的报告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