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真假假谌容.txt 说明: 容,原名湛德容,祖籍四川巫山县,1936年10月3日出生于湖北汉口。1957年毕业于北 京俄语学院,毕业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担任音乐编辑和俄语翻译,1962年因多种疾 病缠身而被机关精简。63年7月,经朋友介绍,谌容自费到山西汾阳县贾家庄大队寄居, 在那里她不仅身心得以恢复健康,而且新的生活引发她沉睡在心灵深处的创作欲。64年谌 容回京,1972年谌湛容根据在北京郊区通县马驹桥公社插队四年积累的生活素材开始创作了 她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真真假假》写某外国文学教研室为批评许明辉一篇文章召开 了三次学习会,小说铺写了会议的全过程,主要突出了知识界对“左倾”思想干扰文学批评 的焦虑。 ~真真假假≈谌容 ~二O一O年九月二十七日版≈ ~好读书柜≈典藏版 一 一喂,您是吉祥东街公用电话吗?劳驾您给传一下五十三号的吴天湘。口天吴,天上的 天||- 一您甭跟我说这些,我不认得字。一那边是个嗓门挺大的女人,一不就是五十三号二楼 的老吴同志吗?一个瘦高老头儿,我认得。一 一对,对。一 一您是哪儿呀?一 一我是外国文学研究室。一 一啥?您是外国,哪儿?一
真真假假 谌容.txt 说明: 容,原名谌德容,祖籍四川巫山县,1936 年 10 月 3 日出生于湖北汉口。1957 年毕业于北 京俄语学院,毕业后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担任音乐编辑和俄语翻译,1962 年因多种疾 病缠身而被机关精简。63 年 7 月,经朋友介绍,谌容自费到山西汾阳县贾家庄大队寄居, 在那里她不仅身心得以恢复健康,而且新的生活引发她沉睡在心灵深处的创作欲。64 年谌 容回京,1972 年谌容根据在北京郊区通县马驹桥公社插队四年积累的生活素材开始创作了 她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真真假假》写某外国文学教研室为批评许明辉一篇文章召开 了三次学习会,小说铺写了会议的全过程,主要突出了知识界对“左倾”思想干扰文学批评 的焦虑。 ︽真真假假︾谌容 ︽二○一○年九月二十七日版︾ ︽好读书柜︾典藏版 一 ﹁喂,您是吉祥东街公用电话吗?劳驾您给传一下五十三号的吴天湘。口天吴,天上的 天││﹂ ﹁您甭跟我说这些,我不认得字。﹂那边是个嗓门挺大的女人,﹁不就是五十三号二楼 的老吴同志吗?一个瘦高老头儿,我认得。﹂ ﹁对,对。﹂ ﹁您是哪儿呀?﹂ ﹁我是外国文学研究室。﹂ ﹁啥?您是外国,哪儿?﹂

一喂,喂,您就说我姓杨,我叫杨昌明。杨丨「一 一行?!您候着吧,我这就叫去!一 树昌明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抄起鸡毛掸子,漫不经心地掸着桌上的灰尘。 喂1|一 那边接电话的人来了。 杨昌明赶紧放下鸡毛掸,双手捧着说筒,声音里带着尊敬: 一您是天湘同志吗?一 一是我。一声音是宏亮的。 一我是杨昌明呀!一 一什麽事?一 一明天上午九点钟开会。一 一不是己经发了通知了吗?一 一是啊,是啊,一杨昌明解释道,一这次会议,院党委非常重视,党委办公室的吉主任 要亲自参加。他要我务必再电话通知一次。一 那边没有说话。 杨昌明又进了一步: 一天湘同志,您明天最好早一点来。这个会还得您主持。一 一你是支部书记,党委布置的学习,当然由你主持。一 杨昌明急了,两手把话筒攥得更紧,好像这就是吴天湘的胳膊,声音里也带出恳求的意 味。 一天湘同志,您是研究室的主任。这不是一般的学习,这是批评老许那篇文章,我主持, 不合适。一 一会,我参加。主持,还是你。一 对方不容分说,把电话挂上了
﹁喂,喂,您就说我姓杨,我叫杨昌明。杨││﹂ ﹁行?!您候着吧,我这就叫去!﹂ 树昌明一手拿着话筒,一手抄起鸡毛掸子,漫不经心地掸着桌上的灰尘。 ﹁喂||﹂ 那边接电话的人来了。 杨昌明赶紧放下鸡毛掸,双手捧着说筒,声音里带着尊敬: ﹁您是天湘同志吗?﹂ ﹁是我。﹂声音是宏亮的。 ﹁我是杨昌明呀!﹂ ﹁什麽事?﹂ ﹁明天上午九点钟开会。﹂ ﹁不是已经发了通知了吗?﹂ ﹁是啊,是啊,﹂杨昌明解释道,﹁这次会议,院党委非常重视,党委办公室的吉主任 要亲自参加。他要我务必再电话通知一次。﹂ 那边没有说话。 杨昌明又进了一步: ﹁天湘同志,您明天最好早一点来。这个会还得您主持。﹂ ﹁你是支部书记,党委布置的学习,当然由你主持。﹂ 杨昌明急了,两手把话筒攥得更紧,好像这就是吴天湘的胳膊,声音里也带出恳求的意 味。 ﹁天湘同志,您是研究室的主任。这不是一般的学习,这是批评老许那篇文章,我主持, 不合适。﹂ ﹁会,我参加。主持,还是你。﹂ 对方不容分说,把电话挂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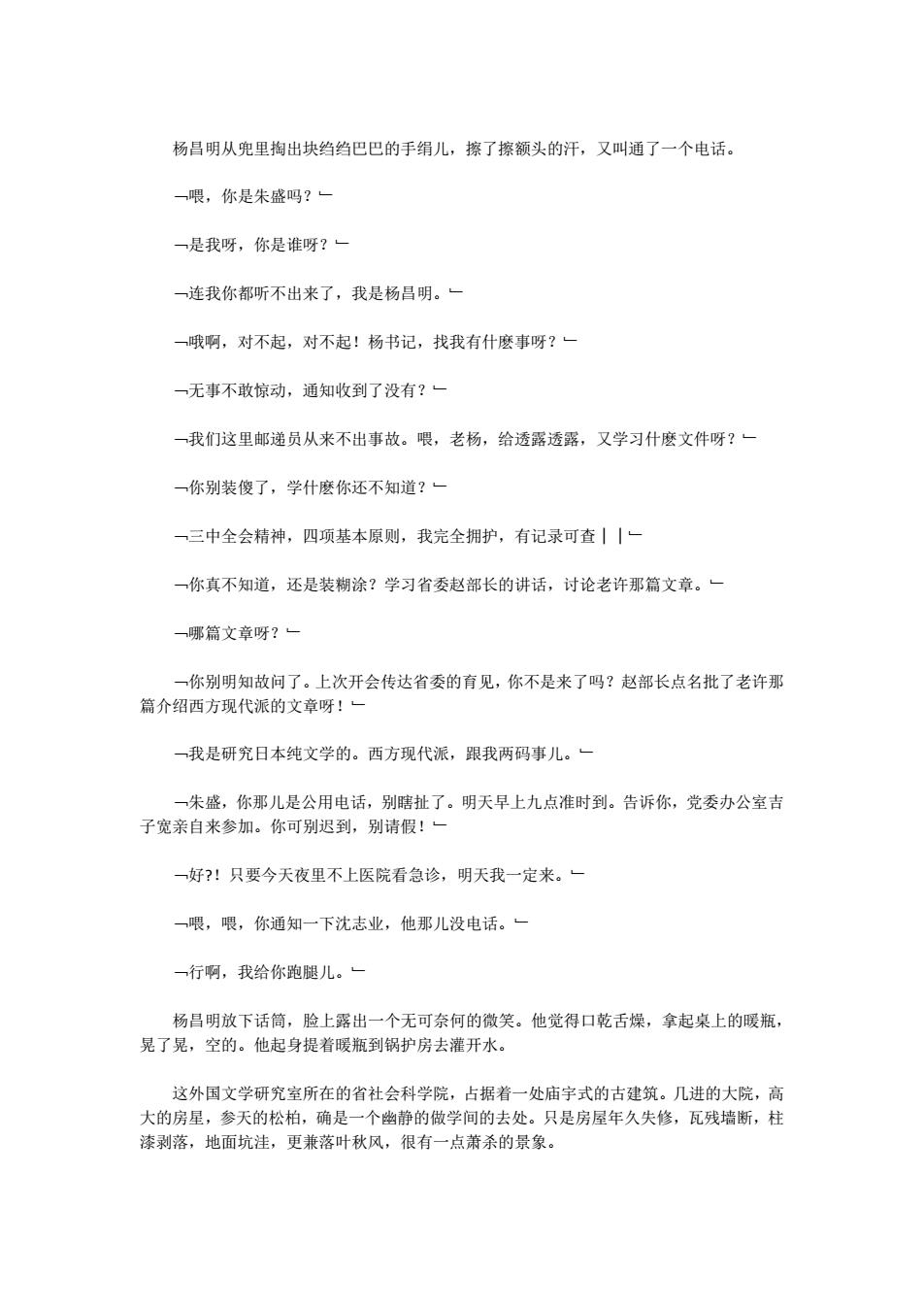
杨昌明从兜里掏出块绉绉巴巴的手绢儿,擦了擦额头的汗,又叫通了一个电话。 一喂,你是朱盛吗?一 一是我呀,你是谁呀?一 一连我你都听不出来了,我是杨昌明。一 一哦啊,对不起,对不起!杨书记,找我有什麽事呀?一 一无事不敢惊动,通知收到了没有?一 一我们这里邮递员从来不出事故。喂,老杨,给透露透露,又学习什麽文件呀?一 一你别装傻了,学什麽你还不知道?一 一三中全会精神,四项基本原则,我完全拥护,有记录可查丨|一 一你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学习省委赵部长的讲话,讨论老许那篇文章。一 一哪篇文章呀?一 一你别明知故问了。上次开会传达省委的育见,你不是来了吗?赵部长点名批了老许那 篇介绍西方现代派的文章呀!一 一我是研究日本纯文学的。西方现代派,跟我两码事儿。一 一朱盛,你那儿是公用电话,别瞎扯了。明天早上九点准时到。告诉你,党委办公室吉 子宽亲自来参加。你可别迟到,别请假!一 一好?!只要今天夜里不上医院看急诊,明天我一定来。一 一喂,喂,你通知一下沈志业,他那儿没电话。一 一行啊,我给你跑腿儿。一 杨昌明放下话筒,脸上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微笑。他觉得口乾舌燥,拿起桌上的暖瓶, 晃了晃,空的。他起身提着暖瓶到锅护房去灌开水。 这外国文学研究室所在的省社会科学院,占据着一处庙宇式的古建筑。几进的大院,高 大的房星,参天的松柏,确是一个幽静的做学间的去处。只是房屋年久失修,瓦残墙断,柱 漆剥落,地面坑洼,更兼落叶秋风,很有一点萧杀的景象
杨昌明从兜里掏出块绉绉巴巴的手绢儿,擦了擦额头的汗,又叫通了一个电话。 ﹁喂,你是朱盛吗?﹂ ﹁是我呀,你是谁呀?﹂ ﹁连我你都听不出来了,我是杨昌明。﹂ ﹁哦啊,对不起,对不起!杨书记,找我有什麽事呀?﹂ ﹁无事不敢惊动,通知收到了没有?﹂ ﹁我们这里邮递员从来不出事故。喂,老杨,给透露透露,又学习什麽文件呀?﹂ ﹁你别装傻了,学什麽你还不知道?﹂ ﹁三中全会精神,四项基本原则,我完全拥护,有记录可查││﹂ ﹁你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学习省委赵部长的讲话,讨论老许那篇文章。﹂ ﹁哪篇文章呀?﹂ ﹁你别明知故问了。上次开会传达省委的育见,你不是来了吗?赵部长点名批了老许那 篇介绍西方现代派的文章呀!﹂ ﹁我是研究日本纯文学的。西方现代派,跟我两码事儿。﹂ ﹁朱盛,你那儿是公用电话,别瞎扯了。明天早上九点准时到。告诉你,党委办公室吉 子宽亲自来参加。你可别迟到,别请假!﹂ ﹁好?!只要今天夜里不上医院看急诊,明天我一定来。﹂ ﹁喂,喂,你通知一下沈志业,他那儿没电话。﹂ ﹁行啊,我给你跑腿儿。﹂ 杨昌明放下话筒,脸上露出一个无可奈何的微笑。他觉得口乾舌燥,拿起桌上的暖瓶, 晃了晃,空的。他起身提着暖瓶到锅护房去灌开水。 这外国文学研究室所在的省社会科学院,占据着一处庙宇式的古建筑。几进的大院,高 大的房星,参天的松柏,确是一个幽静的做学间的去处。只是房屋年久失修,瓦残墙断,柱 漆剥落,地面坑洼,更兼落叶秋风,很有一点萧杀的景象

外国文学研究室属於恢复单位,几经过论研究争夺,才在这里占了一间办室。面积虽然 不小,做个餐厅能摆下七八张桌子,作研究室来用却极不相宜。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除 了聊天,还能研究啥?鉴於文学研究多属个体劳动,吴天湘自己也是把工作室设在寝室里的。 因而从外国文学研究室重建之後,就废除了坐班制度,各自在家搞自己的研究,除了开会和 查找资料,谁也不到研究室来。这间办公室,实际上就变成杨昌明一人用的了。也因此,他 除了一秘书-、一支书两项重任外,又兼任了公务员、电话员、收发员、接待员等项任务。 打了开水回来,杨昌明拿起茶杯,揭开痰盂盖,把隔夜的剩茶往里一倒,一股恶臭扑鼻 而来。他赶紧把痰盂盖上,也顾不得沏水,又回身坐下拿起了话筒。 一喂,童童呀,我是老杨。就你们家电话好打,一直通。这一上午打电话差点儿没把我 累死!一 一您可真够辛苦的!一 秦童童的爸爸是省委统战部的副部长,家里有电话。 一哎,童童,你怎麽也跟那些大研究员一样,不来坐班了?一 一我有病假条儿呀!一 一你的病假条怎麽那麽好开?你能不能也给我开两张?一 一行啊,只要你也在兵团落下病根,十年八年的好不了,我准给你弄假条儿!一 一哎,别开玩笑。明天九点开会,你可得到。一 一敢不来吗?平常没人想起我,到了开会学习,就想起秦童童了。一 一喂,说真的,童童,你明天早点儿来,帮我打扫打扫卫生。吉主任说了,亲自来听会 1- 一亲自来才好呢!叫他看看,挂名儿一个外国文学研究室,就那麽一间破屋子!还怪人 家不来上班,上班有地儿待吗?一 一你哪来那麽多牢骚?我可告诉你,明天的会讨论老许那篇文章。一 一我写不了文章,也不属於批判对象,没我的事儿!丨|一 一喂,我不跟你辩论!你上叶菲家拐个弯儿,通知她一下。她那儿没有传呼电话。一 没有等到明天,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吉子宽就来了
外国文学研究室属於恢复单位,几经过论研究争夺,才在这里占了一间办室。面积虽然 不小,做个餐厅能摆下七八张桌子,作研究室来用却极不相宜。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屋,除 了聊天,还能研究啥?鉴於文学研究多属个体劳动,吴天湘自己也是把工作室设在寝室里的。 因而从外国文学研究室重建之後,就废除了坐班制度,各自在家搞自己的研究,除了开会和 查找资料,谁也不到研究室来。这间办公室,实际上就变成杨昌明一人用的了。也因此,他 除了﹁秘书﹂、﹁支书﹂两项重任外,又兼任了公务员、电话员、收发员、接待员等项任务。 打了开水回来,杨昌明拿起茶杯,揭开痰盂盖,把隔夜的剩茶往里一倒,一股恶臭扑鼻 而来。他赶紧把痰盂盖上,也顾不得沏水,又回身坐下拿起了话筒。 ﹁喂,童童呀,我是老杨。就你们家电话好打,一直通。这一上午打电话差点儿没把我 累死!﹂ ﹁您可真够辛苦的!﹂ 秦童童的爸爸是省委统战部的副部长,家里有电话。 ﹁哎,童童,你怎麽也跟那些大研究员一样,不来坐班了?﹂ ﹁我有病假条儿呀!﹂ ﹁你的病假条怎麽那麽好开?你能不能也给我开两张?﹂ ﹁行啊,只要你也在兵团落下病根,十年八年的好不了,我准给你弄假条儿!﹂ ﹁哎,别开玩笑。明天九点开会,你可得到。﹂ ﹁敢不来吗?平常没人想起我,到了开会学习,就想起秦童童了。﹂ ﹁喂,说真的,童童,你明天早点儿来,帮我打扫打扫卫生。吉主任说了,亲自来听会 ││﹂ ﹁亲自来才好呢!叫他看看,挂名儿一个外国文学研究室,就那麽一间破屋子!还怪人 家不来上班,上班有地儿待吗?﹂ ﹁你哪来那麽多牢骚?我可告诉你,明天的会讨论老许那篇文章。﹂ ﹁我写不了文章,也不属於批判对象,没我的事儿!││﹂ ﹁喂,我不跟你辩论!你上叶菲家拐个弯儿,通知她一下。她那儿没有传呼电话。﹂ 二 没有等到明天,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吉子宽就来了

一老杨,电话都打了没有?一 杨昌明赶紧迎上去说: 一正在打。一 一好。一 年近六旬的吉子宽,虽是满头白发,却仍精力充沛。他拉过一张皮椅子,原想坐下,一 看那椅子,皮子破了,囊里的旧絮和弹簧都露了出来,没敢在上坐,就改用双手扶着椅背那 麽站着。两眼不由自主地把四周打量了一番,微微叹口气,摇着头说: 一你门这研究室像个什麽?破破烂烂,到处是灰,这办公室有几天没打扫了?简直快发 霉了,可怕啊!还研究外国文学呢,这哪儿有一点外国文学的气味?有的是没落潦倒的封建 文人的恶习!一 一我们这儿,卫生是差点。一杨昌明陪笑道。 一不是卫生,是这儿|「一吉子宽指指自己的脑袋说:一是思想发霉。小杨啊,你是多 年的政工干部,也可以说是一老改工一了,你可要警惕啊!不要以为现在重业务,强调出成 果,就放松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不行的。这回许明辉的文章摘了漏子,绝不是偶然的。我早 就说过,知识分子不注意思想改造,迟早要犯错误。你看,这才两、三年,有的人就把尾巴 翘到天上去了,这还不犯错误?一 杨昌明点了点头。他在吉子宽直接领导下,参加过反右派运动、反一右倾一斗争。一文 化大革命一中,吉子宽被当作推行一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的一黑干将揪了出来, 杨昌明也靠边站了。後来吉子宽得到一解放一,当了社会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杨 昌明也在政工组里当了一名组员。粉碎一四人帮一以後,吉子宽一说清楚了,当上党委办 公室主任,本想把杨昌明留在党委办公室里,杨昌明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才分配到外国文 学研究室来。在吉子宽的心目中,他是个很有希望的政工干部,可惜这几年被业务风翻的, 也有点歪歪扭扭的了。 一你接着打你的电话,一吉子宽摆了摆手,一打完电话,我们再商量一下明天的会怎麽 开。一 杨昌明又拨了一个传呼电话。 一喂,请你找一下十八号的张维。弓长张,维持的维。什麽?我是哪儿?我是外国文学 研究室里。一 不料,话筒里传来一个笑嘻嘻的声音。 一喂,同志,给找张电影票嘿!一
﹁老杨,电话都打了没有?﹂ 杨昌明赶紧迎上去说: ﹁正在打。﹂ ﹁好。﹂ 年近六旬的吉子宽,虽是满头白发,却仍精力充沛。他拉过一张皮椅子,原想坐下,一 看那椅子,皮子破了,囊里的旧絮和弹簧都露了出来,没敢在上坐,就改用双手扶着椅背那 麽站着。两眼不由自主地把四周打量了一番,微微叹口气,摇着头说: ﹁你门这研究室像个什麽?破破烂烂,到处是灰,这办公室有几天没打扫了?简直快发 霉了,可怕啊!还研究外国文学呢,这哪儿有一点外国文学的气味?有的是没落潦倒的封建 文人的恶习!﹂ ﹁我们这儿,卫生是差点。﹂杨昌明陪笑道。 ﹁不是卫生,是这儿||﹂吉子宽指指自己的脑袋说:﹁是思想发霉。小杨啊,你是多 年的政工干部,也可以说是﹃老改工﹄了,你可要警惕啊!不要以为现在重业务,强调出成 果,就放松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不行的。这回许明辉的文章摘了漏子,绝不是偶然的。我早 就说过,知识分子不注意思想改造,迟早要犯错误。你看,这才两、三年,有的人就把尾巴 翘到天上去了,这还不犯错误?﹂ 杨昌明点了点头。他在吉子宽直接领导下,参加过反右派运动、反﹁右倾﹂斗争。﹁文 化大革命﹂中,吉子宽被当作推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干将﹂揪了出来, 杨昌明也靠边站了。後来吉子宽得到﹁解放﹂,当了社会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政工组组长,杨 昌明也在政工组里当了一名组员。粉碎﹁四人帮﹂以後,吉子宽﹁说清楚﹂了,当上党委办 公室主任,本想把杨昌明留在党委办公室里,杨昌明念念不忘自己的专业,才分配到外国文 学研究室来。在吉子宽的心目中,他是个很有希望的政工干部,可惜这几年被业务风翻的, 也有点歪歪扭扭的了。 ﹁你接着打你的电话,﹂吉子宽摆了摆手,﹁打完电话,我们再商量一下明天的会怎麽 开。﹂ 杨昌明又拨了一个传呼电话。 ﹁喂,请你找一下十八号的张维。弓长张,维持的维。什麽?我是哪儿?我是外国文学 研究室里。﹂ 不料,话筒里传来一个笑嘻嘻的声音。 ﹁喂,同志,给找张电影票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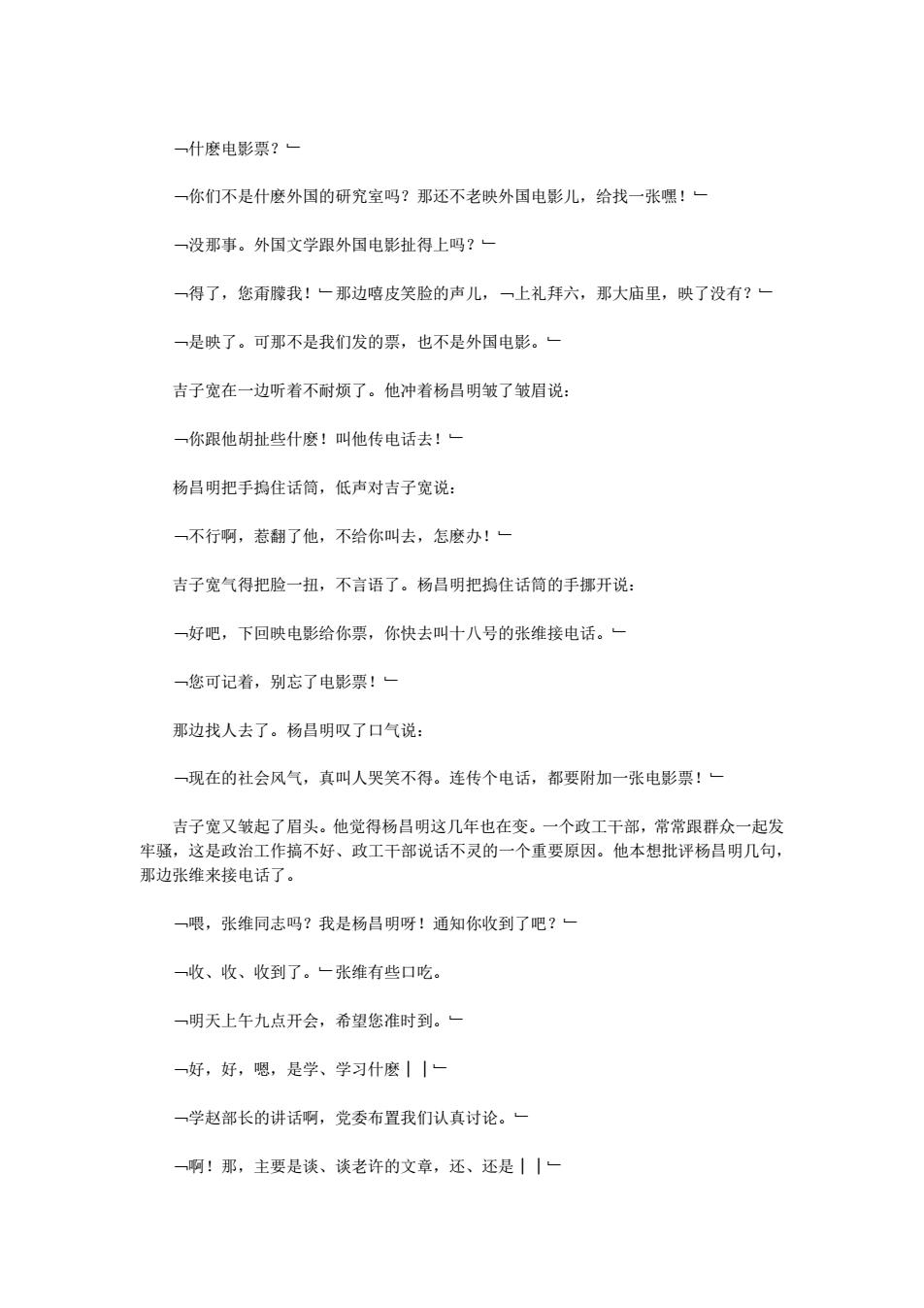
一什麽电影票?一 一你们不是什麽外国的研究室吗?那还不老映外国电影儿,给找一张嘿!一 一没那事。外国文学跟外国电影扯得上吗?一 一得了,您甭朦我!一那边嘻皮笑脸的声儿,一上礼拜六,那大庙里,映了没有?一 一是映了。可那不是我们发的票,也不是外国电影。一 吉子宽在一边听着不耐烦了。他冲着杨昌明皱了皱眉说: 一你跟他胡扯些什麽!叫他传电话去!一 杨昌明把手搗住话筒,低声对吉子宽说: 一不行啊,惹翻了他,不给你叫去,怎麽办!一 吉子宽气得把脸一扭,不言语了。杨昌明把搗住话筒的手挪开说: 一好吧,下回映电影给你票,你快去叫十八号的张维接电话。一 一您可记着,别忘了电影票!一 那边找人去了。杨昌明叹了口气说: 一现在的社会风气,真叫人哭笑不得。连传个电话,都要附加一张电影票!一 吉子宽又皱起了眉头。他觉得杨昌明这几年也在变。一个政工干部,常常跟群众一起发 牢骚,这是政治工作搞不好、政工干部说话不灵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本想批评杨昌明几句, 那边张维来接电话了。 一喂,张维同志吗?我是杨昌明呀!通知你收到了吧?一 一收、收、收到了。一张维有些口吃。 一明天上午九点开会,希望您准时到。一 一好,好,嗯,是学、学习什麽||一 一学赵部长的讲话啊,党委布置我们认真讨论。一 一啊!那,主要是谈、谈老许的文章,还、还是|一
﹁什麽电影票?﹂ ﹁你们不是什麽外国的研究室吗?那还不老映外国电影儿,给找一张嘿!﹂ ﹁没那事。外国文学跟外国电影扯得上吗?﹂ ﹁得了,您甭朦我!﹂那边嘻皮笑脸的声儿,﹁上礼拜六,那大庙里,映了没有?﹂ ﹁是映了。可那不是我们发的票,也不是外国电影。﹂ 吉子宽在一边听着不耐烦了。他冲着杨昌明皱了皱眉说: ﹁你跟他胡扯些什麽!叫他传电话去!﹂ 杨昌明把手摀住话筒,低声对吉子宽说: ﹁不行啊,惹翻了他,不给你叫去,怎麽办!﹂ 吉子宽气得把脸一扭,不言语了。杨昌明把摀住话筒的手挪开说: ﹁好吧,下回映电影给你票,你快去叫十八号的张维接电话。﹂ ﹁您可记着,别忘了电影票!﹂ 那边找人去了。杨昌明叹了口气说: ﹁现在的社会风气,真叫人哭笑不得。连传个电话,都要附加一张电影票!﹂ 吉子宽又皱起了眉头。他觉得杨昌明这几年也在变。一个政工干部,常常跟群众一起发 牢骚,这是政治工作搞不好、政工干部说话不灵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本想批评杨昌明几句, 那边张维来接电话了。 ﹁喂,张维同志吗?我是杨昌明呀!通知你收到了吧?﹂ ﹁收、收、收到了。﹂张维有些口吃。 ﹁明天上午九点开会,希望您准时到。﹂ ﹁好,好,嗯,是学、学习什麽││﹂ ﹁学赵部长的讲话啊,党委布置我们认真讨论。﹂ ﹁啊!那,主要是谈、谈老许的文章,还、还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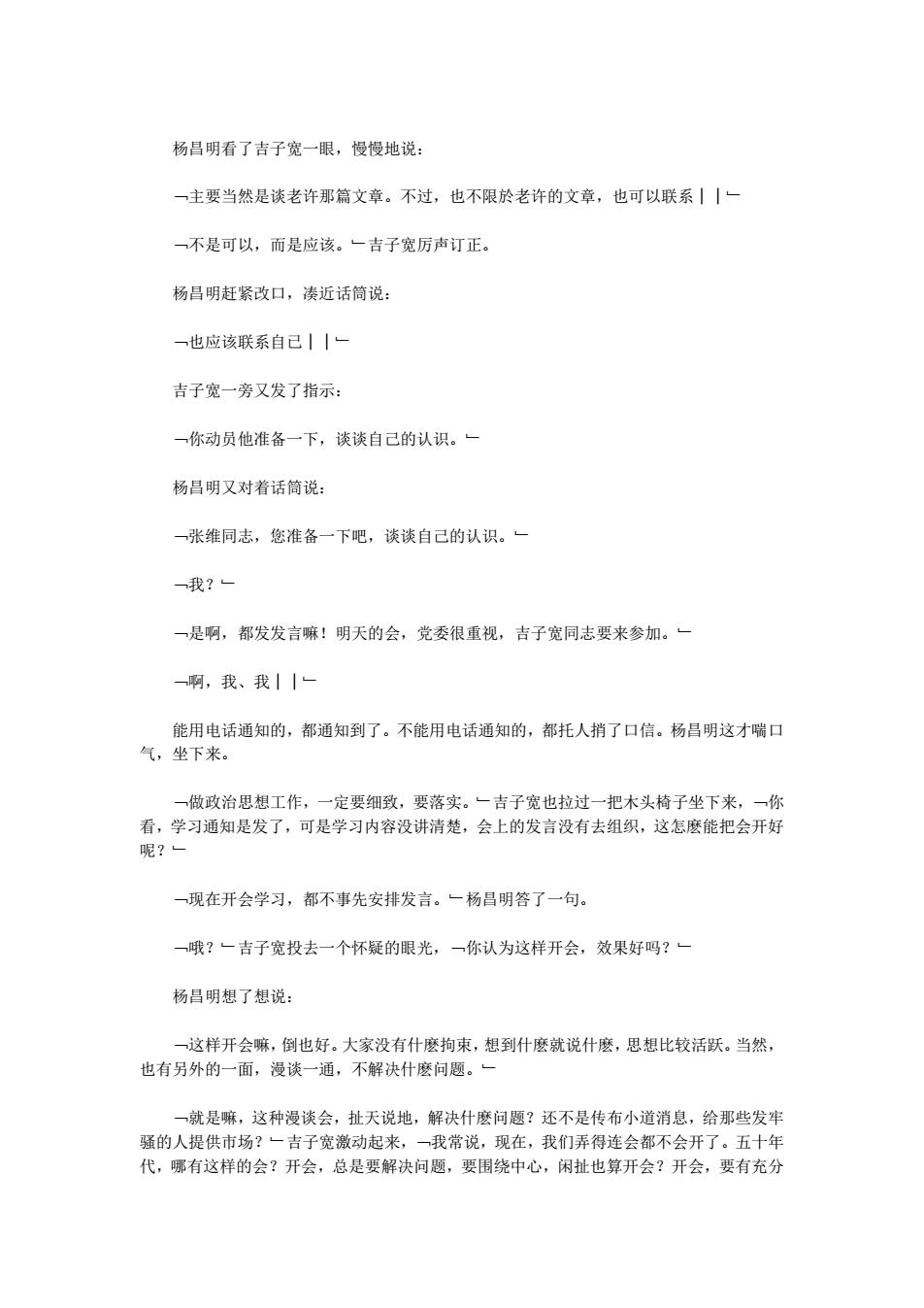
杨昌明看了吉子宽一眼,慢慢地说: 一主要当然是谈老许那篇文章。不过,也不限於老许的文章,也可以联系|一 一不是可以,而是应该。一吉子宽厉声订正。 杨昌明赶紧改口,凑近话筒说: 一也应该联系自已丨|一 吉子宽一旁又发了指示: 一你动员他准备一下,谈谈自己的认识。一 杨昌明又对着话筒说: 一张维同志,您准备一下吧,谈谈自己的认识。一 一我?一 一是啊,都发发言嘛!明天的会,党委很重视,吉子宽同志要来参加。一 一啊,我、我||一 能用电话通知的,都通知到了。不能用电话通知的,都托人捎了口信。杨昌明这才喘口 气,坐下来。 一做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细致,要落实。一吉子宽也拉过一把木头椅子坐下来,一你 看,学习通知是发了,可是学习内容没讲清楚,会上的发言没有去组织,这怎麽能把会开好 呢?一 一现在开会学习,都不事先安排发言。一杨昌明答了一句。 一哦?一吉子宽投去一个怀疑的眼光,一你认为这样开会,效果好吗?一 杨昌明想了想说: 一这样开会嘛,倒也好。大家没有什麽拘束,想到什麽就说什麼,思想比较活跃。当然, 也有另外的一面,漫谈一通,不解决什麽问题。一 一就是嘛,这种漫谈会,扯天说地,解决什麽问题?还不是传布小道消息,给那些发牢 骚的人提供市场?一吉子宽激动起来,一我常说,现在,我们弄得连会都不会开了。五十年 代,哪有这样的会?开会,总是要解决问题,要围绕中心,闲扯也算开会?开会,要有充分
杨昌明看了吉子宽一眼,慢慢地说: ﹁主要当然是谈老许那篇文章。不过,也不限於老许的文章,也可以联系││﹂ ﹁不是可以,而是应该。﹂吉子宽厉声订正。 杨昌明赶紧改口,凑近话筒说: ﹁也应该联系自已││﹂ 吉子宽一旁又发了指示: ﹁你动员他准备一下,谈谈自己的认识。﹂ 杨昌明又对着话筒说: ﹁张维同志,您准备一下吧,谈谈自己的认识。﹂ ﹁我?﹂ ﹁是啊,都发发言嘛!明天的会,党委很重视,吉子宽同志要来参加。﹂ ﹁啊,我、我││﹂ 能用电话通知的,都通知到了。不能用电话通知的,都托人捎了口信。杨昌明这才喘口 气,坐下来。 ﹁做政治思想工作,一定要细致,要落实。﹂吉子宽也拉过一把木头椅子坐下来,﹁你 看,学习通知是发了,可是学习内容没讲清楚,会上的发言没有去组织,这怎麽能把会开好 呢?﹂ ﹁现在开会学习,都不事先安排发言。﹂杨昌明答了一句。 ﹁哦?﹂吉子宽投去一个怀疑的眼光,﹁你认为这样开会,效果好吗?﹂ 杨昌明想了想说: ﹁这样开会嘛,倒也好。大家没有什麽拘束,想到什麽就说什麽,思想比较活跃。当然, 也有另外的一面,漫谈一通,不解决什麽问题。﹂ ﹁就是嘛,这种漫谈会,扯天说地,解决什麽问题?还不是传布小道消息,给那些发牢 骚的人提供市场?﹂吉子宽激动起来,﹁我常说,现在,我们弄得连会都不会开了。五十年 代,哪有这样的会?开会,总是要解决问题,要围绕中心,闲扯也算开会?开会,要有充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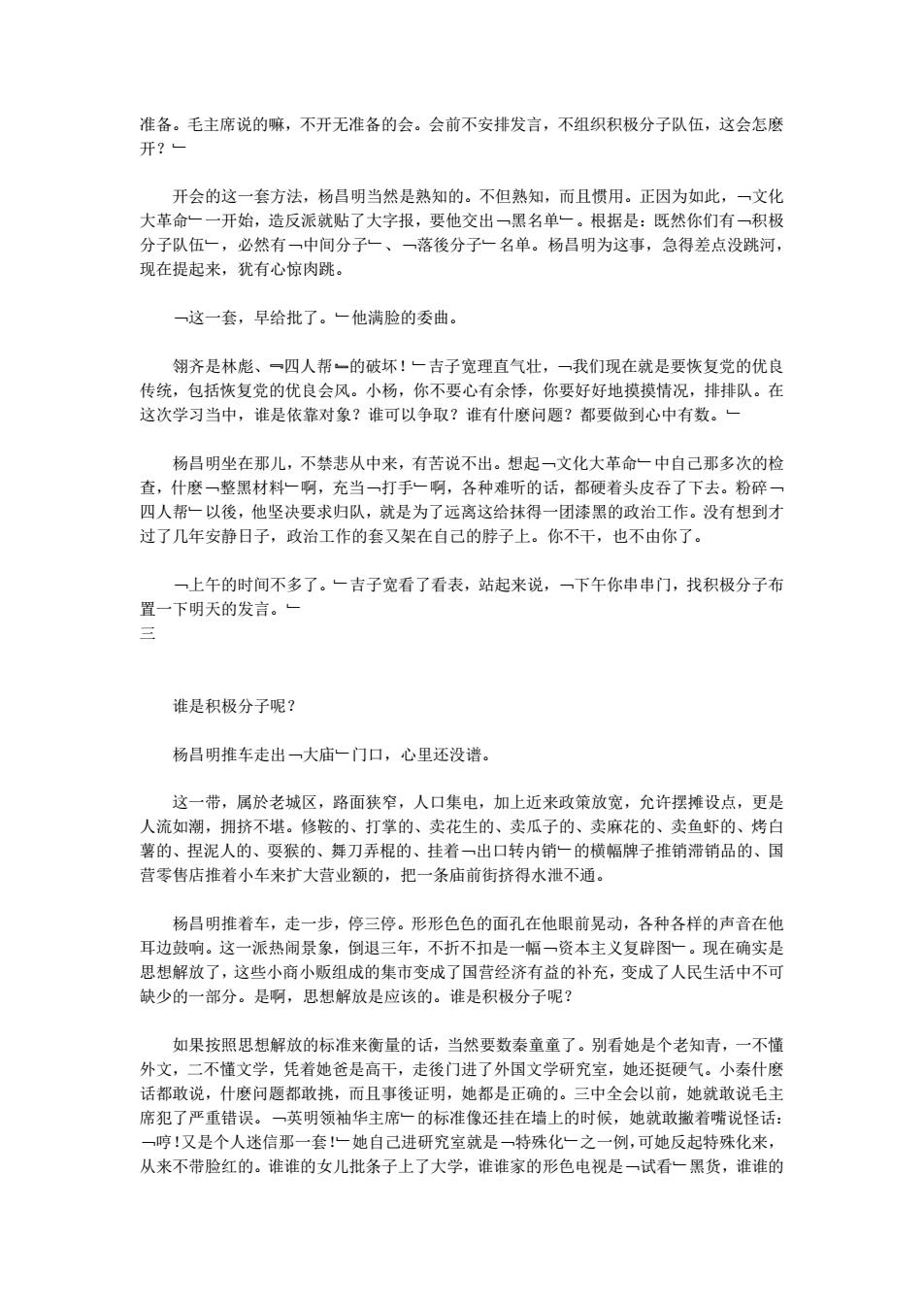
准备。毛主席说的嘛,不开无准备的会。会前不安排发言,不组织积极分子队伍,这会怎麽 开?L 开会的这一套方法,杨昌明当然是熟知的。不但熟知,而且惯用。正因为如此,一文化 大革命一一开始,造反派就贴了大字报,要他交出一黑名单一。根据是:既然你们有一积极 分子队伍一,必然有一中间分子、一落後分子一名单。杨昌明为这事,急得差点没跳河, 现在提起来,犹有心惊肉跳。 一这一套,早给批了。一他满脸的委曲。 翎齐是林彪、一四人帮一的破坏!一吉子宽理直气壮,一我们现在就是要恢复党的优良 传统,包括恢复党的优良会风。小杨,你不要心有余悸,你要好好地摸摸情况,排排队。在 这次学习当中,谁是依靠对象?谁可以争取?谁有什麽问题?都要做到心中有数。一 杨昌明坐在那儿,不禁悲从中来,有苦说不出。想起一文化大革命一中自己那多次的检 查,什麽一整黑材料一啊,充当一打手一啊,各种难听的话,都硬着头皮吞了下去。粉碎一 四人帮以後,他坚决要求归队,就是为了远离这给抹得一团漆黑的政治工作。没有想到才 过了几年安静日子,政治工作的套又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你不干,也不由你了。 一上午的时间不多了。一吉子宽看了看表,站起来说,一下午你串串门,找积极分子布 置一下明天的发言。一 三 谁是积极分子呢? 杨昌明推车走出一大庙一门口,心里还没谱。 这一带,属於老城区,路面狭窄,人口集电,加上近来政策放宽,允许摆摊设点,更是 人流如潮,拥挤不堪。修鞍的、打掌的、卖花生的、卖瓜子的、卖麻花的、卖鱼虾的、烤白 薯的、捏泥人的、耍猴的、舞刀弄棍的、挂着一出口转内销一的横幅牌子推销滞销品的、国 营零售店推着小车来扩大营业额的,把一条庙前街挤得水泄不通。 杨昌明推着车,走一步,停三停。形形色色的面孔在他眼前晃动,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他 耳边鼓响。这一派热闹景象,倒退三年,不折不扣是一幅一资本主义复辟图一。现在确实是 思想解放了,这些小商小贩组成的集市变成了国营经济有益的补充,变成了人民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是啊,思想解放是应该的。谁是积极分子呢? 如果按照思想解放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当然要数秦童童了。别看她是个老知青,一不懂 外文,二不懂文学,凭着她爸是高干,走後门进了外国文学研究室,她还挺硬气。小秦什麽 话都敢说,什麽问题都敢挑,而且事後证明,她都是正确的。三中全会以前,她就敢说毛主 席犯了严重错误。一英明领袖华主席一的标准像还挂在墙上的时候,她就敢撇着嘴说怪话: 一哼!又是个人迷信那一套!一她自己进研究室就是一特殊化一之一例,可她反起特殊化来, 从来不带脸红的。谁谁的女儿批条子上了大学,谁谁家的形色电视是一试看一黑货,谁谁的
准备。毛主席说的嘛,不开无准备的会。会前不安排发言,不组织积极分子队伍,这会怎麽 开?﹂ 开会的这一套方法,杨昌明当然是熟知的。不但熟知,而且惯用。正因为如此,﹁文化 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就贴了大字报,要他交出﹁黑名单﹂。根据是:既然你们有﹁积极 分子队伍﹂,必然有﹁中间分子﹂、﹁落後分子﹂名单。杨昌明为这事,急得差点没跳河, 现在提起来,犹有心惊肉跳。 ﹁这一套,早给批了。﹂他满脸的委曲。 翎齐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吉子宽理直气壮,﹁我们现在就是要恢复党的优良 传统,包括恢复党的优良会风。小杨,你不要心有余悸,你要好好地摸摸情况,排排队。在 这次学习当中,谁是依靠对象?谁可以争取?谁有什麽问题?都要做到心中有数。﹂ 杨昌明坐在那儿,不禁悲从中来,有苦说不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自己那多次的检 查,什麽﹁整黑材料﹂啊,充当﹁打手﹂啊,各种难听的话,都硬着头皮吞了下去。粉碎﹁ 四人帮﹂以後,他坚决要求归队,就是为了远离这给抹得一团漆黑的政治工作。没有想到才 过了几年安静日子,政治工作的套又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你不干,也不由你了。 ﹁上午的时间不多了。﹂吉子宽看了看表,站起来说,﹁下午你串串门,找积极分子布 置一下明天的发言。﹂ 三 谁是积极分子呢? 杨昌明推车走出﹁大庙﹂门口,心里还没谱。 这一带,属於老城区,路面狭窄,人口集电,加上近来政策放宽,允许摆摊设点,更是 人流如潮,拥挤不堪。修鞍的、打掌的、卖花生的、卖瓜子的、卖麻花的、卖鱼虾的、烤白 薯的、捏泥人的、耍猴的、舞刀弄棍的、挂着﹁出口转内销﹂的横幅牌子推销滞销品的、国 营零售店推着小车来扩大营业额的,把一条庙前街挤得水泄不通。 杨昌明推着车,走一步,停三停。形形色色的面孔在他眼前晃动,各种各样的声音在他 耳边鼓响。这一派热闹景象,倒退三年,不折不扣是一幅﹁资本主义复辟图﹂。现在确实是 思想解放了,这些小商小贩组成的集市变成了国营经济有益的补充,变成了人民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是啊,思想解放是应该的。谁是积极分子呢? 如果按照思想解放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当然要数秦童童了。别看她是个老知青,一不懂 外文,二不懂文学,凭着她爸是高干,走後门进了外国文学研究室,她还挺硬气。小秦什麽 话都敢说,什麽问题都敢挑,而且事後证明,她都是正确的。三中全会以前,她就敢说毛主 席犯了严重错误。﹁英明领袖华主席﹂的标准像还挂在墙上的时候,她就敢撇着嘴说怪话: ﹁哼!又是个人迷信那一套!﹂她自己进研究室就是﹁特殊化﹂之一例,可她反起特殊化来, 从来不带脸红的。谁谁的女儿批条子上了大学,谁谁家的形色电视是﹁试看﹂黑货,谁谁的

小秘书是谁谁的儿子,她都敢揭老底儿。可是,她除了那两片嘴滔滔不绝,够思想解放的标 兵,其他可就说不上了。她拿着假条躲在家里学英文,上班时溜到小放映家看参考电影。这 能叫积极分子吗? 一上海新产品,翻领尼龙衫,经久耐用,美观大方,十六块八角一件,要买的您快掏钱, 晚了可就没了!一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站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双手高举着一件紫红色 的样品,抖搂着,高声招徕顾客。平板车四周拥满着看主和买主。看来,这是一个待业青年 组织的小百货店。小伙子笑吟吟地挺会做生意,业务上有一套。 谁是积极分子呢? 如果技照业务上的成就作标准来衡量,第一个就是许明辉了。他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 发表的文学论着就有十七篇,大都是在北京、上海一些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的。还两次出席 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多次被邀请到兄弟省、市的大专院校去作有关西方当代文学的报告。他 家里的生活条件很差,工资低,住房挤,每天晚上他关在厨房里,坐一张小板凳,用一个方 凳当桌字写文章,从来没有怨言,这还不够积极的?可偏偏就是他,写了这篇错误文章,被 赵部长点了名。这次学习就为这事儿引起的,他连积极分子的边儿也挨不上呀! 一呛采、呛采,呛、呛、采引「,前边又听得锣鼓声声,围着一圈儿人,一帮小孩直往 里钻,大概是耍武术的,要不就是变戏法儿的,再不就是卖跌打损伤的狗皮膏药的。这锣鼓 声倒叫杨昌明的头脑清醒了一点。 一谁是积极分子呢?一 不能从一时一事的表现来看,那是表面的,靠不住的。思想解放没了边,就变成思想反 动。钻研业务入了迷,就可能走上歧途。积极不积极,主要看对党的态度!靠拢组织,向党 交心,这才是积极分子的主要标志。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张维应该是积极分子了。他从五十年代末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因为有海外关系,哥哥在英国伦敦,一直没有批准。一文化大革命一中还因此被关了牛棚。 粉碎一四人帮一以後,他又递了申请书。开十一大、开五届人大、开三中全会,每次重要会 议过後,他都有书面的或口头的思想汇报,谈感想,谈认识,找差距,表决心。每次开会, 他都第一个发言,并且都能联系自己的思想。这样一贯的积极分子,确实是很可贵的。可是 丨丨张维这人唯唯诺诺,甚免有些卑躬屈膝,在机关里谁也瞧不上他。他和大家也几乎没有 什麽往来。他,也像个积极分子吗? 杨昌明推着车,挤出人群。前边是家俱市场了。卖沙发的,卖落地灯的,卖大衣柜的, 站立两厢。杨昌明推着车缓缓而行,只见两边大衣柜的玻璃镜子里,都映出了他推车行走的 身影。他索性站住了,探身朝镜子里端详着自己。老了,憔悴了,才四十多岁的人,哪来这 麽多皱纹?我怎麽变成这样了?什麽时候变成这样了?!瞧他,头发乱蓬蓬的,後脑壳顶上 还翘起一大撮,脸色是黑里透黄,分明有一层晦气。当年那个精明强干的杨昌明哪里去了? 五十年代初,杨昌明还在大学中文系念书的时候,就是学生党支部书记了。那时候,他 朝气勃勃,仪表堂堂,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充满了信心,甚至是充满了感情的
小秘书是谁谁的儿子,她都敢揭老底儿。可是,她除了那两片嘴滔滔不绝,够思想解放的标 兵,其他可就说不上了。她拿着假条躲在家里学英文,上班时溜到小放映家看参考电影。这 能叫积极分子吗? ﹁上海新产品,翻领尼龙衫,经久耐用,美观大方,十六块八角一件,要买的您快掏钱, 晚了可就没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站在一辆平板三轮车上,双手高举着一件紫红色 的样品,抖搂着,高声招徕顾客。平板车四周拥满着看主和买主。看来,这是一个待业青年 组织的小百货店。小伙子笑吟吟地挺会做生意,业务上有一套。 谁是积极分子呢? 如果技照业务上的成就作标准来衡量,第一个就是许明辉了。他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 发表的文学论着就有十七篇,大都是在北京、上海一些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的。还两次出席 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多次被邀请到兄弟省、市的大专院校去作有关西方当代文学的报告。他 家里的生活条件很差,工资低,住房挤,每天晚上他关在厨房里,坐一张小板凳,用一个方 凳当桌字写文章,从来没有怨言,这还不够积极的?可偏偏就是他,写了这篇错误文章,被 赵部长点了名。这次学习就为这事儿引起的,他连积极分子的边儿也挨不上呀! ﹁呛采、呛采,呛、呛、采││,前边又听得锣鼓声声,围着一圈儿人,一帮小孩直往 里钻,大概是耍武术的,要不就是变戏法儿的,再不就是卖跌打损伤的狗皮膏药的。这锣鼓 声倒叫杨昌明的头脑清醒了一点。 ﹁谁是积极分子呢?﹂ 不能从一时一事的表现来看,那是表面的,靠不住的。思想解放没了边,就变成思想反 动。钻研业务入了迷,就可能走上歧途。积极不积极,主要看对党的态度!靠拢组织,向党 交心,这才是积极分子的主要标志。 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张维应该是积极分子了。他从五十年代末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因为有海外关系,哥哥在英国伦敦,一直没有批准。﹁文化大革命﹂中还因此被关了牛棚。 粉碎﹁四人帮﹂以後,他又递了申请书。开十一大、开五届人大、开三中全会,每次重要会 议过後,他都有书面的或口头的思想汇报,谈感想,谈认识,找差距,表决心。每次开会, 他都第一个发言,并且都能联系自己的思想。这样一贯的积极分子,确实是很可贵的。可是 ││张维这人唯唯诺诺,甚免有些卑躬屈膝,在机关里谁也瞧不上他。他和大家也几乎没有 什麽往来。他,也像个积极分子吗? 杨昌明推着车,挤出人群。前边是家俱市场了。卖沙发的,卖落地灯的,卖大衣柜的, 站立两厢。杨昌明推着车缓缓而行,只见两边大衣柜的玻璃镜子里,都映出了他推车行走的 身影。他索性站住了,探身朝镜子里端详着自己。老了,憔悴了,才四十多岁的人,哪来这 麽多皱纹?我怎麽变成这样了?什麽时候变成这样了?!瞧他,头发乱蓬蓬的,後脑壳顶上 还翘起一大撮,脸色是黑里透黄,分明有一层晦气。当年那个精明强干的杨昌明哪里去了? 五十年代初,杨昌明还在大学中文系念书的时候,就是学生党支部书记了。那时候,他 朝气勃勃,仪表堂堂,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充满了信心,甚至是充满了感情的

这与他自己的经历也许是分不开的。他幼年丧母,父亲工作忙,他只得朝夕和继母相处。 虽说吃穿不愁,不打不骂,却没有什麽家庭温暖可言。他有过少年的不慎,有过青年的荒庸。 一次一次,都是团组织、党组织有力的手扶住了他。他在党的怀抱中成长,他也把对母亲的 爱献给了党。他在高中毕业时申请入了党。 他热爱党的工作,全心全意做好这个工作。就在他当选为支部书记的那一年,他第一次 以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同一位因为一生活问题一被取消了候补党员资格的女同学一个别谈话 一。这种一生活问题一,如果搁在一文化革命一中,或者在今天,也许都不算什麽问题了。 可是,那时候党纪森严,一个候补党员发生这样的问题,还有什麽资格留在党的行列里呢! 这位女同学和他不同班,平常很少交往。但是,在支部书记面前,她敞开自己的思想, 悔恨自己的失足,解剖自己的灵魂,谈到了一些也许连她生母也不曾知道的心灵深处的隐秘。 她忏悔,她伤心,她觉得一党不要我了一。 一不,党还是对你寄以希望的。一杨昌明说,一希望你改正错误,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 来。那女同学先是一怔,随後,两行晶莹的泪水默默地淌了下来。这无声的眼泪倾诉了她对 党的感激,召回了她失去的希望。 杨昌明第一次感到,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那麽平凡的话竞有那麽不平凡的威力。它抚慰 了一个受伤的灵魂,甚至是给予了一个陷在深渊的弱者以生的力量。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是 一个党的工作者。他感到,党是圣洁的。它伟大而又平凡,崇高而又亲切。党是温暖的。它 有父亲般的严厉,也有母亲般的爱。党是透明的。在它的周围,容不得半点污秽丑行。 当杨昌明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而被留校的时候,他被分配到党委学生部去工作。老师和同 学都惋借一个很有希望的专业人才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连党委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也 准备用种种理由,去说服杨晶明服从组织分配。 出乎意外的是,杨昌明非常偷快地踏上党的政治工作岗位。他的女友林佩芬丨」後来成 为他的妻子,当时也劝他再考虑考虑。她说: 一你学的是文学,去搞政治,不後悔吗?一 一不!政治工作和文学工作是相通的。一杨昌明高高兴兴地说,一文学工作的对象是人, 政抬工作的对象也是人。文学工作陶治人的心灵,使人变得美好起来。政治工作也是净化人 的灵魂,使人变得美好起来。一 一瞧你,简直把政治工作说成一首诗了!一 一是一首诗,一首关於人的诗!或许正因为我是学文学的,我才更看重政治工作。它像 文学一样是美学,是人学,是科学,是一门艺术。我愿意为这门综合性的科学,为这门研究 人的艺术贡献一切。一 林佩芬被他的热情所打动,她表示赞同了
这与他自己的经历也许是分不开的。他幼年丧母,父亲工作忙,他只得朝夕和继母相处。 虽说吃穿不愁,不打不骂,却没有什麽家庭温暖可言。他有过少年的不慎,有过青年的荒庸。 一次一次,都是团组织、党组织有力的手扶住了他。他在党的怀抱中成长,他也把对母亲的 爱献给了党。他在高中毕业时申请入了党。 他热爱党的工作,全心全意做好这个工作。就在他当选为支部书记的那一年,他第一次 以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同一位因为﹁生活问题﹂被取消了候补党员资格的女同学﹁个别谈话 ﹂。这种﹁生活问题﹂,如果搁在﹁文化革命﹂中,或者在今天,也许都不算什麽问题了。 可是,那时候党纪森严,一个候补党员发生这样的问题,还有什麽资格留在党的行列里呢! 这位女同学和他不同班,平常很少交往。但是,在支部书记面前,她敞开自己的思想, 悔恨自己的失足,解剖自己的灵魂,谈到了一些也许连她生母也不曾知道的心灵深处的隐秘。 她忏悔,她伤心,她觉得﹁党不要我了﹂。 ﹁不,党还是对你寄以希望的。﹂杨昌明说,﹁希望你改正错误,重新回到党的怀抱里 来。那女同学先是一怔,随後,两行晶莹的泪水默默地淌了下来。这无声的眼泪倾诉了她对 党的感激,召回了她失去的希望。 杨昌明第一次感到,从自己嘴里说出来的那麽平凡的话竟有那麽不平凡的威力。它抚慰 了一个受伤的灵魂,甚至是给予了一个陷在深渊的弱者以生的力量。而这一切仅仅因为他是 一个党的工作者。他感到,党是圣洁的。它伟大而又平凡,崇高而又亲切。党是温暖的。它 有父亲般的严厉,也有母亲般的爱。党是透明的。在它的周围,容不得半点污秽丑行。 当杨昌明以优秀的成绩毕业而被留校的时候,他被分配到党委学生部去工作。老师和同 学都惋借一个很有希望的专业人才不能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连党委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也 准备用种种理由,去说服杨晶明服从组织分配。 出乎意外的是,杨昌明非常愉快地踏上党的政治工作岗位。他的女友林佩芬||後来成 为他的妻子,当时也劝他再考虑考虑。她说: ﹁你学的是文学,去搞政治,不後悔吗?﹂ ﹁不!政治工作和文学工作是相通的。﹂杨昌明高高兴兴地说,﹁文学工作的对象是人, 政抬工作的对象也是人。文学工作陶冶人的心灵,使人变得美好起来。政治工作也是净化人 的灵魂,使人变得美好起来。﹂ ﹁瞧你,简直把政治工作说成一首诗了!﹂ ﹁是一首诗,一首关於人的诗!或许正因为我是学文学的,我才更看重政治工作。它像 文学一样是美学,是人学,是科学,是一门艺术。我愿意为这门综合性的科学,为这门研究 人的艺术贡献一切。﹂ 林佩芬被他的热情所打动,她表示赞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