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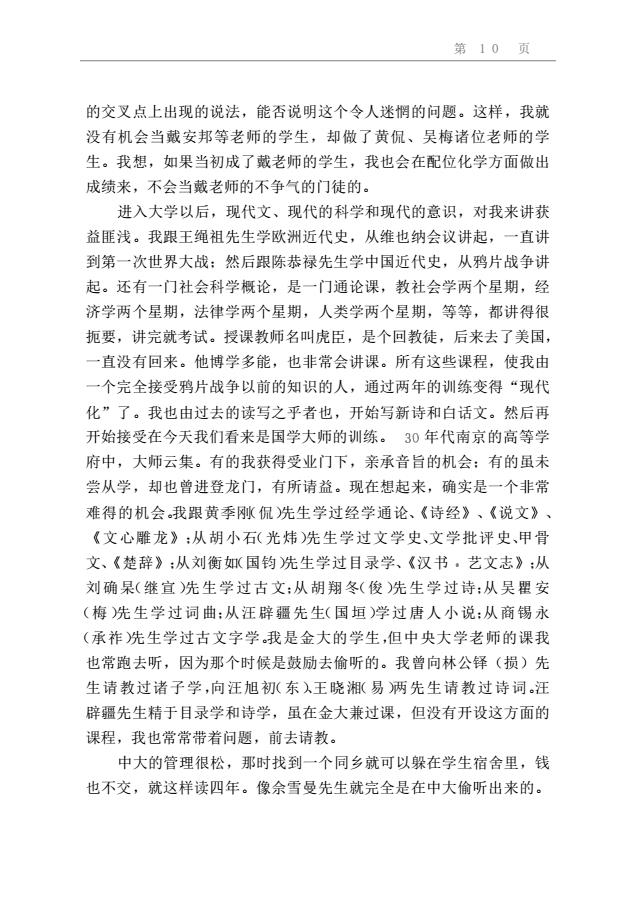
第10币 的交叉点上出现的说法,能否说明这个令人迷惘的问题。这样,我就 没有机会当戴安邦等老师的学生,却做了黄侃、吴梅诸位老师的学 生。我想,如果当初成了戴老师的学生,我也会在配位化学方面做出 成绩来,不会当戴老师的不争气的门徒的。 进入大学以后,现代文、现代的科学和现代的意识,对我来讲获 益匪浅。我跟王绳祖先生学欧洲近代史,从维也纳会议讲起,一直讲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跟陈恭禄先生学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 起。还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是一门通论课,教社会学两个星期,经 济学两个星期,法律学两个星期,人类学两个星期,等等,都讲得很 扼要,讲完就考试。授课教师名叫虎臣,是个回教徒,后来去了美国, 一直没有回来。他博学多能,也非常会讲课。所有这些课程,使我由 一个完全接受鸦片战争以前的知识的人,通过两年的训练变得“现代 化”了。我也由过去的读写之乎者也,开始写新诗和白话文。然后再 开始接受在今天我们看来是国学大师的训练。30年代南京的高等学 府中,大师云集。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的机会:有的虽未 尝从学,却也曾进登龙门,有所请益。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 难得的机会我跟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 《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 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冼生学过目录学、《汉书·艺文志》:从 刘确杲(继宜)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 (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 (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我是金大的学生,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我 也常跑去听,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去偷听的。我曾向林公铎(损)先 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入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 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 课程,我也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学生宿舍里,钱 也不交,就这样读四年。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 的交叉点上出现的说法,能否说明这个令人迷惘的问题。这样,我就 没有机会当戴安邦等老师的学生,却做了黄侃、吴梅诸位老师的学 生。我想,如果当初成了戴老师的学生,我也会在配位化学方面做出 成绩来,不会当戴老师的不争气的门徒的。 进入大学以后,现代文、现代的科学和现代的意识,对我来讲获 益匪浅。我跟王绳祖先生学欧洲近代史,从维也纳会议讲起,一直讲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跟陈恭禄先生学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讲 起。还有一门社会科学概论,是一门通论课,教社会学两个星期,经 济学两个星期,法律学两个星期,人类学两个星期,等等,都讲得很 扼要,讲完就考试。授课教师名叫虎臣,是个回教徒,后来去了美国, 一直没有回来。他博学多能,也非常会讲课。所有这些课程,使我由 一个完全接受鸦片战争以前的知识的人,通过两年的训练变得“现代 化”了。我也由过去的读写之乎者也,开始写新诗和白话文。然后再 开始接受在今天我们看来是国学大师的训练。 年代南京的高等学 府中,大师云集。有的我获得受业门下,亲承音旨的机会;有的虽未 尝从学,却也曾进登龙门,有所请益。现在想起来,确实是一个非常 难得的机会。我跟黄季刚(侃)先生学过经学通论、《诗经》、《说文》、 《文心雕龙》;从胡小石(光炜)先生学过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甲骨 文、《楚辞》;从刘衡如(国钧)先生学过目录学、《汉书 艺文志》;从 刘确杲(继宣)先生学过古文;从胡翔冬(俊)先生学过诗;从吴瞿安 (梅)先生学过词曲;从汪辟疆先生(国垣)学过唐人小说;从商锡永 (承祚)先生学过古文字学。我是金大的学生,但中央大学老师的课我 也常跑去听,因为那个时候是鼓励去偷听的。我曾向林公铎(损)先 生请教过诸子学,向汪旭初(东)、王晓湘(易)两先生请教过诗词。汪 辟疆先生精于目录学和诗学,虽在金大兼过课,但没有开设这方面的 课程,我也常常带着问题,前去请教。 中大的管理很松,那时找到一个同乡就可以躲在学生宿舍里,钱 也不交,就这样读四年。像佘雪曼先生就完全是在中大偷听出来的。 第 1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