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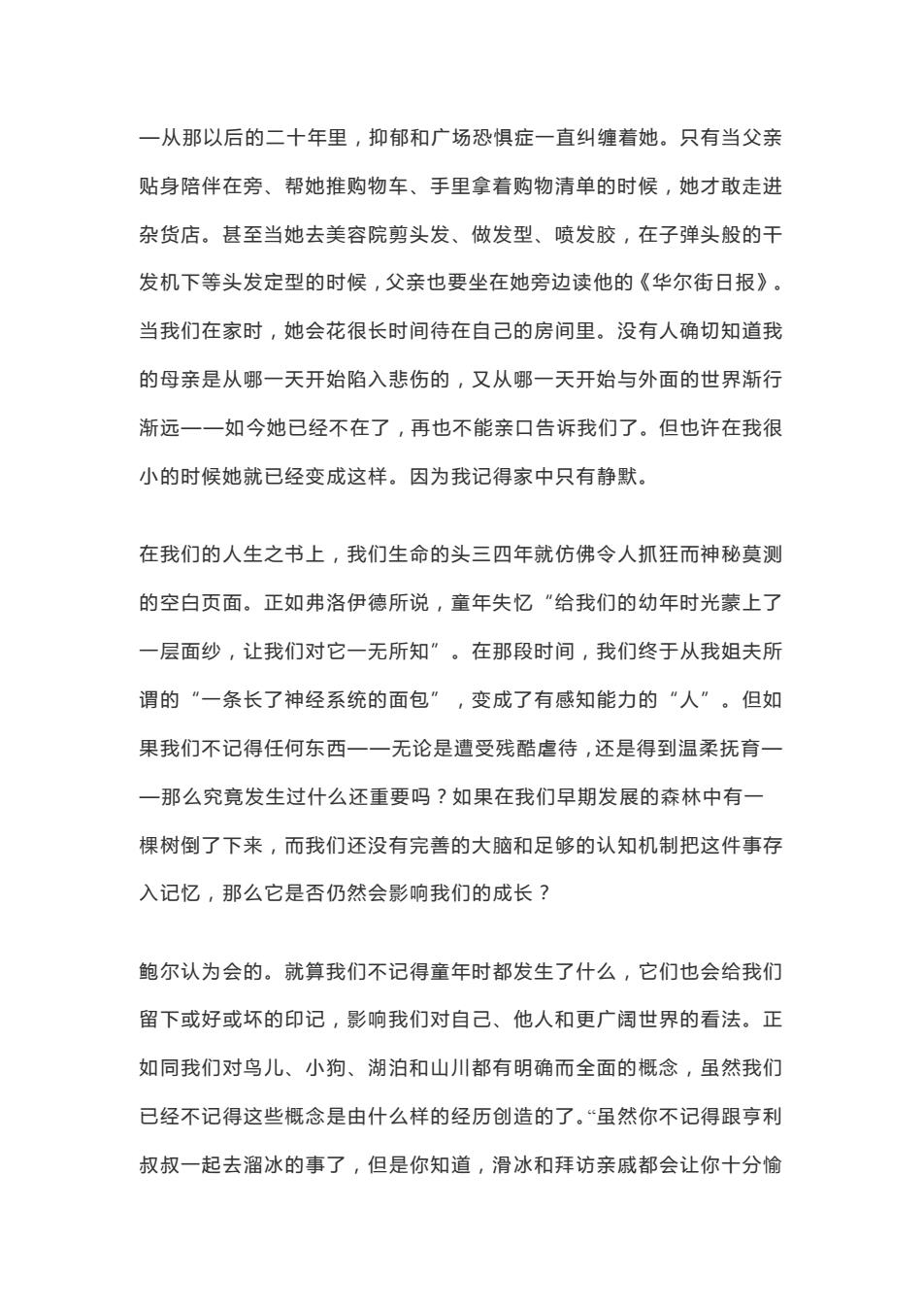
一从那以后的二十年里,抑郁和广场恐惧症一直纠缠着她。只有当父亲 贴身陪伴在旁、帮她推购物车、手里拿着购物清单的时候,她才敢走进 杂货店。甚至当她去美容院剪头发、做发型、喷发胶,在子弹头般的干 发机下等头发定型的时候,父亲也要坐在她旁边读他的《华尔街日报》。 当我们在家时,她会花很长时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人确切知道我 的母亲是从哪一天开始陷入悲伤的,又从哪一天开始与外面的世界渐行 渐远一一如今她已经不在了,再也不能亲口告诉我们了。但也许在我很 小的时候她就已经变成这样。因为我记得家中只有静默。 在我们的人生之书上,我们生命的头三四年就仿佛令人抓狂而神秘莫测 的空白页面。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童年失忆“给我们的幼年时光蒙上了 一层面纱,让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在那段时间,我们终于从我姐夫所 谓的”一条长了神经系统的面包”,变成了有感知能力的“人”。但如 果我们不记得任何东西一一无论是遭受残酷虐待,还是得到温柔抚育一 一那么究竟发生过什么还重要吗?如果在我们早期发展的森林中有一 棵树倒了下来,而我们还没有完善的大脑和足够的认知机制把这件事存 入记忆,那么它是否仍然会影响我们的成长? 鲍尔认为会的。就算我们不记得童年时都发生了什么,它们也会给我们 留下或好或坏的印记,影响我们对自己、他人和更广阔世界的看法。正 如同我们对鸟儿、小狗、湖泊和山川都有明确而全面的概念,虽然我们 已经不记得这些概念是由什么样的经历创造的了。“虽然你不记得跟亨利 叔叔一起去溜冰的事了,但是你知道,滑冰和拜访亲戚都会让你十分愉—从那以后的二十年里,抑郁和广场恐惧症一直纠缠着她。只有当父亲 贴身陪伴在旁、帮她推购物车、手里拿着购物清单的时候,她才敢走进 杂货店。甚至当她去美容院剪头发、做发型、喷发胶,在子弹头般的干 发机下等头发定型的时候,父亲也要坐在她旁边读他的《华尔街日报》。 当我们在家时,她会花很长时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没有人确切知道我 的母亲是从哪一天开始陷入悲伤的,又从哪一天开始与外面的世界渐行 渐远——如今她已经不在了,再也不能亲口告诉我们了。但也许在我很 小的时候她就已经变成这样。因为我记得家中只有静默。 在我们的人生之书上,我们生命的头三四年就仿佛令人抓狂而神秘莫测 的空白页面。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童年失忆“给我们的幼年时光蒙上了 一层面纱,让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在那段时间,我们终于从我姐夫所 谓的“一条长了神经系统的面包”,变成了有感知能力的“人”。但如 果我们不记得任何东西——无论是遭受残酷虐待,还是得到温柔抚育— —那么究竟发生过什么还重要吗?如果在我们早期发展的森林中有一 棵树倒了下来,而我们还没有完善的大脑和足够的认知机制把这件事存 入记忆,那么它是否仍然会影响我们的成长? 鲍尔认为会的。就算我们不记得童年时都发生了什么,它们也会给我们 留下或好或坏的印记,影响我们对自己、他人和更广阔世界的看法。正 如同我们对鸟儿、小狗、湖泊和山川都有明确而全面的概念,虽然我们 已经不记得这些概念是由什么样的经历创造的了。“虽然你不记得跟亨利 叔叔一起去溜冰的事了,但是你知道,滑冰和拜访亲戚都会让你十分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