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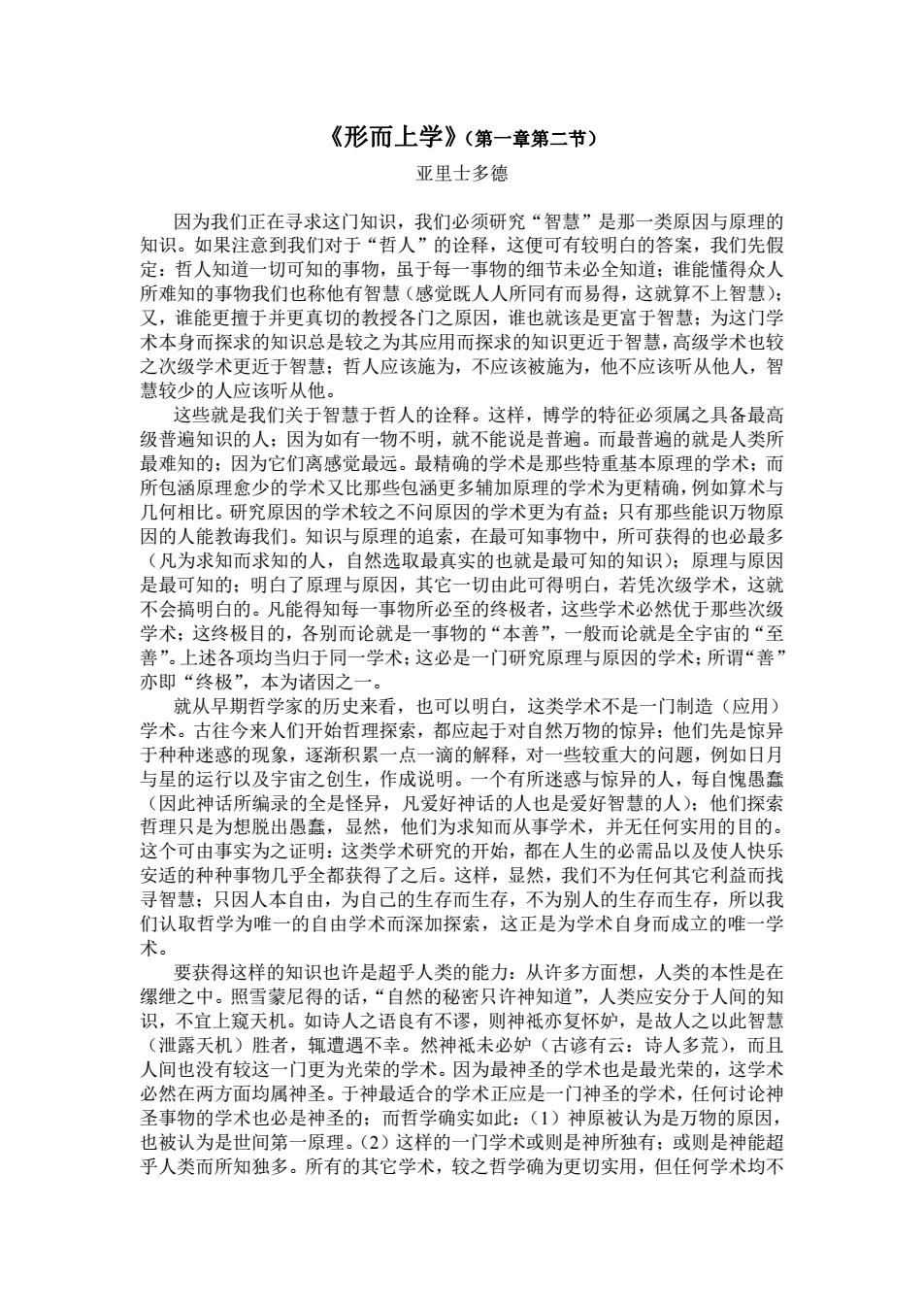
《形而上学》(第一章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 因为我们正在寻求这门知识,我们必须研究“智慧”是那一类原因与原理的 知识。如果注意到我们对于“哲人”的诠释,这便可有较明白的答案,我们先假 定:哲人知道一切可知的事物,虽于每一事物的细节未必全知道:谁能懂得众人 所难知的事物我们也称他有智慧(感觉既人人所同有而易得,这就算不上智慧): 又,谁能更擅于并更真切的教授各门之原因,谁也就该是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 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 之次级学术更近于智慧: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该被施为,他不应该听从他人,智 慧较少的人应该听从他。 这些就是我们关于智慧于哲人的诠释。这样,博学的特征必须属之具备最高 级普遍知识的人:因为如有一物不明,就不能说是普遍。而最普遍的就是人类所 最难知的:因为它们离感觉最远。最精确的学术是那些特重基本原理的学术;而 所包涵原理愈少的学术又比那些包涵更多辅加原理的学术为更精确,例如算术与 几何相比。研究原因的学术较之不问原因的学术更为有益:只有那些能识万物原 因的人能教诲我们。知识与原理的追索,在最可知事物中,所可获得的也必最多 (凡为求知而求知的人,自然选取最真实的也就是最可知的知识):原理与原因 是最可知的:明白了原理与原因,其它一切由此可得明白,若凭次级学术,这就 不会搞明白的。凡能得知每一事物所必至的终极者,这些学术必然优于那些次级 学术;这终极目的,各别而论就是一事物的“本善”,一般而论就是全宇宙的“至 善”。上述各项均当归于同一学术:这必是一门研究原理与原因的学术;所谓“善” 亦即“终极”,本为诸因之一 就从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来看,也可以明白,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应用) 学术。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 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 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 (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探索 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 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之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 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 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 术。 要获得这样的知识也许是超乎人类的能力:从许多方面想,人类的本性是在 缧绁之中。照雪蒙尼得的话,“自然的秘密只许神知道”,人类应安分于人间的知 识,不宜上窥天机。如诗人之语良有不谬,则神祗亦复怀妒,是故人之以此智慧 (泄露天机)胜者,辄遭遇不幸。然神祗未必妒(古谚有云:诗人多荒),而且 人间也没有较这一门更为光荣的学术。因为最神圣的学术也是最光荣的,这学术 必然在两方面均属神圣。于神最适合的学术正应是一门神圣的学术,任何讨论神 圣事物的学术也必是神圣的:而哲学确实如此:(1)神原被认为是万物的原因, 也被认为是世间第一原理。(2)这样的一门学术或则是神所独有;或则是神能超 乎人类而所知独多。所有的其它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形而上学》(第一章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 因为我们正在寻求这门知识,我们必须研究“智慧”是那一类原因与原理的 知识。如果注意到我们对于“哲人”的诠释,这便可有较明白的答案,我们先假 定:哲人知道一切可知的事物,虽于每一事物的细节未必全知道;谁能懂得众人 所难知的事物我们也称他有智慧(感觉既人人所同有而易得,这就算不上智慧); 又,谁能更擅于并更真切的教授各门之原因,谁也就该是更富于智慧;为这门学 术本身而探求的知识总是较之为其应用而探求的知识更近于智慧,高级学术也较 之次级学术更近于智慧;哲人应该施为,不应该被施为,他不应该听从他人,智 慧较少的人应该听从他。 这些就是我们关于智慧于哲人的诠释。这样,博学的特征必须属之具备最高 级普遍知识的人;因为如有一物不明,就不能说是普遍。而最普遍的就是人类所 最难知的;因为它们离感觉最远。最精确的学术是那些特重基本原理的学术;而 所包涵原理愈少的学术又比那些包涵更多辅加原理的学术为更精确,例如算术与 几何相比。研究原因的学术较之不问原因的学术更为有益;只有那些能识万物原 因的人能教诲我们。知识与原理的追索,在最可知事物中,所可获得的也必最多 (凡为求知而求知的人,自然选取最真实的也就是最可知的知识);原理与原因 是最可知的;明白了原理与原因,其它一切由此可得明白,若凭次级学术,这就 不会搞明白的。凡能得知每一事物所必至的终极者,这些学术必然优于那些次级 学术;这终极目的,各别而论就是一事物的“本善”,一般而论就是全宇宙的“至 善”。上述各项均当归于同一学术;这必是一门研究原理与原因的学术;所谓“善” 亦即“终极”,本为诸因之一。 就从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来看,也可以明白,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应用) 学术。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 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 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 (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探索 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 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 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之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 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 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 术。 要获得这样的知识也许是超乎人类的能力:从许多方面想,人类的本性是在 缧绁之中。照雪蒙尼得的话,“自然的秘密只许神知道”,人类应安分于人间的知 识,不宜上窥天机。如诗人之语良有不谬,则神祗亦复怀妒,是故人之以此智慧 (泄露天机)胜者,辄遭遇不幸。然神祗未必妒(古谚有云:诗人多荒),而且 人间也没有较这一门更为光荣的学术。因为最神圣的学术也是最光荣的,这学术 必然在两方面均属神圣。于神最适合的学术正应是一门神圣的学术,任何讨论神 圣事物的学术也必是神圣的;而哲学确实如此:(1)神原被认为是万物的原因, 也被认为是世间第一原理。(2)这样的一门学术或则是神所独有;或则是神能超 乎人类而所知独多。所有的其它学术,较之哲学确为更切实用,但任何学术均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