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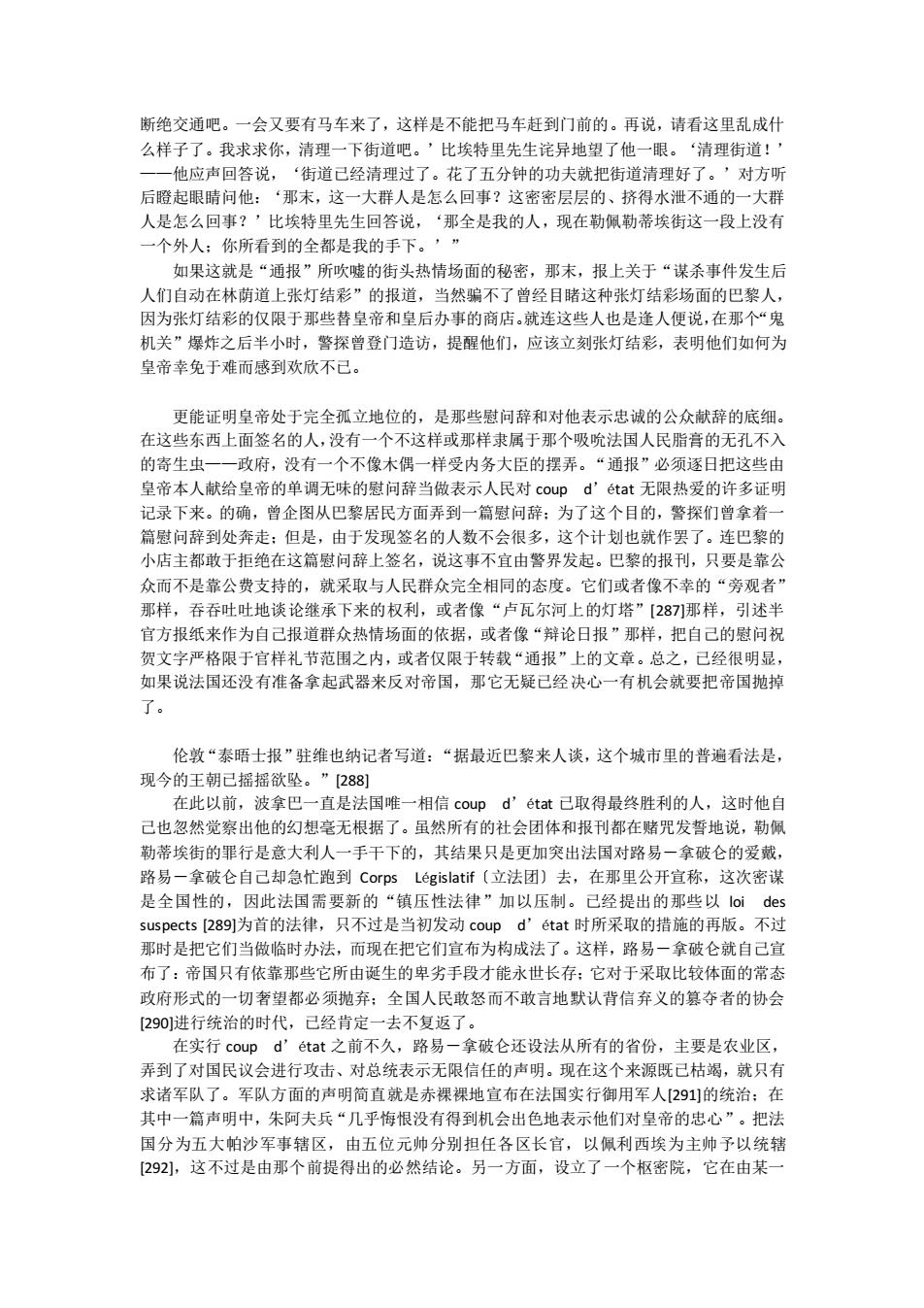
断绝交通吧。一会又要有马车来了,这样是不能把马车赶到门前的。再说,请看这里乱成什 么样子了。我求求你,清理一下街道吧。’比埃特里先生诧异地望了他一眼。‘清理街道!’ 一一他应声回答说,‘街道已经清理过了。花了五分钟的功夫就把街道清理好了。’对方听 后瞪起眼睛问他:‘那末,这一大群人是怎么回事?这密密层层的、挤得水泄不通的一大群 人是怎么回事?’比埃特里先生回答说,‘那全是我的人,现在勒佩勒蒂埃街这一段上没有 一个外人:你所看到的全都是我的手下。’” 如果这就是“通报”所吹嘘的街头热情场面的秘密,那末,报上关于“谋杀事件发生后 人们自动在林荫道上张灯结彩”的报道,当然骗不了曾经目睹这种张灯结彩场面的巴黎人, 因为张灯结彩的仅限于那些替皇帝和皇后办事的商店。就连这些人也是逢人便说,在那个“鬼 机关”爆炸之后半小时,警探曾登门造访,提醒他们,应该立刻张灯结彩,表明他们如何为 皇帝幸免于难而感到欢欣不己。 更能证明皇帝处于完全孤立地位的,是那些慰问辞和对他表示忠诚的公众献辞的底细。 在这些东西上面签名的人,没有一个不这样或那样隶属于那个吸吮法国人民脂膏的无孔不入 的寄生虫一一政府,没有一个不像木偶一样受内务大臣的摆弄。“通报”必须逐日把这些由 皇帝本人献给皇帝的单调无味的慰问辞当做表示人民对coup d'tat无限热爱的许多证明 记录下来。的确,曾企图从巴黎居民方面弄到一篇慰问辞:为了这个目的,警探们曾拿着一 篇慰问辞到处奔走:但是,由于发现签名的人数不会很多,这个计划也就作罢了。连巴黎的 小店主都敢于拒绝在这篇慰问辞上签名,说这事不宜由警界发起。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 众而不是靠公费支持的,就采取与人民群众完全相同的态度。它们或者像不幸的“旁观者” 那样,吞吞吐吐地谈论继承下来的权利,或者像“卢瓦尔河上的灯塔”[287]那样,引述半 官方报纸来作为自己报道群众热情场面的依据,或者像“辩论日报”那样,把自己的慰问祝 贺文字严格限于官样礼节范围之内,或者仅限于转载“通报”上的文章。总之,已经很明显, 如果说法国还没有准备拿起武器来反对帝国,那它无疑已经决心一有机会就要把帝国抛掉 了。 伦敦“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写道:“据最近巴黎来人谈,这个城市里的普遍看法是, 现今的王朝已摇摇欲坠。”[288] 在此以前,波拿巴一直是法国唯一相信coup d'état己取得最终胜利的人,这时他自 己也忽然觉察出他的幻想毫无根据了。虽然所有的社会团体和报刊都在赌咒发誓地说,勒佩 勒蒂埃街的罪行是意大利人一手干下的,其结果只是更加突出法国对路易一拿破仑的爱戴, 路易一拿破仑自己却急忙跑到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去,在那里公开宣称,这次密谋 是全国性的,因此法国需要新的“镇压性法律”加以压制。己经提出的那些以loi des suspects[289]为首的法律,只不过是当初发动coup d'etat时所采取的措施的再版。不过 那时是把它们当做临时办法,而现在把它们宣布为构成法了。这样,路易一拿破仑就自己宣 布了:帝国只有依靠那些它所由诞生的卑劣手段才能永世长存:它对于采取比较体面的常态 政府形式的一切奢望都必须抛弃: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默认背信弃义的篡夺者的协会 [290进行统治的时代,已经肯定一去不复返了。 在实行coup d'tat之前不久,路易一拿破仑还设法从所有的省份,主要是农业区, 弄到了对国民议会进行攻击、对总统表示无限信任的声明。现在这个来源既已枯竭,就只有 求诸军队了。军队方面的声明简直就是赤裸裸地宣布在法国实行御用军人[291]的统治:在 其中一篇声明中,朱阿夫兵“几乎悔恨没有得到机会出色地表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把法 国分为五大帕沙军事辖区,由五位元帅分别担任各区长官,以佩利西埃为主帅予以统辖 [292],这不过是由那个前提得出的必然结论。另一方面,设立了一个枢密院,它在由某一断绝交通吧。一会又要有马车来了,这样是不能把马车赶到门前的。再说,请看这里乱成什 么样子了。我求求你,清理一下街道吧。’比埃特里先生诧异地望了他一眼。‘清理街道!’ ——他应声回答说,‘街道已经清理过了。花了五分钟的功夫就把街道清理好了。’对方听 后瞪起眼睛问他:‘那末,这一大群人是怎么回事?这密密层层的、挤得水泄不通的一大群 人是怎么回事?’比埃特里先生回答说,‘那全是我的人,现在勒佩勒蒂埃街这一段上没有 一个外人;你所看到的全都是我的手下。’” 如果这就是“通报”所吹嘘的街头热情场面的秘密,那末,报上关于“谋杀事件发生后 人们自动在林荫道上张灯结彩”的报道,当然骗不了曾经目睹这种张灯结彩场面的巴黎人, 因为张灯结彩的仅限于那些替皇帝和皇后办事的商店。就连这些人也是逢人便说,在那个“鬼 机关”爆炸之后半小时,警探曾登门造访,提醒他们,应该立刻张灯结彩,表明他们如何为 皇帝幸免于难而感到欢欣不已。 更能证明皇帝处于完全孤立地位的,是那些慰问辞和对他表示忠诚的公众献辞的底细。 在这些东西上面签名的人,没有一个不这样或那样隶属于那个吸吮法国人民脂膏的无孔不入 的寄生虫——政府,没有一个不像木偶一样受内务大臣的摆弄。“通报”必须逐日把这些由 皇帝本人献给皇帝的单调无味的慰问辞当做表示人民对 coup d’état 无限热爱的许多证明 记录下来。的确,曾企图从巴黎居民方面弄到一篇慰问辞;为了这个目的,警探们曾拿着一 篇慰问辞到处奔走;但是,由于发现签名的人数不会很多,这个计划也就作罢了。连巴黎的 小店主都敢于拒绝在这篇慰问辞上签名,说这事不宜由警界发起。巴黎的报刊,只要是靠公 众而不是靠公费支持的,就采取与人民群众完全相同的态度。它们或者像不幸的“旁观者” 那样,吞吞吐吐地谈论继承下来的权利,或者像“卢瓦尔河上的灯塔”[287]那样,引述半 官方报纸来作为自己报道群众热情场面的依据,或者像“辩论日报”那样,把自己的慰问祝 贺文字严格限于官样礼节范围之内,或者仅限于转载“通报”上的文章。总之,已经很明显, 如果说法国还没有准备拿起武器来反对帝国,那它无疑已经决心一有机会就要把帝国抛掉 了。 伦敦“泰晤士报”驻维也纳记者写道:“据最近巴黎来人谈,这个城市里的普遍看法是, 现今的王朝已摇摇欲坠。”[288] 在此以前,波拿巴一直是法国唯一相信 coup d’état 已取得最终胜利的人,这时他自 己也忽然觉察出他的幻想毫无根据了。虽然所有的社会团体和报刊都在赌咒发誓地说,勒佩 勒蒂埃街的罪行是意大利人一手干下的,其结果只是更加突出法国对路易-拿破仑的爱戴, 路易-拿破仑自己却急忙跑到 Corps Législatif〔立法团〕去,在那里公开宣称,这次密谋 是全国性的,因此法国需要新的“镇压性法律”加以压制。已经提出的那些以 loi des suspects [289]为首的法律,只不过是当初发动 coup d’état 时所采取的措施的再版。不过 那时是把它们当做临时办法,而现在把它们宣布为构成法了。这样,路易-拿破仑就自己宣 布了:帝国只有依靠那些它所由诞生的卑劣手段才能永世长存;它对于采取比较体面的常态 政府形式的一切奢望都必须抛弃;全国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地默认背信弃义的篡夺者的协会 [290]进行统治的时代,已经肯定一去不复返了。 在实行 coup d’état 之前不久,路易-拿破仑还设法从所有的省份,主要是农业区, 弄到了对国民议会进行攻击、对总统表示无限信任的声明。现在这个来源既已枯竭,就只有 求诸军队了。军队方面的声明简直就是赤裸裸地宣布在法国实行御用军人[291]的统治;在 其中一篇声明中,朱阿夫兵“几乎悔恨没有得到机会出色地表示他们对皇帝的忠心”。把法 国分为五大帕沙军事辖区,由五位元帅分别担任各区长官,以佩利西埃为主帅予以统辖 [292],这不过是由那个前提得出的必然结论。另一方面,设立了一个枢密院,它在由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