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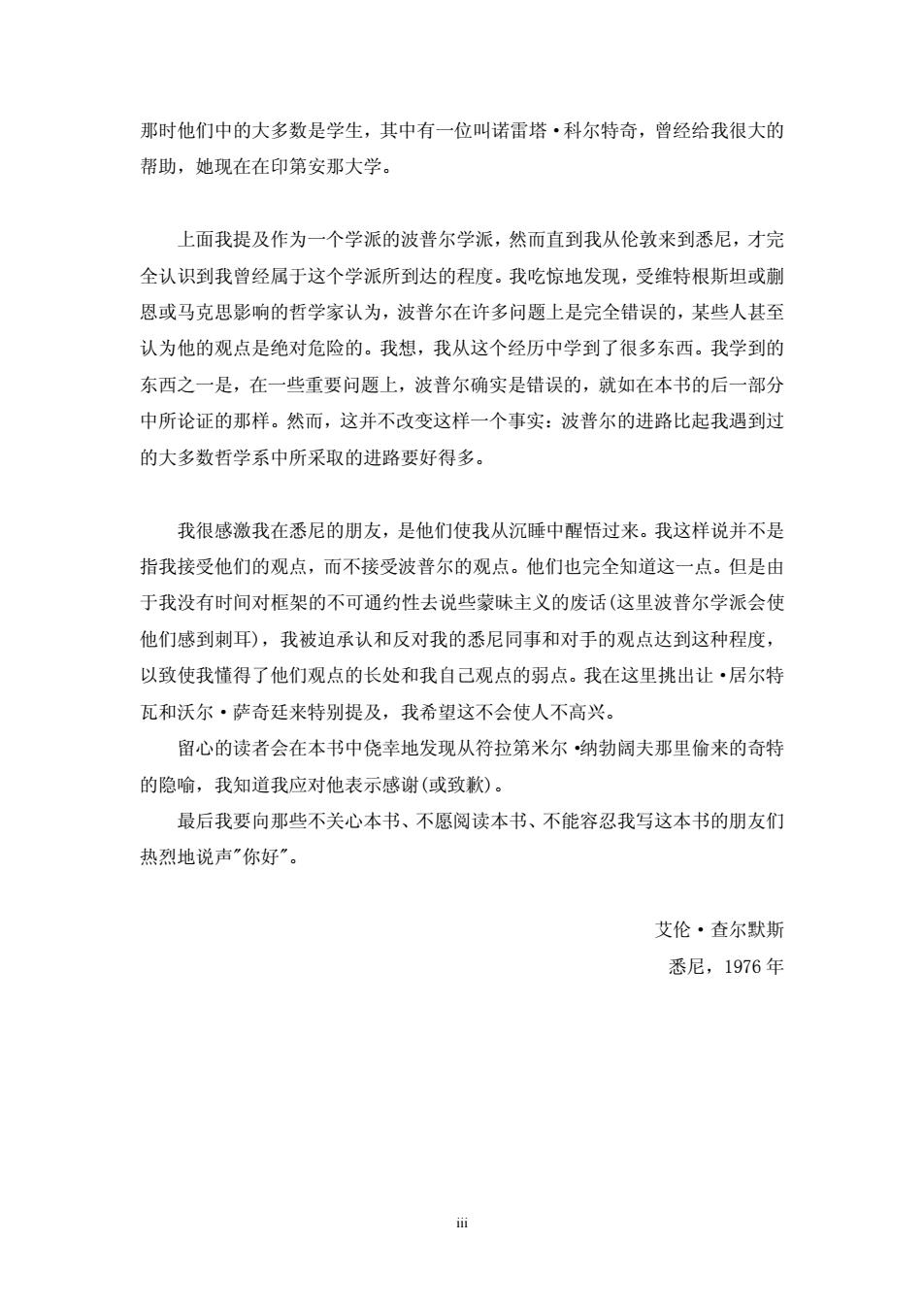
那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学生,其中有一位叫诺雷塔·科尔特奇,曾经给我很大的 帮助,她现在在印第安那大学。 上面我提及作为一个学派的波普尔学派,然而直到我从伦敦来到悉尼,才完 全认识到我曾经属于这个学派所到达的程度。我吃惊地发现,受维特根斯坦或蒯 恩或马克思影响的哲学家认为,波普尔在许多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某些人甚至 认为他的观点是绝对危险的。我想,我从这个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到的 东西之一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波普尔确实是错误的,就如在本书的后一部分 中所论证的那样。然而,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波普尔的进路比起我遇到过 的大多数哲学系中所采取的进路要好得多。 我很感激我在悉尼的朋友,是他们使我从沉睡中醒悟过来。我这样说并不是 指我接受他们的观点,而不接受波普尔的观点。他们也完全知道这一点。但是由 于我没有时间对框架的不可通约性去说些蒙昧主义的废话(这里波普尔学派会使 他们感到刺耳),我被迫承认和反对我的悉尼同事和对手的观点达到这种程度, 以致使我懂得了他们观点的长处和我自己观点的弱点。我在这里挑出让·居尔特 瓦和沃尔·萨奇廷来特别提及,我希望这不会使人不高兴。 留心的读者会在本书中侥幸地发现从符拉第米尔纳勃阔夫那里偷来的奇特 的隐喻,我知道我应对他表示感谢(或致歉)。 最后我要向那些不关心本书、不愿阅读本书、不能容忍我写这本书的朋友们 热烈地说声”你好”。 艾伦·查尔默斯 悉尼,1976年 公那时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学生,其中有一位叫诺雷塔·科尔特奇,曾经给我很大的 帮助,她现在在印第安那大学。 上面我提及作为一个学派的波普尔学派,然而直到我从伦敦来到悉尼,才完 全认识到我曾经属于这个学派所到达的程度。我吃惊地发现,受维特根斯坦或蒯 恩或马克思影响的哲学家认为,波普尔在许多问题上是完全错误的,某些人甚至 认为他的观点是绝对危险的。我想,我从这个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到的 东西之一是,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波普尔确实是错误的,就如在本书的后一部分 中所论证的那样。然而,这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波普尔的进路比起我遇到过 的大多数哲学系中所采取的进路要好得多。 我很感激我在悉尼的朋友,是他们使我从沉睡中醒悟过来。我这样说并不是 指我接受他们的观点,而不接受波普尔的观点。他们也完全知道这一点。但是由 于我没有时间对框架的不可通约性去说些蒙昧主义的废话(这里波普尔学派会使 他们感到刺耳),我被迫承认和反对我的悉尼同事和对手的观点达到这种程度, 以致使我懂得了他们观点的长处和我自己观点的弱点。我在这里挑出让·居尔特 瓦和沃尔·萨奇廷来特别提及,我希望这不会使人不高兴。 留心的读者会在本书中侥幸地发现从符拉第米尔·纳勃阔夫那里偷来的奇特 的隐喻,我知道我应对他表示感谢(或致歉)。 最后我要向那些不关心本书、不愿阅读本书、不能容忍我写这本书的朋友们 热烈地说声"你好"。 艾伦·查尔默斯 悉尼,1976 年 i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