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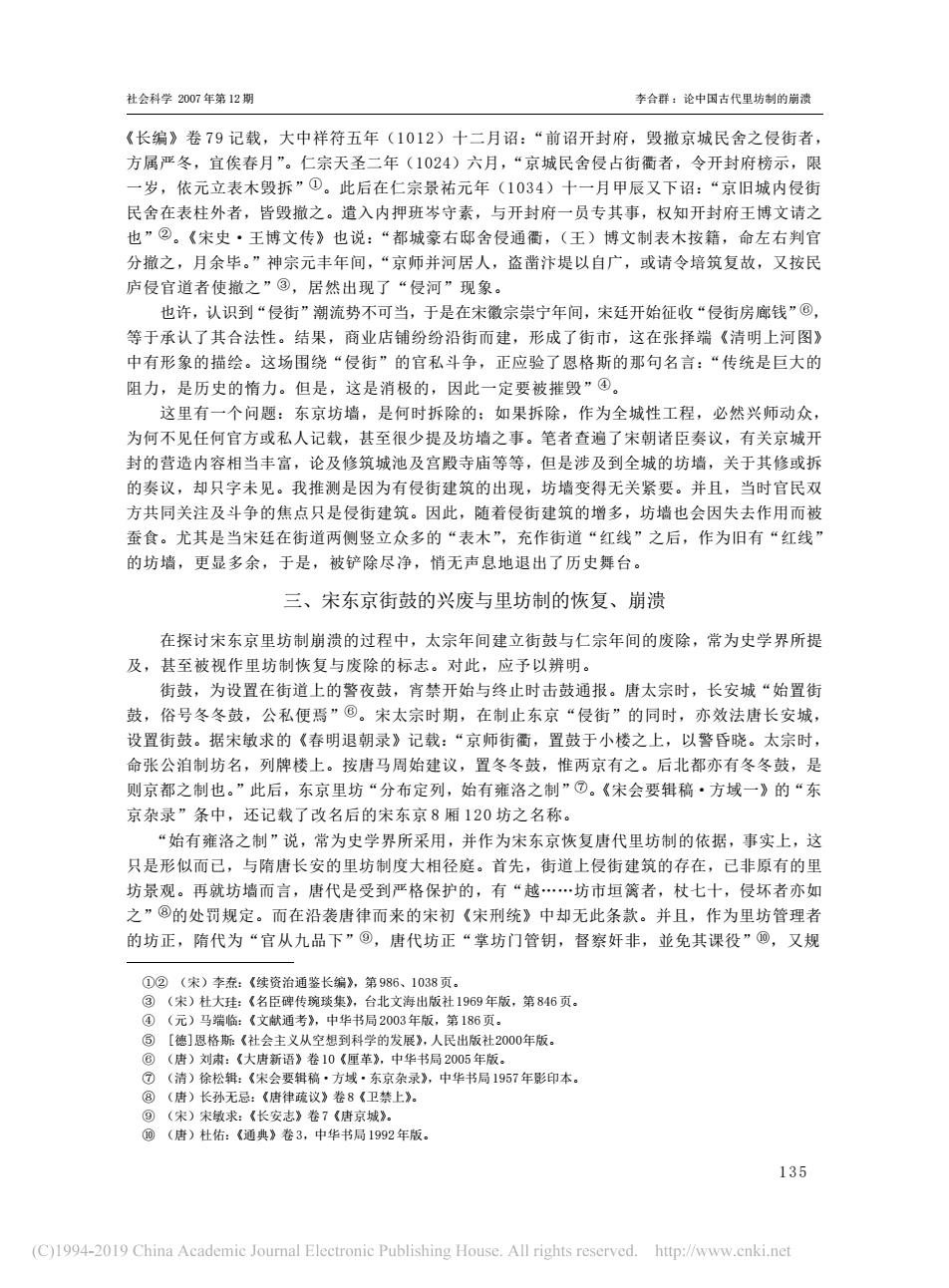
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李合群:论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崩溃 《长编》卷79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 方属严冬,宜俟春月”。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 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①。此后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甲辰又下诏:“京旧城内侵街 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遣入内押班岑守素,与开封府一员专其事,权知开封府王博文请之 也”②。《宋史·王博文传》也说:“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王)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 分撤之,月余毕。”神宗元丰年间,“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 庐侵官道者使撤之”③,居然出现了“侵河”现象。 也许,认识到“侵街”潮流势不可当,于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宋廷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 等于承认了其合法性。结果,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形成了街市,这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中有形象的描绘。这场围绕“侵街”的官私斗争,正应验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传统是巨大的 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但是,这是消极的,因此一定要被摧毁”④。 这里有一个问题:东京坊墙,是何时拆除的:如果拆除,作为全城性工程,必然兴师动众, 为何不见任何官方或私人记载,甚至很少提及坊墙之事。笔者查遍了宋朝诸臣奏议,有关京城开 封的营造内容相当丰富,论及修筑城池及宫殿寺庙等等,但是涉及到全城的坊墙,关于其修或拆 的奏议,却只字未见。我推测是因为有侵街建筑的出现,坊墙变得无关紧要。并且,当时官民双 方共同关注及斗争的焦点只是侵街建筑。因此,随着侵街建筑的增多,坊墙也会因失去作用而被 蚕食。尤其是当宋廷在街道两侧竖立众多的“表木”,充作街道“红线”之后,作为旧有“红线” 的坊墙,更显多余,于是,被铲除尽净,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宋东京街鼓的兴废与里坊制的恢复、崩溃 在探讨宋东京里坊制崩溃的过程中,太宗年间建立街鼓与仁宗年间的废除,常为史学界所提 及,甚至被视作里坊制恢复与废除的标志。对此,应予以辨明。 街鼓,为设置在街道上的警夜鼓,宵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唐太宗时,长安城“始置街 鼓,俗号冬冬鼓,公私便焉”©。宋太宗时期,在制止东京“侵街”的同时,亦效法唐长安城, 设置街鼓。据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记载:“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 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 则京都之制也。”此后,东京里坊“分布定列,始有雍洛之制”⑦。《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的“东 京杂录”条中,还记载了改名后的宋东京8厢120坊之名称。 “始有雍洛之制”说,常为史学界所采用,并作为宋东京恢复唐代里坊制的依据,事实上,这 只是形似而已,与隋唐长安的里坊制度大相径庭。首先,街道上侵街建筑的存在,已非原有的里 坊景观。再就坊墙而言,唐代是受到严格保护的,有“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 之”⑧的处罚规定。而在沿袭唐律而来的宋初《宋刑统》中却无此条款。并且,作为里坊管理者 的坊正,隋代为“官从九品下”⑨,唐代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並免其课役”⑩,又规 ①②(宋)李煮:《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86、1038页。 ③(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846页。 ④(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86页。 同[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中华书局2005年版。 ⑦(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东京杂录》,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⑧(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8《卫禁上》。 ⑨(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唐京城》。 ⑩(唐)杜佑:《通典》卷3,中华书局1992年版。 135 (C)1994-201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社会科学 2007 年第 12 期 135 《长编》卷 7 9 记载,大中祥符五年(1012)十二月诏:“前诏开封府,毁撤京城民舍之侵街者, 方属严冬,宜俟春月”。仁宗天圣二年(1024)六月,“京城民舍侵占街衢者,令开封府榜示,限 一岁,依元立表木毁拆”①。此后在仁宗景祐元年(1034)十一月甲辰又下诏:“京旧城内侵街 民舍在表柱外者,皆毁撤之。遣入内押班岑守素,与开封府一员专其事,权知开封府王博文请之 也”②。《宋史·王博文传》也说:“都城豪右邸舍侵通衢,(王)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 分撤之,月余毕。”神宗元丰年间,“京师并河居人,盗凿汴堤以自广,或请令培筑复故,又按民 庐侵官道者使撤之”③,居然出现了“侵河”现象。 也许,认识到“侵街”潮流势不可当,于是在宋徽宗崇宁年间,宋廷开始征收“侵街房廊钱”⑥, 等于承认了其合法性。结果,商业店铺纷纷沿街而建,形成了街市,这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中有形象的描绘。这场围绕“侵街”的官私斗争,正应验了恩格斯的那句名言:“传统是巨大的 阻力,是历史的惰力。但是,这是消极的,因此一定要被摧毁”④。 这里有一个问题:东京坊墙,是何时拆除的;如果拆除,作为全城性工程,必然兴师动众, 为何不见任何官方或私人记载,甚至很少提及坊墙之事。笔者查遍了宋朝诸臣奏议,有关京城开 封的营造内容相当丰富,论及修筑城池及宫殿寺庙等等,但是涉及到全城的坊墙,关于其修或拆 的奏议,却只字未见。我推测是因为有侵街建筑的出现,坊墙变得无关紧要。并且,当时官民双 方共同关注及斗争的焦点只是侵街建筑。因此,随着侵街建筑的增多,坊墙也会因失去作用而被 蚕食。尤其是当宋廷在街道两侧竖立众多的“表木”,充作街道“红线”之后,作为旧有“红线” 的坊墙,更显多余,于是,被铲除尽净,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宋东京街鼓的兴废与里坊制的恢复、崩溃 在探讨宋东京里坊制崩溃的过程中,太宗年间建立街鼓与仁宗年间的废除,常为史学界所提 及,甚至被视作里坊制恢复与废除的标志。对此,应予以辨明。 街鼓,为设置在街道上的警夜鼓,宵禁开始与终止时击鼓通报。唐太宗时,长安城“始置街 鼓,俗号冬冬鼓,公私便焉”⑥。宋太宗时期,在制止东京“侵街”的同时,亦效法唐长安城, 设置街鼓。据宋敏求的《春明退朝录》记载:“京师街衢,置鼓于小楼之上,以警昏晓。太宗时, 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楼上。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惟两京有之。后北都亦有冬冬鼓,是 则京都之制也。”此后,东京里坊“分布定列,始有雍洛之制”⑦。《宋会要辑稿·方域一》的“东 京杂录”条中,还记载了改名后的宋东京 8 厢 120 坊之名称。 “始有雍洛之制”说,常为史学界所采用,并作为宋东京恢复唐代里坊制的依据,事实上,这 只是形似而已,与隋唐长安的里坊制度大相径庭。首先,街道上侵街建筑的存在,已非原有的里 坊景观。再就坊墙而言,唐代是受到严格保护的,有“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 之”⑧的处罚规定。而在沿袭唐律而来的宋初《宋刑统》中却无此条款。并且,作为里坊管理者 的坊正,隋代为“官从九品下”⑨,唐代坊正“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並免其课役”⑩,又规 ①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986、1038页。 ③ (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846页。 ④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华书局 2003年版,第186页。 ⑤ [德]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⑥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10《厘革》,中华书局 2005年版。 ⑦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方域·东京杂录》,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 ⑧ (唐)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8《卫禁上》。 ⑨ (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唐京城》。 ⑩ (唐)杜佑:《通典》卷3,中华书局 1992年版。 李合群 :论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