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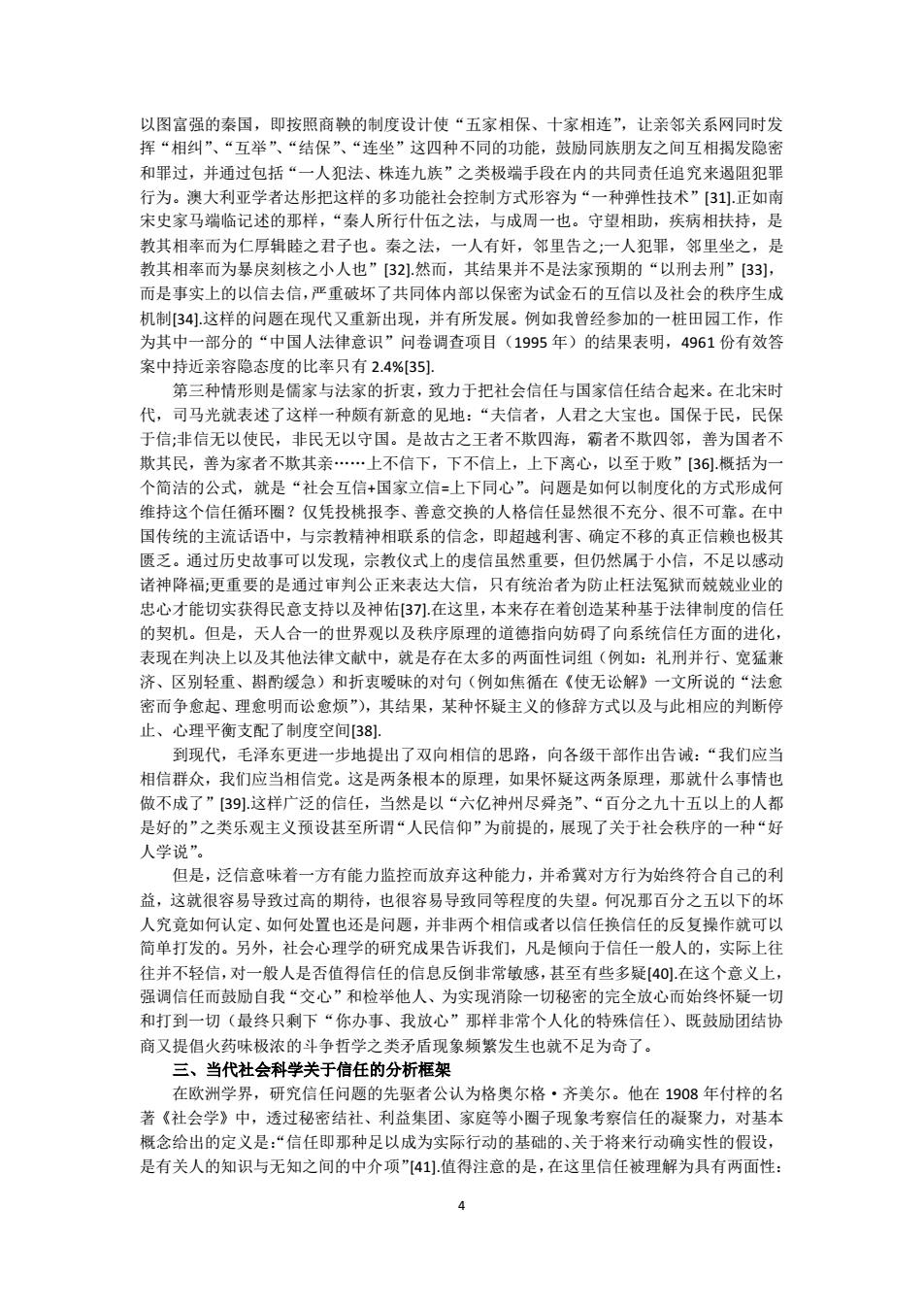
以图富强的秦国,即按照商鞅的制度设计使“五家相保、十家相连”,让亲邻关系网同时发 挥“相纠”、“互举”、“结保”、“连坐”这四种不同的功能,鼓励同族朋友之间互相揭发隐密 和罪过,并通过包括“一人犯法、株连九族”之类极端手段在内的共同责任追究来遏阻犯罪 行为。澳大利亚学者达彤把这样的多功能社会控制方式形容为“一种弹性技术”[31].正如南 宋史家马端临记述的那样,“秦人所行什伍之法,与成周一也。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 教其相率而为仁厚辑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是 教其相率而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32]然而,其结果并不是法家预期的“以刑去刑”[33], 而是事实上的以信去信,严重破坏了共同体内部以保密为试金石的互信以及社会的秩序生成 机制[34]这样的问题在现代又重新出现,并有所发展。例如我曾经参加的一桩田园工作,作 为其中一部分的“中国人法律意识”问卷调查项目(1995年)的结果表明,4961份有效答 案中持近亲容隐态度的比率只有2.4%[35]. 第三种情形则是儒家与法家的折衷,致力于把社会信任与国家信任结合起来。在北宋时 代,司马光就表述了这样一种颇有新意的见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 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 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36概括为一 个简洁的公式,就是“社会互信+国家立信=上下同心”。问题是如何以制度化的方式形成何 维持这个信任循环圈?仅凭投桃报李、善意交换的人格信任显然很不充分、很不可靠。在中 国传统的主流话语中,与宗教精神相联系的信念,即超越利害、确定不移的真正信赖也极其 匮乏。通过历史故事可以发现,宗教仪式上的虔信虽然重要,但仍然属于小信,不足以感动 诸神降福;更重要的是通过审判公正来表达大信,只有统治者为防止枉法冤狱而兢兢业业的 忠心才能切实获得民意支持以及神佑37]在这里,本来存在着创造某种基于法律制度的信任 的契机。但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以及秩序原理的道德指向妨碍了向系统信任方面的进化, 表现在判决上以及其他法律文献中,就是存在太多的两面性词组(例如:礼刑并行、宽猛兼 济、区别轻重、斟酌缓急)和折衷暖味的对句(例如焦循在《使无讼解》一文所说的“法愈 密而争愈起、理愈明而讼愈烦”),其结果,某种怀疑主义的修辞方式以及与此相应的判断停 止、心理平衡支配了制度空间[38]. 到现代,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双向相信的思路,向各级干部作出告诫:“我们应当 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 做不成了”[39]这样广泛的信任,当然是以“六亿神州尽舜尧”、“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 是好的”之类乐观主义预设甚至所谓“人民信仰”为前提的,展现了关于社会秩序的一种“好 人学说”。 但是,泛信意味着一方有能力监控而放弃这种能力,并希冀对方行为始终符合自己的利 益,这就很容易导致过高的期待,也很容易导致同等程度的失望。何况那百分之五以下的坏 人究竟如何认定、如何处置也还是问题,并非两个相信或者以信任换信任的反复操作就可以 简单打发的。另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凡是倾向于信任一般人的,实际上往 往并不轻信,对一般人是否值得信任的信息反倒非常敏感,甚至有些多疑[40]在这个意义上, 强调信任而鼓励自我“交心”和检举他人、为实现消除一切秘密的完全放心而始终怀疑一切 和打到一切(最终只剩下“你办事、我放心”那样非常个人化的特殊信任)、既鼓励团结协 商又提倡火药味极浓的斗争哲学之类矛盾现象频繁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当代社会科学关于信任的分析框架 在欧洲学界,研究信任问题的先驱者公认为格奥尔格·齐美尔。他在1908年付梓的名 著《社会学》中,透过秘密结社、利益集团、家庭等小圈子现象考察信任的凝聚力,对基本 概念给出的定义是:“信任即那种足以成为实际行动的基础的、关于将来行动确实性的假设, 是有关人的知识与无知之间的中介项”[41]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信任被理解为具有两面性:4 以图富强的秦国,即按照商鞅的制度设计使“五家相保、十家相连”,让亲邻关系网同时发 挥“相纠”、“互举”、“结保”、“连坐”这四种不同的功能,鼓励同族朋友之间互相揭发隐密 和罪过,并通过包括“一人犯法、株连九族”之类极端手段在内的共同责任追究来遏阻犯罪 行为。澳大利亚学者达彤把这样的多功能社会控制方式形容为“一种弹性技术”[31].正如南 宋史家马端临记述的那样,“秦人所行什伍之法,与成周一也。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 教其相率而为仁厚辑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奸,邻里告之;一人犯罪,邻里坐之,是 教其相率而为暴戾刻核之小人也”[32].然而,其结果并不是法家预期的“以刑去刑”[33], 而是事实上的以信去信,严重破坏了共同体内部以保密为试金石的互信以及社会的秩序生成 机制[34].这样的问题在现代又重新出现,并有所发展。例如我曾经参加的一桩田园工作,作 为其中一部分的“中国人法律意识”问卷调查项目(1995 年)的结果表明,4961 份有效答 案中持近亲容隐态度的比率只有 2.4%[35]. 第三种情形则是儒家与法家的折衷,致力于把社会信任与国家信任结合起来。在北宋时 代,司马光就表述了这样一种颇有新意的见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 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 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36].概括为一 个简洁的公式,就是“社会互信+国家立信=上下同心”。问题是如何以制度化的方式形成何 维持这个信任循环圈?仅凭投桃报李、善意交换的人格信任显然很不充分、很不可靠。在中 国传统的主流话语中,与宗教精神相联系的信念,即超越利害、确定不移的真正信赖也极其 匮乏。通过历史故事可以发现,宗教仪式上的虔信虽然重要,但仍然属于小信,不足以感动 诸神降福;更重要的是通过审判公正来表达大信,只有统治者为防止枉法冤狱而兢兢业业的 忠心才能切实获得民意支持以及神佑[37].在这里,本来存在着创造某种基于法律制度的信任 的契机。但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以及秩序原理的道德指向妨碍了向系统信任方面的进化, 表现在判决上以及其他法律文献中,就是存在太多的两面性词组(例如:礼刑并行、宽猛兼 济、区别轻重、斟酌缓急)和折衷暧昧的对句(例如焦循在《使无讼解》一文所说的“法愈 密而争愈起、理愈明而讼愈烦”),其结果,某种怀疑主义的修辞方式以及与此相应的判断停 止、心理平衡支配了制度空间[38]. 到现代,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双向相信的思路,向各级干部作出告诫:“我们应当 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 做不成了”[39].这样广泛的信任,当然是以“六亿神州尽舜尧”、“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都 是好的”之类乐观主义预设甚至所谓“人民信仰”为前提的,展现了关于社会秩序的一种“好 人学说”。 但是,泛信意味着一方有能力监控而放弃这种能力,并希冀对方行为始终符合自己的利 益,这就很容易导致过高的期待,也很容易导致同等程度的失望。何况那百分之五以下的坏 人究竟如何认定、如何处置也还是问题,并非两个相信或者以信任换信任的反复操作就可以 简单打发的。另外,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凡是倾向于信任一般人的,实际上往 往并不轻信,对一般人是否值得信任的信息反倒非常敏感,甚至有些多疑[40].在这个意义上, 强调信任而鼓励自我“交心”和检举他人、为实现消除一切秘密的完全放心而始终怀疑一切 和打到一切(最终只剩下“你办事、我放心”那样非常个人化的特殊信任)、既鼓励团结协 商又提倡火药味极浓的斗争哲学之类矛盾现象频繁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当代社会科学关于信任的分析框架 在欧洲学界,研究信任问题的先驱者公认为格奥尔格·齐美尔。他在 1908 年付梓的名 著《社会学》中,透过秘密结社、利益集团、家庭等小圈子现象考察信任的凝聚力,对基本 概念给出的定义是:“信任即那种足以成为实际行动的基础的、关于将来行动确实性的假设, 是有关人的知识与无知之间的中介项”[41].值得注意的是,在这里信任被理解为具有两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