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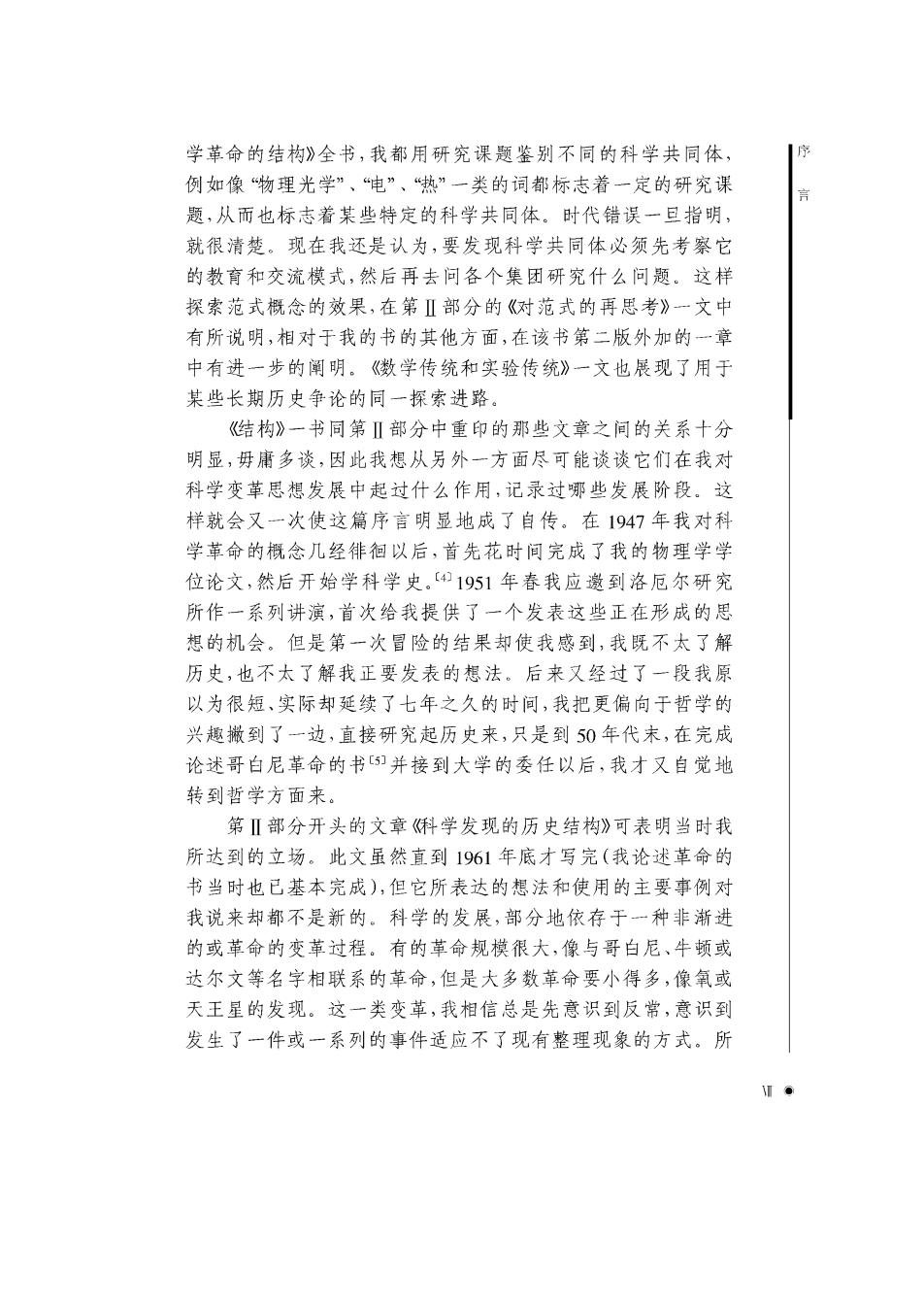
学革命的结构》全书,我都用研究课题鉴别不同的科学共同体, 序 例如像“物理光学”、“电”、“热”一类的词都标志着一定的研究课 言 题,从而也标志着某些特定的科学共同体。时代错误一旦指明, 就很清楚。现在我还是认为,要发现科学共同体必须先考察它 的教育和交流模式,然后再去问各个集团研究什么问题。这样 探索范式概念的效果,在第Ⅱ部分的《对范式的再思考》一文中 有所说明,相对于我的书的其他方面,在该书第二版外加的一章 中有进一步的阐明。《数学传统和实验传统》一文也展现了用于 某些长期历史争论的同一探索进路。 《结构》一书同第Ⅱ部分中重印的那些文章之间的关系十分 明显,毋庸多谈,因此我想从另外一方面尽可能谈谈它们在我对 科学变革思想发展中起过什么作用,记录过哪些发展阶段。这 样就会又一次使这篇序言明显地成了自传。在1947年我对科 学革命的概念几经徘徊以后,首先花时间完成了我的物理学学 位论文,然后开始学科学史。〔41951年春我应邀到洛厄尔研究 所作一系列讲演,首次给我提供了一个发表这些正在形成的思 想的机会。但是第一次冒险的结果却使我感到,我既不太了解 历史,也不太了解我正要发表的想法。后来又经过了一段我原 以为很短、实际却延续了七年之久的时间,我把更偏向于哲学的 兴趣撇到了一边,直接研究起历史来,只是到50年代末,在完成 论述哥白尼革命的书[5并接到大学的委任以后,我才又自觉地 转到哲学方面来。 第Ⅱ部分开头的文章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可表明当时我 所达到的立场。此文虽然直到1961年底才写完(我论述革命的 书当时也已基本完成),但它所表达的想法和使用的主要事例对 我说来却都不是新的。科学的发展,部分地依存于一种非渐进 的或革命的变革过程。有的革命规模很大,像与哥白尼、牛顿或 达尔文等名字相联系的革命,但是大多数革命要小得多,像氧或 天王星的发现。这一类变革,我相信总是先意识到反常,意识到 发生了一件或一系列的事件适应不了现有整理现象的方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