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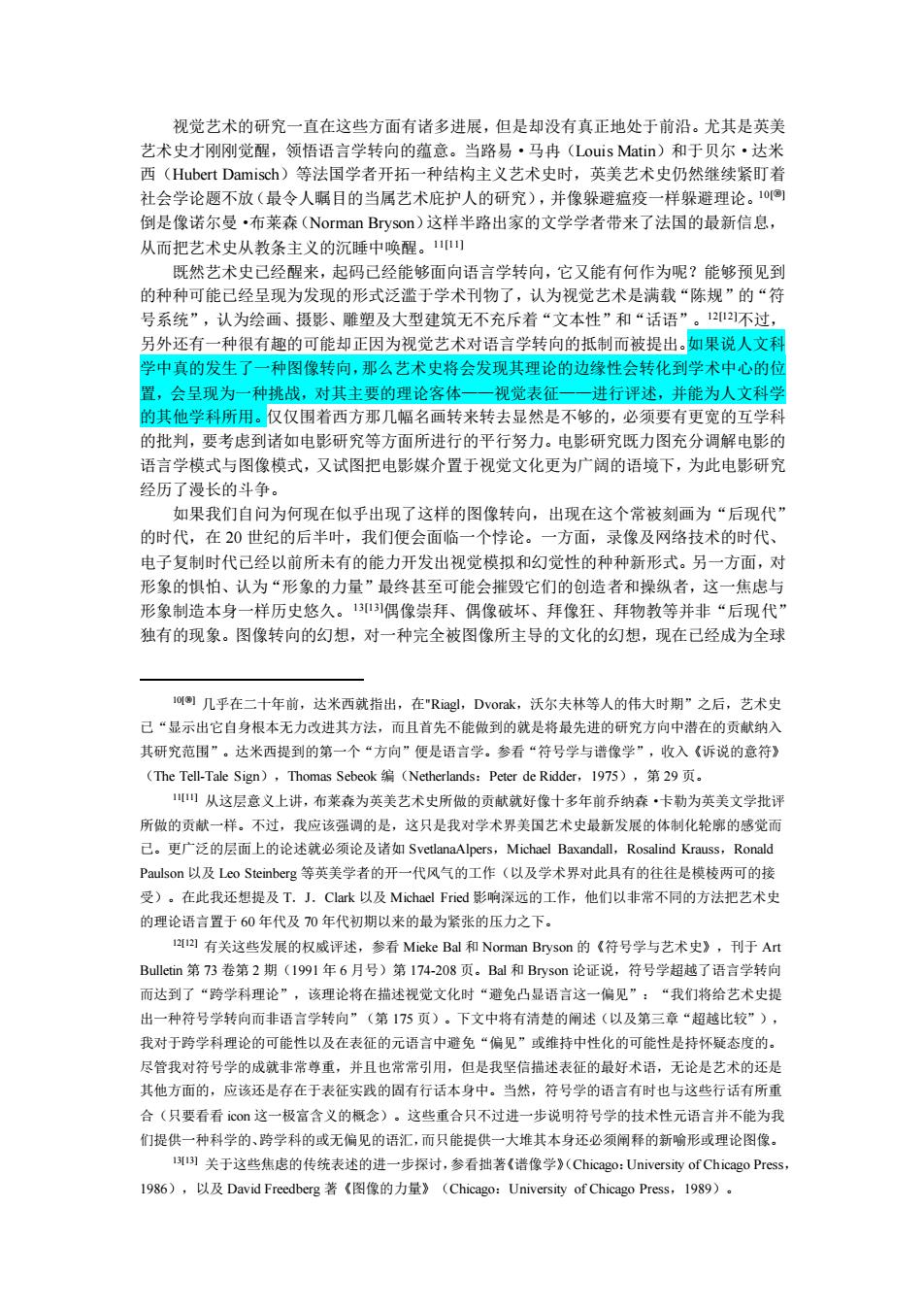
视微艺术的研究一直在这些方面右诸多讲展,但是却沿右直正恤处于前沿。北其是革望 艺术史才刚刚觉 悟语言学转 向的蕴意。当路易·马 Matin 和于贝尔 达米 西(Hubert Damisch 等法国学者开拓一种结构主义艺术史时,英美艺术史仍然继续紧町者 社会学论题不放(最令人瞩目的当属艺术庇护人的研究),并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理论。 倒是像诺尔曼·布莱森(Norman Bryson)这样半路出家的文学学者带来了法国的最新信息, 从而把艺术史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晚阴。1川 既然艺术史已经醒来,起码已经能够面向语言学转向,它又能有何作为呢?能够预见到 的种种可能已经呈现为发现的 形式泛滥于学术刊物了,认为视觉艺术是满载“陈规”的“符 号系统”,认为绘画、摄影、塑及大型建筑无不充斥着“文本性”和“话语” 。22不过 另外还有一种很有趣的可能却正因为视觉艺术对语言学转向的抵制而被提出。如果说人文科 学中真的发生了一种图像转向,那么艺术史将会发现其理论的边缘性会转化到学术中心的 进行评述,并能为人文科 的其他学 。仅仅围着西方那几幅名画转来转去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更宽的互学利 的批判,要考虑到诸如电影研究等方面所进行的平行努力。电影研究既力图充分调解电影的 语言学模式与图像模式,又试图把电影媒介置于视觉文化更为广阔的语境下,为此电影研究 经历了漫长的斗争。 如果我们白间为何现在似平出现了这样的图像转向,出现在这个常被刻画为“后现代 的时代,在20世纪的后半叶,我们便会面临 个论 一方面,录像及网络技术的时代 电子复制时代已经以前所未有的能力开发出视觉模拟和幻觉性的种种新形式。另一方面,对 形象的惧怕、认为“形象的力量”最终甚至可能会摧毁它们的创造者和操纵者,这一焦虑与 形象制造本身一样历史悠久。偶像崇拜、偶像破坏、拜像狂、拜物教等并非“后现代 独有的现象。图像转向的幻想,对一种完全被图像所主导的文化的幻想,现在已经成为全球 几乎在二十年前,达米西就指 k,沃尔夫林等人的伟大时期”之后,艺术 已“显示出它自身根本无力改进其方法 而且首先不能做到的就是将最先进的研究方向中潜在的贡献纳 其研究范用 达米西提到的第一个“方向”使是语言学。参看“符号学与语像学” ,收入《诉说的意符》 (The Tell-Tale Sign),Thomas Sebeok (Netherlands:Peter de Ridder,1975).29. 训从这层意义上讲,布莱森为英美艺术史所做的贡献袜好像十多年前乔纳森·卡勒为英美文学批评 所做的一样。不过,我应该调的是,议只是我对学术界关国艺术中最新发展的体化轮的感觉 己。更广泛的层面上的论述就必须论及请如 m以及Leo Stcinberg等英美学者的开一代风气的工作(以及学术界对此具有的往往是模棱两可的 受)。在此我还想提及T.J.Clark以及Michael Fried影响深远的工作,他们以非常不同的方法把艺术生 的理论语言置于60年代及7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为紧张的压力之下, 】有关这此发展的权威球,参看Mieke Bal和Norman B 0的《符号学与艺术史》,刊于A Bum第73卷第2期(191年6月号)第174208页.Ba和Bn0m论证说,符号学超 了语学转向 而达到了 “跨学科理询 该理论将在描述视觉文化时“卷免凸显语言这 偏见“ 我们将给艺术史封 出一种符号学转向而非语言学转向”(第175页)·下文中将有清楚的闸述(以及第三章“超越比较”) 我对于骑学科理论的可能性以及在表征的元语言中避免“偏见”或维持中性化的可能性是持怀疑态度的 尽管我对符号学的成就非常尊重,并且也常常引用,但是我坚信描述表征的最好术语,无论是艺术的还是 其他方面的,应该还是存在于表征实践的因有行话本身中,当然,符号学的语言有时也与这些行话有所重 合(只要看看iom这一极富含义的概念) ,这些重合只不过进一步说明符号学的技术性元语言并不能为我 们提供一种科学的、跨学科的或无偏见的语汇,而只能提供一大堆其本身还必须闸释的新喻形或理论图像 11]关于这些焦虑的传统表述的进一步探讨,参看拙著《谱像学》(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以及David Freedberg若《图像的力量》(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视觉艺术的研究一直在这些方面有诸多进展,但是却没有真正地处于前沿。尤其是英美 艺术史才刚刚觉醒,领悟语言学转向的蕴意。当路易·马冉(Louis Matin)和于贝尔·达米 西(Hubert Damisch)等法国学者开拓一种结构主义艺术史时,英美艺术史仍然继续紧盯着 社会学论题不放(最令人瞩目的当属艺术庇护人的研究),并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理论。10[⑩] 倒是像诺尔曼·布莱森(Norman Bryson)这样半路出家的文学学者带来了法国的最新信息, 从而把艺术史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唤醒。11[11] 既然艺术史已经醒来,起码已经能够面向语言学转向,它又能有何作为呢?能够预见到 的种种可能已经呈现为发现的形式泛滥于学术刊物了,认为视觉艺术是满载“陈规”的“符 号系统”,认为绘画、摄影、雕塑及大型建筑无不充斥着“文本性”和“话语”。12[12]不过, 另外还有一种很有趣的可能却正因为视觉艺术对语言学转向的抵制而被提出。如果说人文科 学中真的发生了一种图像转向,那么艺术史将会发现其理论的边缘性会转化到学术中心的位 置,会呈现为一种挑战,对其主要的理论客体——视觉表征——进行评述,并能为人文科学 的其他学科所用。仅仅围着西方那几幅名画转来转去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更宽的互学科 的批判,要考虑到诸如电影研究等方面所进行的平行努力。电影研究既力图充分调解电影的 语言学模式与图像模式,又试图把电影媒介置于视觉文化更为广阔的语境下,为此电影研究 经历了漫长的斗争。 如果我们自问为何现在似乎出现了这样的图像转向,出现在这个常被刻画为“后现代” 的时代,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我们便会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录像及网络技术的时代、 电子复制时代已经以前所未有的能力开发出视觉模拟和幻觉性的种种新形式。另一方面,对 形象的惧怕、认为“形象的力量”最终甚至可能会摧毁它们的创造者和操纵者,这一焦虑与 形象制造本身一样历史悠久。13[13]偶像崇拜、偶像破坏、拜像狂、拜物教等并非“后现代” 独有的现象。图像转向的幻想,对一种完全被图像所主导的文化的幻想,现在已经成为全球 10[⑩] 几乎在二十年前,达米西就指出,在"Riagl,Dvorak,沃尔夫林等人的伟大时期”之后,艺术史 已“显示出它自身根本无力改进其方法,而且首先不能做到的就是将最先进的研究方向中潜在的贡献纳入 其研究范围”。达米西提到的第一个“方向”便是语言学。参看“符号学与谱像学”,收入《诉说的意符》 (The Tell-Tale Sign),Thomas Sebeok 编(Netherlands:Peter de Ridder,1975),第 29 页。 11[11] 从这层意义上讲,布莱森为英美艺术史所做的贡献就好像十多年前乔纳森·卡勒为英美文学批评 所做的贡献一样。不过,我应该强调的是,这只是我对学术界美国艺术史最新发展的体制化轮廓的感觉而 已。更广泛的层面上的论述就必须论及诸如 SvetlanaAlpers,Michael Baxandall,Rosalind Krauss,Ronald Paulson 以及 Leo Steinberg 等英美学者的开一代风气的工作(以及学术界对此具有的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接 受)。在此我还想提及 T.J.Clark 以及 Michael Fried 影响深远的工作,他们以非常不同的方法把艺术史 的理论语言置于 60 年代及 70 年代初期以来的最为紧张的压力之下。 12[12] 有关这些发展的权威评述,参看 Mieke Bal 和 Norman Bryson 的《符号学与艺术史》,刊于 Art Bulletin 第 73 卷第 2 期(1991 年 6 月号)第 174-208 页。Bal 和 Bryson 论证说,符号学超越了语言学转向 而达到了“跨学科理论”,该理论将在描述视觉文化时“避免凸显语言这一偏见”:“我们将给艺术史提 出一种符号学转向而非语言学转向”(第 175 页)。下文中将有清楚的阐述(以及第三章“超越比较”), 我对于跨学科理论的可能性以及在表征的元语言中避免“偏见”或维持中性化的可能性是持怀疑态度的。 尽管我对符号学的成就非常尊重,并且也常常引用,但是我坚信描述表征的最好术语,无论是艺术的还是 其他方面的,应该还是存在于表征实践的固有行话本身中。当然,符号学的语言有时也与这些行话有所重 合(只要看看 icon 这一极富含义的概念)。这些重合只不过进一步说明符号学的技术性元语言并不能为我 们提供一种科学的、跨学科的或无偏见的语汇,而只能提供一大堆其本身还必须阐释的新喻形或理论图像。 13[13] 关于这些焦虑的传统表述的进一步探讨,参看拙著《谱像学》(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以及 David Freedberg 著《图像的力量》(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