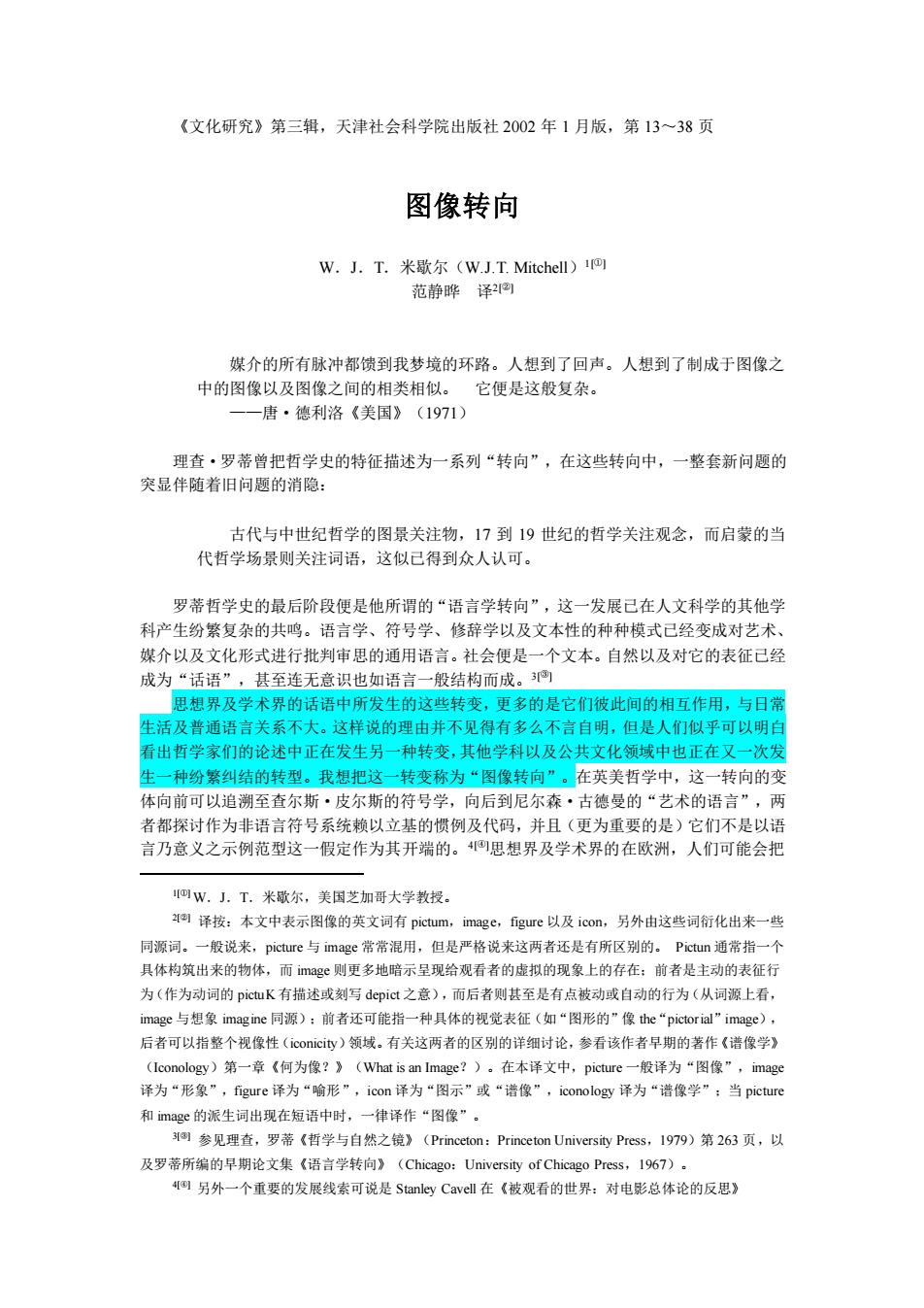
《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3~38页 图像转向 w.J.T.米歇尔(WJ.T.Mitchell)四 范静修译到 媒介的所有脉冲都馈到我梦境的环路。人想到了回声。人想到了制成于图像之 中的图像以及图像之间的相类相似。它便是这般复杂。 一一唐·德利洛《美国》(1971) 理查·罗蒂曾把哲学史的特征描述为一系列“转向”,在这些转向中,一整套新问题的 突显伴随着旧问题的消隐: 古代与中世纪哲学的图景关注物,17到19世纪的哲学关注观念,而启蒙的当 代哲学场景则关注词语,这似已得到众人认可。 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己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 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 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己经 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鸣 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 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 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 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 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 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 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 吉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吧想界及学术界的在欧洲, 人们可能会把 四W。J.T.米敢尔,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译按:本文中表示图像的英文词有pictum,mge,figure以及icon,另外由这些词衍化出来一些 同源词。一般说来,picture与mae常常混用,但是严格说来这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Pictun通常指一个 具体构筑出来的物体, 则更多地暗示呈现给观看者的虚拟的现象上的存在:前者是主动的表征行 为(作为动词的pcuK有描述或刻写depict之意),而后者则甚至是有点被动或自动的行为(从词源上看 mage与想象imagine同源):前者还可能指一种具体的视觉表征(如“图形的”像the“pictorial”image) 后者可以指整个视像性(1coi©i心y)领域。有关这两者的区别的详细时论,参看该作者早明的苦作《洁像学》 (Iconology)第一章《何为像?》(What is an Image?)。在本译文中,picture一般译为“图像”,imag 译为“形象”,gure译为“喻形”,icon译为“图示”或“谱像”,iconology译为“谱像学”;当picture 和m:的深生 出现在短语中时,一律译作“图像”。 参见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第263页,以 及罗蒂所编的平期论文集《语言学转向》(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I967), 四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线素可说是Stanley Cavell在《被观看的世界:对电影,总体论的反思》
《文化研究》第三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2 年 1 月版,第 13~38 页 图像转向 W.J.T.米歇尔(W.J.T. Mitchell)1[①] 范静晔 译2[②] 媒介的所有脉冲都馈到我梦境的环路。人想到了回声。人想到了制成于图像之 中的图像以及图像之间的相类相似。 它便是这般复杂。 ——唐·德利洛《美国》(1971) 理查·罗蒂曾把哲学史的特征描述为一系列“转向”,在这些转向中,一整套新问题的 突显伴随着旧问题的消隐: 古代与中世纪哲学的图景关注物,17 到 19 世纪的哲学关注观念,而启蒙的当 代哲学场景则关注词语,这似已得到众人认可。 罗蒂哲学史的最后阶段便是他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这一发展已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 科产生纷繁复杂的共鸣。语言学、符号学、修辞学以及文本性的种种模式已经变成对艺术、 媒介以及文化形式进行批判审思的通用语言。社会便是一个文本。自然以及对它的表征已经 成为“话语”,甚至连无意识也如语言一般结构而成。3[③] 思想界及学术界的话语中所发生的这些转变,更多的是它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与日常 生活及普通语言关系不大。这样说的理由并不见得有多么不言自明,但是人们似乎可以明白 看出哲学家们的论述中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其他学科以及公共文化领域中也正在又一次发 生一种纷繁纠结的转型。我想把这一转变称为“图像转向”。在英美哲学中,这一转向的变 体向前可以追溯至查尔斯·皮尔斯的符号学,向后到尼尔森·古德曼的“艺术的语言”,两 者都探讨作为非语言符号系统赖以立基的惯例及代码,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不是以语 言乃意义之示例范型这一假定作为其开端的。4[④]思想界及学术界的在欧洲,人们可能会把 1[①] W.J.T.米歇尔,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 2[②] 译按:本文中表示图像的英文词有 pictum,image,figure 以及 icon,另外由这些词衍化出来一些 同源词。一般说来,picture 与 image 常常混用,但是严格说来这两者还是有所区别的。 Pictun 通常指一个 具体构筑出来的物体,而 image 则更多地暗示呈现给观看者的虚拟的现象上的存在;前者是主动的表征行 为(作为动词的 pictuK 有描述或刻写 depict 之意),而后者则甚至是有点被动或自动的行为(从词源上看, image 与想象 imagine 同源);前者还可能指一种具体的视觉表征(如“图形的”像 the“pictorial”image), 后者可以指整个视像性(iconicity)领域。有关这两者的区别的详细讨论,参看该作者早期的著作《谱像学》 (Iconology)第一章《何为像?》(What is an Image?)。在本译文中,picture 一般译为“图像”,image 译为“形象”,figure 译为“喻形”,icon 译为“图示”或“谱像”,iconology 译为“谱像学”;当 picture 和 image 的派生词出现在短语中时,一律译作“图像”。 3[③] 参见理查,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第 263 页,以 及罗蒂所编的早期论文集《语言学转向》(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7)。 4[④] 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线索可说是 Stanley Cavell 在《被观看的世界:对电影总体论的反思》

它与现象学对想象及视觉经验的探究一致起来:或者与德里达的文字学相一致,这一理论通 过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书写的可视的材料痕迹上,从而将语言的“语音中心”模式去中心 或者把它与法 克福学 对现代 众文化以及视觉媒介的探讨相 动, 者将它 米歇尔·福柯所坚持的权力/知识的历史及理论相一致,这套理论及历史把话语的与“可视 的”、可见的与可言说的之间的新寥阐术为现代性的“视界政体”中关键的分界线。可首 先,我将会把图像转向的哲学成形置于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体系下,尤其置于他哲 学生涯那表面悖论下来考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生涯始于一种关于意义的“图像理论”,而 以一种圣像破 不的出现告终,这种对形象的批判导致他摈弃了早期的图像主义,并说出这村 的话: “图像俘虏了我们。而我们无法逃脱它,因为它置于我们的语言之中,而且语言似 不停地向我们重复它。”6侧罗蒂想“把视觉的,尤其是镜映的隐喻彻底驱除出我们的言语。 他的这一决心也回响者维特根斯坦恐像症以及语言哲学对视觉表征的总体焦虑。我想指 出,这种焦虑,这种想维护“我们的言语”而反对“视物”的需要,正是图像转向正在发生 的可靠标志。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与视觉表征的不同遇都可以简化为某个单独的论题,也不 是说对于“视物”的所有焦虑都源于同一物。罗蒂所关注的是使哲学超越它对认识论的迷恋 尤其是要超裁它对形象作为表征诱明性及现实性的的形(山e)这一模式的迷恋。对他而 言,这个“镜”是走向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诱惑。法兰克福学派的看法则与此相反,他们 认为视物的体制与大众媒介再加上某种法西斯文化的威胁相联系。因而,图像转换之所 以具有意义是因为图像开 个特别的摩擦与不快的焦点,跨越广阔的学术探讨范围,并 不是因为我们对产生文化理论诸多术语的视觉表征具有什么有力的表述。图像现在所达到的 地位处于托马斯·库恩所谓的“范式”与“变异”(aomd小v)之间,正如语言兴起而成为 人文科学的中心话题一样。也就是说,图像正成为其他事物(包括喻形的构成本身)的一种 模式和喻形,一个未解的难题,甚至是其自身的对象,即欧文·潘诺夫斯基所谓的“谱像学” 这门“科学”的客体 以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便是,在这个常常被刻画为“景观”(居伊 波语)和“监视”(福柯语)及形象制作无新不在的时代,我们仍然不知道图像到底是什么 它们与语言的关系究竟如何,它们到底如何作用于观者和世界,究竟该如何理解其历史,人 们对它们能做什么,有什么能做。 (Cambridge,MA:Harvad Universi y Press,l980)一书中的尝试。他试图把关国电影和现代绘画放置于 英关浪漫主义的哲学框架内探讨。 我在这里借鉴了Sean Hand译、吉列斯·德物兹著《( University of Minnesto 1988) 一书中对福柯方法的分析。尤其参看《分层或历史形态:可祝的及可述的(知识)》,第476 页。关于“视界政体”的观念,参看收入霍尔·福斯特编《视觉与视觉性》(VisionandVisuality,Seartle: BayPress,1988)一书第3.77页马丁·杰的论文《现代性的视界攻体》(soopic Regimes of Modernity)以 及让弗钥索瓦·利奥塔若《话语/图像》(DsQ0 rse/Figure,Paris:Klincksieck,1971) 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C.E。M ew York :15.对于这一论愿的充分论述,参看拙文《维特根斯坦的形象以及它所告知我们的》,刊于《新文学 史》19卷第2期(1988年冬季号),第361-370页。 同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第371页。 Charles Altieri指出,这里的“焦虑”在于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认识,即“分析哲学本身便是基于 种关于自我明证和可呈示性的极其图像化的观念。192年10月与本作者的通信 对罗蒂和法兰克福学派有关视物体制作出的最接近于哲学综合的论文克然是马丁·海德格尔的 "Die Zeit des Welthildes" ,William Lovitt译为《世界图像时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收入海 德格尔《论技术问题及其他论文》(New York:Harper&Row,1977),第1I5-154真
它与现象学对想象及视觉经验的探究一致起来;或者与德里达的文字学相一致,这一理论通 过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书写的可视的材料痕迹上,从而将语言的“语音中心”模式去中心 化;或者把它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性、大众文化以及视觉媒介的探讨相一致;或者将它与 米歇尔·福柯所坚持的权力/知识的历史及理论相一致,这套理论及历史把话语的与“可视 的”、可见的与可言说的之间的断裂阐述为现代性的“视界政体”中关键的分界线。5[⑤]首 先,我将会把图像转向的哲学成形置于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体系下,尤其置于他哲 学生涯那表面悖论下来考察。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生涯始于一种关于意义的“图像理论”,而 以一种圣像破坏的出现告终,这种对形象的批判导致他摈弃了早期的图像主义,并说出这样 的话:“图像俘虏了我们。而我们无法逃脱它,因为它置于我们的语言之中,而且语言似乎 不停地向我们重复它。”6[⑥]罗蒂想“把视觉的,尤其是镜映的隐喻彻底驱除出我们的言语。” 7[⑦]他的这一决心也回响着维特根斯坦恐像症以及语言哲学对视觉表征的总体焦虑。我想指 出,这种焦虑,这种想维护“我们的言语”而反对“视物”的需要,正是图像转向正在发生 的可靠标志。8[⑧] 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这些与视觉表征的不同遭遇都可以简化为某个单独的论题,也不 是说对于“视物”的所有焦虑都源于同一物。罗蒂所关注的是使哲学超越它对认识论的迷恋, 尤其是要超越它对形象作为表征透明性及现实性的喻形(rlsule)这一模式的迷恋。对他而 言,这个“镜”是走向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诱惑。法兰克福学派的看法则与此相反,他们 认为视物的体制与大众媒介再加上某种法西斯文化的威胁相联系。9[⑨]因而,图像转换之所 以具有意义是因为图像形成了一个特别的摩擦与不快的焦点,跨越广阔的学术探讨范围,并 不是因为我们对产生文化理论诸多术语的视觉表征具有什么有力的表述。图像现在所达到的 地位处于托马斯·库恩所谓的“范式”与“变异”(anomdy)之间,正如语言兴起而成为 人文科学的中心话题一样。也就是说,图像正成为其他事物(包括喻形的构成本身)的一种 模式和喻形,一个未解的难题,甚至是其自身的对象,即欧文·潘诺夫斯基所谓的“谱像学” 这门“科学”的客体。以最简单的方式来描述便是,在这个常常被刻画为“景观”(居伊·德 波语)和“监视”(福柯语)及形象制作无新不在的时代,我们仍然不知道图像到底是什么, 它们与语言的关系究竟如何,它们到底如何作用于观者和世界,究竟该如何理解其历史,人 们对它们能做什么,有什么能做。 (Cambridge,MA:Harvad University Press,1980)一书中的尝试。他试图把美国电影和现代绘画放置于 英美浪漫主义的哲学框架内探讨。 5[⑤] 我在这里借鉴了 Sean Hand 译、吉列斯·德勒兹著《福柯》(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tota Press,1988)一书中对福柯方法的分析。尤其参看《分层或历史形态:可视的及可述的(知识)》,第 47-69 页。关于“视界政体”的观念,参看收入霍尔·福斯特编《视觉与视觉性》(VisionandVisuality,Seattle: BayPress,1988)一书第 3-77 页马丁·杰的论文《现代性的视界政体》(soopic Regimes of Modernity)以 及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着《话语/图像》(Discourse/Figure,Paris:Klincksieck,1971)。 6[⑥] 路德维格·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C.E.M.Anscombe 译(New York:Macmillan,1953), I:115.对于这一论题的充分论述,参看拙文《维特根斯坦的形象以及它所告知我们的》,刊于《新文学 史》19 卷第 2 期(1988 年冬季号),第 361-370 页。 7[⑦]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第 371 页。 8[⑧] Charles Altieri 指出,这里的“焦虑”在于维特根斯坦的这一认识,即“分析哲学本身便是基于一 种关于自我明证和可呈示性的极其图像化的观念”。1992 年 10 月与本作者的通信。 9[⑨] 对罗蒂和法兰克福学派有关视物体制作出的最接近于哲学综合的论文竟然是马丁·海德格尔的 “Die Zeit des Welthildes”,William Lovitt 译为《世界图像时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收入海 德格尔《论技术问题及其他论文》(New York:Harper & Row,1977),第 115-15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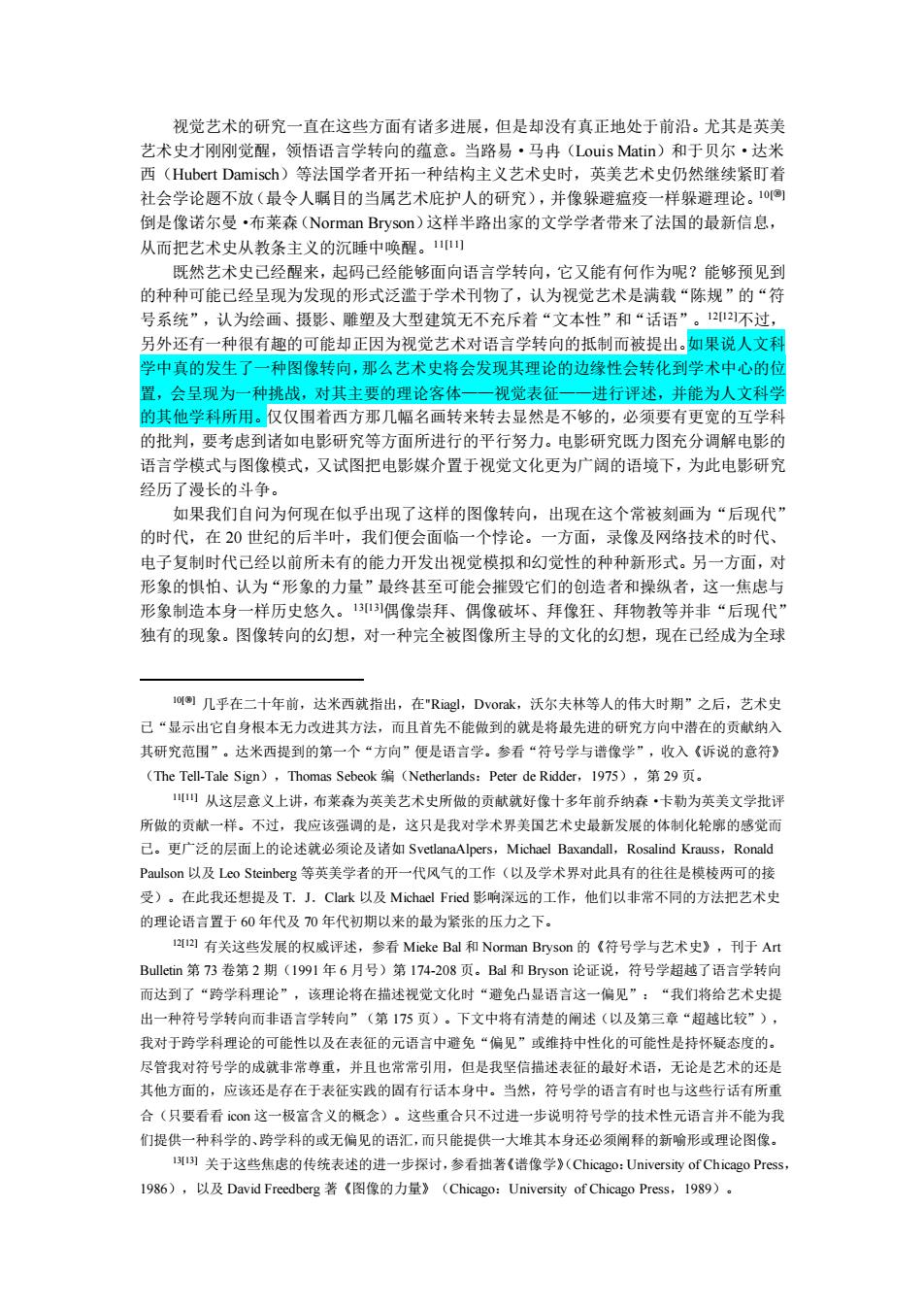
视微艺术的研究一直在这些方面右诸多讲展,但是却沿右直正恤处于前沿。北其是革望 艺术史才刚刚觉 悟语言学转 向的蕴意。当路易·马 Matin 和于贝尔 达米 西(Hubert Damisch 等法国学者开拓一种结构主义艺术史时,英美艺术史仍然继续紧町者 社会学论题不放(最令人瞩目的当属艺术庇护人的研究),并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理论。 倒是像诺尔曼·布莱森(Norman Bryson)这样半路出家的文学学者带来了法国的最新信息, 从而把艺术史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晚阴。1川 既然艺术史已经醒来,起码已经能够面向语言学转向,它又能有何作为呢?能够预见到 的种种可能已经呈现为发现的 形式泛滥于学术刊物了,认为视觉艺术是满载“陈规”的“符 号系统”,认为绘画、摄影、塑及大型建筑无不充斥着“文本性”和“话语” 。22不过 另外还有一种很有趣的可能却正因为视觉艺术对语言学转向的抵制而被提出。如果说人文科 学中真的发生了一种图像转向,那么艺术史将会发现其理论的边缘性会转化到学术中心的 进行评述,并能为人文科 的其他学 。仅仅围着西方那几幅名画转来转去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更宽的互学利 的批判,要考虑到诸如电影研究等方面所进行的平行努力。电影研究既力图充分调解电影的 语言学模式与图像模式,又试图把电影媒介置于视觉文化更为广阔的语境下,为此电影研究 经历了漫长的斗争。 如果我们白间为何现在似平出现了这样的图像转向,出现在这个常被刻画为“后现代 的时代,在20世纪的后半叶,我们便会面临 个论 一方面,录像及网络技术的时代 电子复制时代已经以前所未有的能力开发出视觉模拟和幻觉性的种种新形式。另一方面,对 形象的惧怕、认为“形象的力量”最终甚至可能会摧毁它们的创造者和操纵者,这一焦虑与 形象制造本身一样历史悠久。偶像崇拜、偶像破坏、拜像狂、拜物教等并非“后现代 独有的现象。图像转向的幻想,对一种完全被图像所主导的文化的幻想,现在已经成为全球 几乎在二十年前,达米西就指 k,沃尔夫林等人的伟大时期”之后,艺术 已“显示出它自身根本无力改进其方法 而且首先不能做到的就是将最先进的研究方向中潜在的贡献纳 其研究范用 达米西提到的第一个“方向”使是语言学。参看“符号学与语像学” ,收入《诉说的意符》 (The Tell-Tale Sign),Thomas Sebeok (Netherlands:Peter de Ridder,1975).29. 训从这层意义上讲,布莱森为英美艺术史所做的贡献袜好像十多年前乔纳森·卡勒为英美文学批评 所做的一样。不过,我应该调的是,议只是我对学术界关国艺术中最新发展的体化轮的感觉 己。更广泛的层面上的论述就必须论及请如 m以及Leo Stcinberg等英美学者的开一代风气的工作(以及学术界对此具有的往往是模棱两可的 受)。在此我还想提及T.J.Clark以及Michael Fried影响深远的工作,他们以非常不同的方法把艺术生 的理论语言置于60年代及70年代初期以来的最为紧张的压力之下, 】有关这此发展的权威球,参看Mieke Bal和Norman B 0的《符号学与艺术史》,刊于A Bum第73卷第2期(191年6月号)第174208页.Ba和Bn0m论证说,符号学超 了语学转向 而达到了 “跨学科理询 该理论将在描述视觉文化时“卷免凸显语言这 偏见“ 我们将给艺术史封 出一种符号学转向而非语言学转向”(第175页)·下文中将有清楚的闸述(以及第三章“超越比较”) 我对于骑学科理论的可能性以及在表征的元语言中避免“偏见”或维持中性化的可能性是持怀疑态度的 尽管我对符号学的成就非常尊重,并且也常常引用,但是我坚信描述表征的最好术语,无论是艺术的还是 其他方面的,应该还是存在于表征实践的因有行话本身中,当然,符号学的语言有时也与这些行话有所重 合(只要看看iom这一极富含义的概念) ,这些重合只不过进一步说明符号学的技术性元语言并不能为我 们提供一种科学的、跨学科的或无偏见的语汇,而只能提供一大堆其本身还必须闸释的新喻形或理论图像 11]关于这些焦虑的传统表述的进一步探讨,参看拙著《谱像学》(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以及David Freedberg若《图像的力量》(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视觉艺术的研究一直在这些方面有诸多进展,但是却没有真正地处于前沿。尤其是英美 艺术史才刚刚觉醒,领悟语言学转向的蕴意。当路易·马冉(Louis Matin)和于贝尔·达米 西(Hubert Damisch)等法国学者开拓一种结构主义艺术史时,英美艺术史仍然继续紧盯着 社会学论题不放(最令人瞩目的当属艺术庇护人的研究),并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理论。10[⑩] 倒是像诺尔曼·布莱森(Norman Bryson)这样半路出家的文学学者带来了法国的最新信息, 从而把艺术史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唤醒。11[11] 既然艺术史已经醒来,起码已经能够面向语言学转向,它又能有何作为呢?能够预见到 的种种可能已经呈现为发现的形式泛滥于学术刊物了,认为视觉艺术是满载“陈规”的“符 号系统”,认为绘画、摄影、雕塑及大型建筑无不充斥着“文本性”和“话语”。12[12]不过, 另外还有一种很有趣的可能却正因为视觉艺术对语言学转向的抵制而被提出。如果说人文科 学中真的发生了一种图像转向,那么艺术史将会发现其理论的边缘性会转化到学术中心的位 置,会呈现为一种挑战,对其主要的理论客体——视觉表征——进行评述,并能为人文科学 的其他学科所用。仅仅围着西方那几幅名画转来转去显然是不够的,必须要有更宽的互学科 的批判,要考虑到诸如电影研究等方面所进行的平行努力。电影研究既力图充分调解电影的 语言学模式与图像模式,又试图把电影媒介置于视觉文化更为广阔的语境下,为此电影研究 经历了漫长的斗争。 如果我们自问为何现在似乎出现了这样的图像转向,出现在这个常被刻画为“后现代” 的时代,在 20 世纪的后半叶,我们便会面临一个悖论。一方面,录像及网络技术的时代、 电子复制时代已经以前所未有的能力开发出视觉模拟和幻觉性的种种新形式。另一方面,对 形象的惧怕、认为“形象的力量”最终甚至可能会摧毁它们的创造者和操纵者,这一焦虑与 形象制造本身一样历史悠久。13[13]偶像崇拜、偶像破坏、拜像狂、拜物教等并非“后现代” 独有的现象。图像转向的幻想,对一种完全被图像所主导的文化的幻想,现在已经成为全球 10[⑩] 几乎在二十年前,达米西就指出,在"Riagl,Dvorak,沃尔夫林等人的伟大时期”之后,艺术史 已“显示出它自身根本无力改进其方法,而且首先不能做到的就是将最先进的研究方向中潜在的贡献纳入 其研究范围”。达米西提到的第一个“方向”便是语言学。参看“符号学与谱像学”,收入《诉说的意符》 (The Tell-Tale Sign),Thomas Sebeok 编(Netherlands:Peter de Ridder,1975),第 29 页。 11[11] 从这层意义上讲,布莱森为英美艺术史所做的贡献就好像十多年前乔纳森·卡勒为英美文学批评 所做的贡献一样。不过,我应该强调的是,这只是我对学术界美国艺术史最新发展的体制化轮廓的感觉而 已。更广泛的层面上的论述就必须论及诸如 SvetlanaAlpers,Michael Baxandall,Rosalind Krauss,Ronald Paulson 以及 Leo Steinberg 等英美学者的开一代风气的工作(以及学术界对此具有的往往是模棱两可的接 受)。在此我还想提及 T.J.Clark 以及 Michael Fried 影响深远的工作,他们以非常不同的方法把艺术史 的理论语言置于 60 年代及 70 年代初期以来的最为紧张的压力之下。 12[12] 有关这些发展的权威评述,参看 Mieke Bal 和 Norman Bryson 的《符号学与艺术史》,刊于 Art Bulletin 第 73 卷第 2 期(1991 年 6 月号)第 174-208 页。Bal 和 Bryson 论证说,符号学超越了语言学转向 而达到了“跨学科理论”,该理论将在描述视觉文化时“避免凸显语言这一偏见”:“我们将给艺术史提 出一种符号学转向而非语言学转向”(第 175 页)。下文中将有清楚的阐述(以及第三章“超越比较”), 我对于跨学科理论的可能性以及在表征的元语言中避免“偏见”或维持中性化的可能性是持怀疑态度的。 尽管我对符号学的成就非常尊重,并且也常常引用,但是我坚信描述表征的最好术语,无论是艺术的还是 其他方面的,应该还是存在于表征实践的固有行话本身中。当然,符号学的语言有时也与这些行话有所重 合(只要看看 icon 这一极富含义的概念)。这些重合只不过进一步说明符号学的技术性元语言并不能为我 们提供一种科学的、跨学科的或无偏见的语汇,而只能提供一大堆其本身还必须阐释的新喻形或理论图像。 13[13] 关于这些焦虑的传统表述的进一步探讨,参看拙著《谱像学》(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以及 David Freedberg 著《图像的力量》(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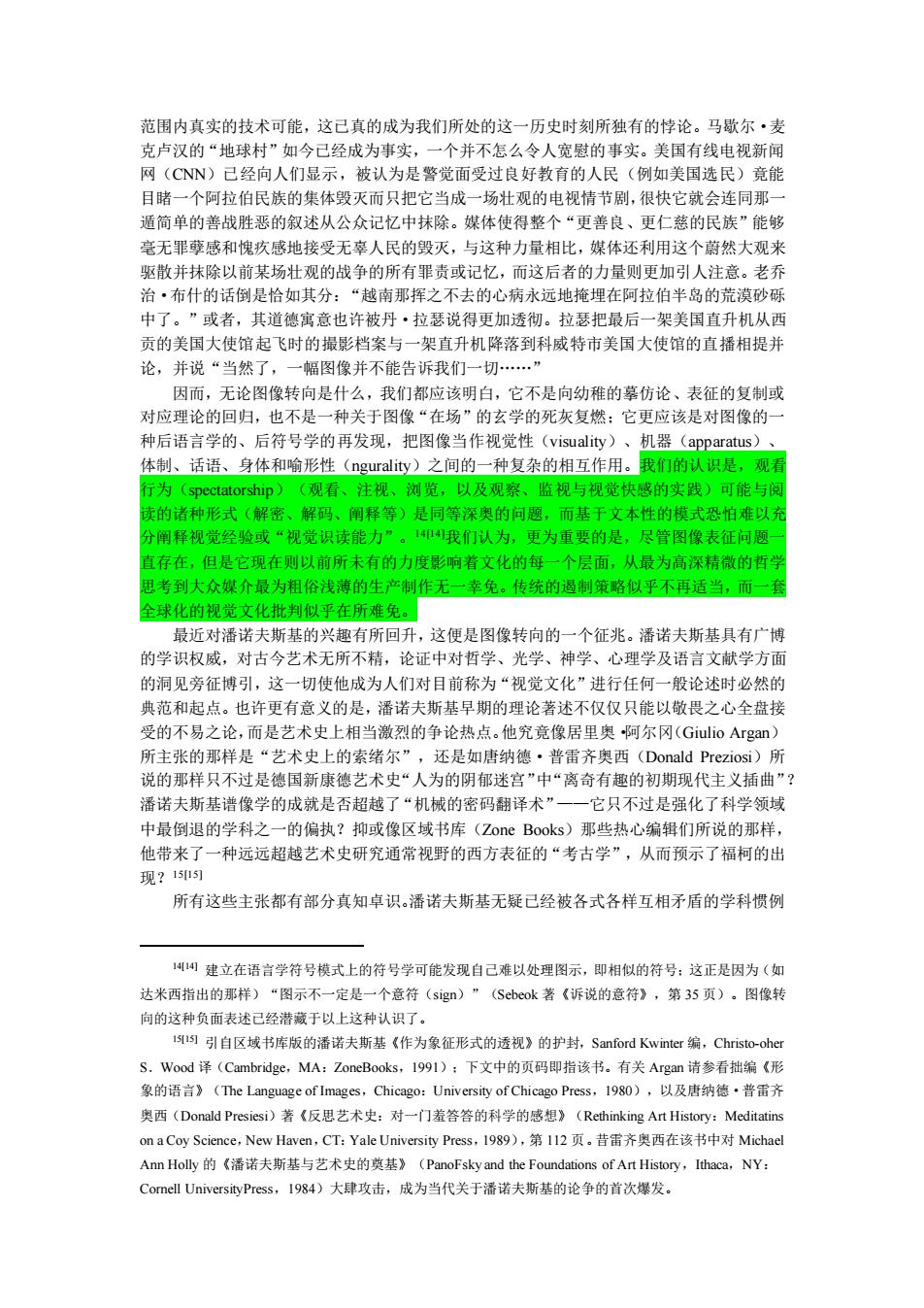
范围内真实的技术可能,这己点的成为我们所处的这一历史时刻所独有的悖论。马歇尔·麦 克卢汉的“地球村”如今己经成为事实 一个并不怎么令人宽慰的事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已经向人们显示 被认) 是警觉面受过良好教有的人 选民 目睹 个阿拉伯民族的集体毁灭而只把它当成一场壮观的电视情节刷,很快它就会连同那 遁简单的善战胜恶的叙述从公众记忆中抹除。媒体使得整个“更善良、更仁慈的民族”能第 案无罪孽成和愧疚感地接受无辜人民的毁灭,与这种力量相比,媒体还利用这个尊然大观来 驱散并抹除以前某场壮观的战争的所有罪责或记忆,而这后者的力量则更加引人注意。老乔 治·布什的话倒是恰如其分 “城支 那挥之不去的心病永远地掩埋在 拉伯半岛的荒漠 中了 或者, 其道德寓意也许被丹·拉瑟说得更加透彻。拉瑟把最后 一架美国直升机从西 贡的美国大使馆起飞时的撮影档案与一架直升机降落到科威特市美国大使馆的直播相提并 论,并说“当然了,一幅图像并不能告诉我们一切” 因而,无论图像转向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明白,它不是向幼的墓仿论、麦征的复制或 对应理论的回归,也不是 轴关图像“在杨”的左学的那 ,它更应该是对图像的 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再发现,把图像当作视觉性(visuality) 机器(apparatus) 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gurality)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的认识是 大(spectatorship 观香、生视流,以及观察、蓝现与视觉快的我)可非 的诸种形式(解、解码:细释等)是同等深奥的园题,而基于文本性的模式恐怕难以子 细视觉经验或“视识力” 。我认为,中为重要的基,尽管图表征职 存在 但是它现在则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若文化的每 个层面 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相俗浅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传统的制策路似乎不再适 全球化的视货文化批判似平在所难免 最近对潘诺夫斯基的兴趣有所回升,这便是图像转向的一个征兆。潘诺夫斯基具有广博 的学识权威,对古今艺术无所不精,论证中对哲学、光学、神学、心理学及语言文献学方面 的洞见旁征博引,这 切使他成为人们对目前利 为“视觉文化”进行任何一般论述时必然 典范和起点。也许更有意义的是,潘诺夫斯基早期的理论著述不仅仅只能以畏之心全盘接 受的不易之论,而是艺术史上相当激烈的争论热点。他究竞像居里奥阿尔冈(Giulio Argan) 所主张的那样是“艺术史上的索绪尔”,还是如唐纳德·普雷齐奥西(Donald Preziosi)所 说的那样只不过是德国新康德艺术史“人为的明郁迷宫”中“离奇有趣的初期现代主义插曲”? 潘诺夫斯基谱像学的成就是否超越了“机械的密码翻译术” 它只不讨是化了科学领域 中最倒退的学科之 的偏执?抑或像区域书库(Zone Books)那些热 心编辑们所说的那样 他带来了一种远远超越艺术史研究通常视野的西方表征的“考古学”,从而预示了福柯的出 现?1到 所有这些主张都有部分真知卓识。潘诺夫斯基无疑已经被各式各样互相矛盾的学科惯例 建立在语言学符号模式上的符号学可德发现白己难以处理图示,即相似的符号,这正是因为(如 达米西指出的那样 “图示不 定 个意符(sign (Sebeok著《诉说的意符》,第35页)。图像 白的神表提于笑种证形衣的的护,C购 S.Wood译(Cambridge,.MA:ZoneBooks,1991):下文中的页码即指该书。有关Argan请参看拉编《形 象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Imag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以及唐纳德·普雷齐 奥西(Donald Prs)著《反思艺术史:对一门羞答答的科学的感想》(Rethinking onaCoy Science,New Haven,CT:Yale Uni crsi0 Press,l989),第112页。昔需齐奥西在该书中对Michae Ann Holly的《话诺夫斯基与艺术史的奠基》(PanoFsk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rt History,Ithaca,NY Comell UniversityPress,I984)大肆攻击,成为当代关于潘诺夫斯基的论争的首次爆发
范围内真实的技术可能,这已真的成为我们所处的这一历史时刻所独有的悖论。马歇尔·麦 克卢汉的“地球村”如今已经成为事实,一个并不怎么令人宽慰的事实。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已经向人们显示,被认为是警觉面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例如美国选民)竟能 目睹一个阿拉伯民族的集体毁灭而只把它当成一场壮观的电视情节剧,很快它就会连同那一 遁简单的善战胜恶的叙述从公众记忆中抹除。媒体使得整个“更善良、更仁慈的民族”能够 毫无罪孽感和愧疚感地接受无辜人民的毁灭,与这种力量相比,媒体还利用这个蔚然大观来 驱散并抹除以前某场壮观的战争的所有罪责或记忆,而这后者的力量则更加引人注意。老乔 治·布什的话倒是恰如其分:“越南那挥之不去的心病永远地掩埋在阿拉伯半岛的荒漠砂砾 中了。”或者,其道德寓意也许被丹·拉瑟说得更加透彻。拉瑟把最后一架美国直升机从西 贡的美国大使馆起飞时的撮影档案与一架直升机降落到科威特市美国大使馆的直播相提并 论,并说“当然了,一幅图像并不能告诉我们一切.” 因而,无论图像转向是什么,我们都应该明白,它不是向幼稚的摹仿论、表征的复制或 对应理论的回归,也不是一种关于图像“在场”的玄学的死灰复燃;它更应该是对图像的一 种后语言学的、后符号学的再发现,把图像当作视觉性(visuality)、机器(apparatus)、 体制、话语、身体和喻形性(ngurality)之间的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我们的认识是,观看 行为(spectatorship)(观看、注视、浏览,以及观察、监视与视觉快感的实践)可能与阅 读的诸种形式(解密、解码、阐释等)是同等深奥的问题,而基于文本性的模式恐怕难以充 分阐释视觉经验或“视觉识读能力”。14[14]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图像表征问题一 直存在,但是它现在则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影响着文化的每一个层面,从最为高深精微的哲学 思考到大众媒介最为粗俗浅薄的生产制作无一幸免。传统的遏制策略似乎不再适当,而一套 全球化的视觉文化批判似乎在所难免。 最近对潘诺夫斯基的兴趣有所回升,这便是图像转向的一个征兆。潘诺夫斯基具有广博 的学识权威,对古今艺术无所不精,论证中对哲学、光学、神学、心理学及语言文献学方面 的洞见旁征博引,这一切使他成为人们对目前称为“视觉文化”进行任何一般论述时必然的 典范和起点。也许更有意义的是,潘诺夫斯基早期的理论著述不仅仅只能以敬畏之心全盘接 受的不易之论,而是艺术史上相当激烈的争论热点。他究竟像居里奥·阿尔冈(Giulio Argan) 所主张的那样是“艺术史上的索绪尔”,还是如唐纳德·普雷齐奥西(Donald Preziosi)所 说的那样只不过是德国新康德艺术史“人为的阴郁迷宫”中“离奇有趣的初期现代主义插曲”? 潘诺夫斯基谱像学的成就是否超越了“机械的密码翻译术”——它只不过是强化了科学领域 中最倒退的学科之一的偏执?抑或像区域书库(Zone Books)那些热心编辑们所说的那样, 他带来了一种远远超越艺术史研究通常视野的西方表征的“考古学”,从而预示了福柯的出 现?15[15] 所有这些主张都有部分真知卓识。潘诺夫斯基无疑已经被各式各样互相矛盾的学科惯例 14[14] 建立在语言学符号模式上的符号学可能发现自己难以处理图示,即相似的符号;这正是因为(如 达米西指出的那样)“图示不一定是一个意符(sign)”(Sebeok 著《诉说的意符》,第 35 页)。图像转 向的这种负面表述已经潜藏于以上这种认识了。 15[15] 引自区域书库版的潘诺夫斯基《作为象征形式的透视》的护封,Sanford Kwinter 编,Christo-oher S.Wood 译(Cambridge,MA:ZoneBooks,1991);下文中的页码即指该书。有关 Argan 请参看拙编《形 象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Imag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以及唐纳德·普雷齐 奥西(Donald Presiesi)著《反思艺术史:对一门羞答答的科学的感想》(Rethinking Art History:Meditatins on a Coy Science,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第 112 页。昔雷齐奥西在该书中对 Michael Ann Holly 的《潘诺夫斯基与艺术史的奠基》(PanoFsk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Art History,Ithaca,NY: 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84)大肆攻击,成为当代关于潘诺夫斯基的论争的首次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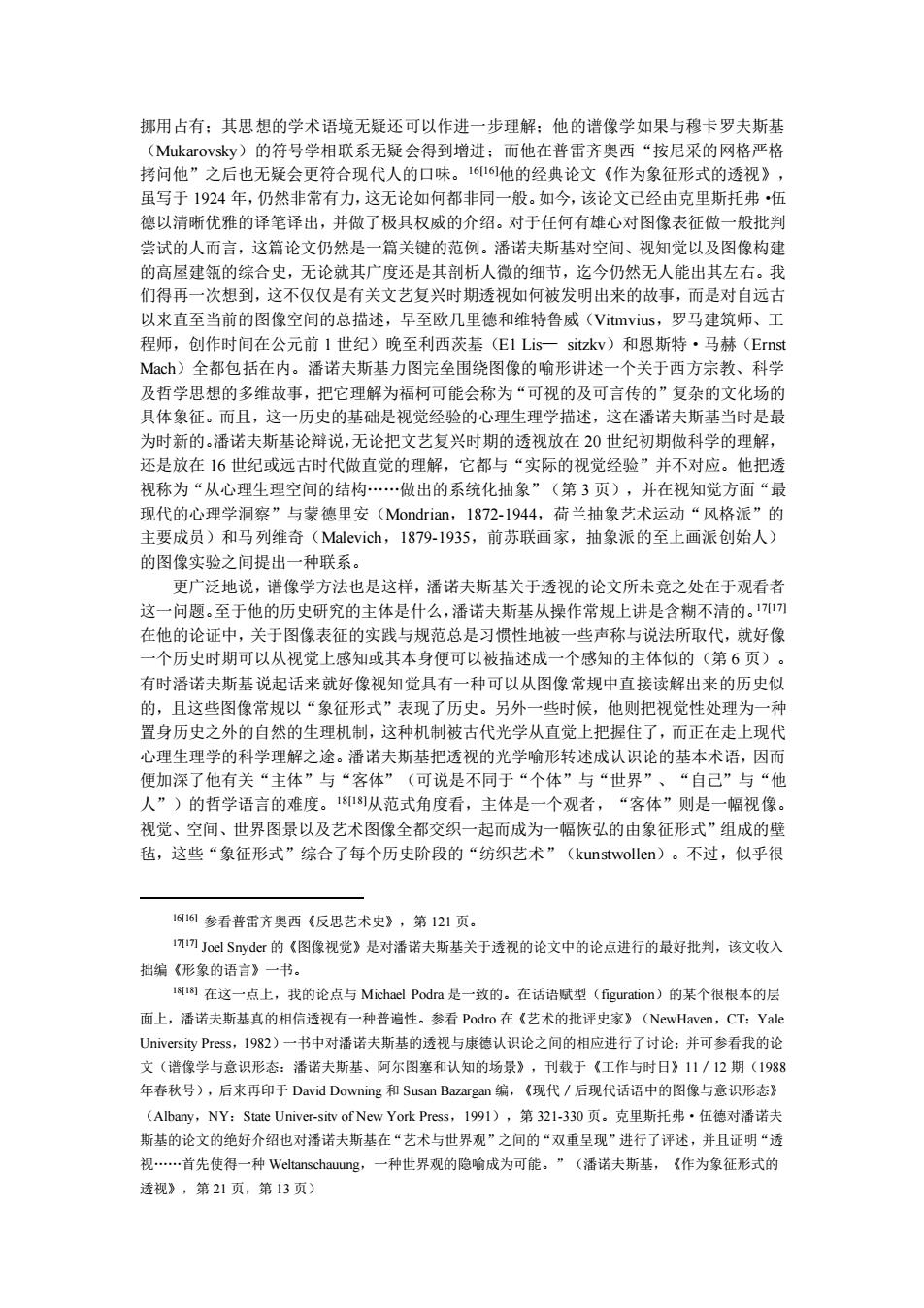
挪用占有:其思想的学术语境无疑还可以作进一步理解:他的谱像学如果与穆卡罗夫斯基 面他在香齐爽西按尼采的网格 的符号学相联系无疑会得到增选。作的经具论文《作为象征形式的透 虽写于1924年,仍然非常有力,这无论如何都非同一般。如今,该论文已经由克里斯托弗·伍 德以清晰优雅的译箪译出,并做了极其权威的介绍。对干任何有雄心对图像表征做一般批判 尝试的人而言,这篇论文仍然是一篇关键的范例。潘诺夫断基对空间、视知觉以及图像构津 的高屋建瓴的综合史,无论就其广度还是其剖析人微的细节,迄今仍然无人能出其左右。 们得再 次想全 这不仅仅是有关文艺复兴时期透视如何被发明出来的故事 ,而是对自远古 以来直至当前的图像空间的总描述,早至欧几里德和维特鲁威(Vitmvius,罗马建筑师、工 程师,创作时间在公元前1世纪)晚至利西茨基(E1Lis一sitz水v)和恩断特·马赫(Es MCh)全都包括在内。潘诺夫斯基力图完垒围绕图像的喻形讲述一个关于西方宗教、科学 及哲学思想的多维故事,把它理解为福柯可能会称为“可视的及可言传的”复杂的文化场的 具体象征 ·而且, 这 历史的基。 经验 诺夫斯基当时是最 为时新的,潘诺夫斯基论辩说,无论把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放在20世纪初期做科学的理解 还是放在16世纪或远古时代做直觉的理解,它都与“实际的视觉经验”并不对应。他把透 视称为“从心理生理空间的结构.做出的系统化抽象”(第3页),并在视知觉方面“最 现代的心理学洞察”与蒙德里安(Mondrian,1872-1944,荷兰抽象艺术运动“风格派”的 主要成员)和马列维奇(Malevich,.1879-1935,前苏联画家,抽象派的至上画派创始人) 的图像实验之间提出 一种联系 更广泛地说,谱像学方法也是这样,潘诺夫斯基关于透视的论文所未竟之处在于观看者 这一问题。至于他的历史研究的主体是什么,潘诺夫斯基从操作常规上讲是含糊不清的。11 在他的论证中,关于图像表征的实践与规范总是习惯性地被一些声称与说法所取代,就好像 个历中时期以从视微上成知或其本身便可以被描林成一个成知的主体似的(第6页 有时潘诺夫斯基说起话来就好像视知觉 种可以从图像常规中直接读解出来的历史似 的,且这些图像常规以“象征形式”表现了历史。另外一些时候,他则把视觉性处理为一种 置身历史之外的自然的生理机制,这种机制被古代光学从直觉上把握住了,而正在走上现代 心理生理学的科学理解之途。潘诺夫斯基把透视的光学喻形转述成认识论的基本术语,因面 便加深了他有关“主体”与“客体”(可说是不同于“个体”与“世界”、“自己”与“他 人”)的哲学 语言的难度 。181从范式角度看, 主体是一个观者 “客体”则是 幅视像 视觉、空间、世界图景以及艺术图像全都交织一起而成为一幅恢弘的由象征形式”组成的型 毡,这些“象征形式”综合了每个历史阶段的“纺织艺术”(kunstwo川n)。不过,似乎很 阿参看誓雷齐奥西《反见艺术史》,第121页, 1T Joel Snyd:的(图像祝觉》是对潘诺夫斯基关于透税的论文中的论点进行的最好批判,该文收入 拙编(形象的语》 上,我的论点与Michael Podra是一致的。在话语赋型(figuration)的某个很根本的 面上,潘诺夫斯基真的相信透视有一种普遍性。参看Podo在(艺术的批评史家》(NcwHaven,CT:YalG University Press,1982)一书中对活诺夫斯基的透视与康情认识论之间的相应进行了讨论:并可参看我的论 文(谱像学与意识形态:潘诺夫斯基、阿尔图塞和认知的场景》,刊载于《工作与时日》11/12期(1988 年春秋号),后来再印于David Downing和Susan Bazar1编,《现代/后现代话语中的图像与意识形态》 (AIbany NY:Stale Un r-sitv of New York Press ,第321-330页。克里斯托弗·伍德对潘诺夫 新基的论文的绝好介绍也对潘诺夫斯基在“艺术与世界观”之间的“双重呈现”进行了评述,并且证明“透 视.首先使得一种Wehtanschauung,一种世界观的隐喻成为可能。”(潘诺夫斯基,《作为象征形式的 透视》,第21页,第13页)
挪用占有;其思想的学术语境无疑还可以作进一步理解;他的谱像学如果与穆卡罗夫斯基 (Mukarovsky)的符号学相联系无疑会得到增进;而他在普雷齐奥西“按尼采的网格严格 拷问他”之后也无疑会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16[16]他的经典论文《作为象征形式的透视》, 虽写于 1924 年,仍然非常有力,这无论如何都非同一般。如今,该论文已经由克里斯托弗·伍 德以清晰优雅的译笔译出,并做了极具权威的介绍。对于任何有雄心对图像表征做一般批判 尝试的人而言,这篇论文仍然是一篇关键的范例。潘诺夫斯基对空间、视知觉以及图像构建 的高屋建瓴的综合史,无论就其广度还是其剖析人微的细节,迄今仍然无人能出其左右。我 们得再一次想到,这不仅仅是有关文艺复兴时期透视如何被发明出来的故事,而是对自远古 以来直至当前的图像空间的总描述,早至欧几里德和维特鲁威(Vitmvius,罗马建筑师、工 程师,创作时间在公元前 1 世纪)晚至利西茨基(E1 Lis— sitzkv)和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全都包括在内。潘诺夫斯基力图完垒围绕图像的喻形讲述一个关于西方宗教、科学 及哲学思想的多维故事,把它理解为福柯可能会称为“可视的及可言传的”复杂的文化场的 具体象征。而且,这一历史的基础是视觉经验的心理生理学描述,这在潘诺夫斯基当时是最 为时新的。潘诺夫斯基论辩说,无论把文艺复兴时期的透视放在 20 世纪初期做科学的理解, 还是放在 16 世纪或远古时代做直觉的理解,它都与“实际的视觉经验”并不对应。他把透 视称为“从心理生理空间的结构.做出的系统化抽象”(第 3 页),并在视知觉方面“最 现代的心理学洞察”与蒙德里安(Mondrian,1872-1944,荷兰抽象艺术运动“风格派”的 主要成员)和马列维奇(Malevich,1879-1935,前苏联画家,抽象派的至上画派创始人) 的图像实验之间提出一种联系。 更广泛地说,谱像学方法也是这样,潘诺夫斯基关于透视的论文所未竟之处在于观看者 这一问题。至于他的历史研究的主体是什么,潘诺夫斯基从操作常规上讲是含糊不清的。17[17] 在他的论证中,关于图像表征的实践与规范总是习惯性地被一些声称与说法所取代,就好像 一个历史时期可以从视觉上感知或其本身便可以被描述成一个感知的主体似的(第 6 页)。 有时潘诺夫斯基说起话来就好像视知觉具有一种可以从图像常规中直接读解出来的历史似 的,且这些图像常规以“象征形式”表现了历史。另外一些时候,他则把视觉性处理为一种 置身历史之外的自然的生理机制,这种机制被古代光学从直觉上把握住了,而正在走上现代 心理生理学的科学理解之途。潘诺夫斯基把透视的光学喻形转述成认识论的基本术语,因而 便加深了他有关“主体”与“客体”(可说是不同于“个体”与“世界”、“自己”与“他 人”)的哲学语言的难度。18[18]从范式角度看,主体是一个观者,“客体”则是一幅视像。 视觉、空间、世界图景以及艺术图像全都交织一起而成为一幅恢弘的由象征形式”组成的壁 毡,这些“象征形式”综合了每个历史阶段的“纺织艺术”(kunstwollen)。不过,似乎很 16[16] 参看普雷齐奥西《反思艺术史》,第 121 页。 17[17] Joel Snyder 的《图像视觉》是对潘诺夫斯基关于透视的论文中的论点进行的最好批判,该文收入 拙编《形象的语言》一书。 18[18] 在这一点上,我的论点与 Michael Podra 是一致的。在话语赋型(figuration)的某个很根本的层 面上,潘诺夫斯基真的相信透视有一种普遍性。参看 Podro 在《艺术的批评史家》(New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2)一书中对潘诺夫斯基的透视与康德认识论之间的相应进行了讨论;并可参看我的论 文(谱像学与意识形态:潘诺夫斯基、阿尔图塞和认知的场景》,刊载于《工作与时日》11/12 期(1988 年春秋号),后来再印于 David Downing 和 Susan Bazargan 编,《现代/后现代话语中的图像与意识形态》 (Albany,NY:State Univer-sitv of New York Press,1991),第 321-330 页。克里斯托弗·伍德对潘诺夫 斯基的论文的绝好介绍也对潘诺夫斯基在“艺术与世界观”之间的“双重呈现”进行了评述,并且证明“透 视.首先使得一种 Weltanschauung,一种世界观的隐喻成为可能。”(潘诺夫斯基,《作为象征形式的 透视》,第 21 页,第 13 页)

显然,如果图像转向要实现潘诺夫斯基所梦想的批判谱像学,我们需要拆散这块壁毡,而不 只是细加阐述而己。 态,也许我们可以打碎那些镜子并把被压迫的小写主体拯救出那个法力无边的大写主体。 那么 我们有此能力吗?这种“所有意识形态 形式结构 是否像潘诺夫斯基的透视 样 也是一种特异的历史形成,将会随着生产关系、再生产以及自它们演化而来的社会关系 变而时过境迁?或者,它是否(也像潘诺夫斯基的透视一样)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结构,将诸 多社会形态及所有历史时期吸收进它的应用范围?如果阿尔图塞采取第一种选择(即作为具 体的历史形态的那一模式),那么他便放弃了他对科学和普遍性的主张:基督教意识形态的 构可能并不能完全按“伦理的、法律的 治的、美 意识形态等等”被复制。这一“等 等 可能包括着与宗教退异的各种形态,而宗教意识形态本身可能会随历史与文化而变化 如果河尔图塞采取第二种选择,坚持镜反模式普遍的科学通性,他就像潘诺夫斯基一样变成 了一个谱像学家,具有一种意识形态而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潘诺夫斯基和阿尔图塞的招呼,怎么也胜过科学与历史的死胡同,胜过意识形态与谱你 学的一种致命的镜映:我们如何才能展示这种招呼?除了在街上扶帽致意外,法国的这位马 克思主义哲学家与德国的那位康 义艺术史家还能彼此做些什么呢?他们能否像阿尔图 塞那戏剧性的说法,从关着的门两边彼此“招呼” ,并且指望对方有所表示,有所应答,而 不会产生成为“日常警察的”怀疑对象这种错误认识?也许不会。从我们迄今为止所描绘出 来的共同空间来看,他们所占据的这一共同空间只不过是把认知场景放置在他们反思的中心。 认知作为意识形态与谱像学之间的联系,其主要重要性在于它对两门“科学”都从认识论的 “认知的”根基(小写主体对客体的知识)转换到 一种伦理的、政治的和阐释的根基(小三 主体对小写主体、甚至也许是大写主体对大写主体的知识)。判断的范畴从 认知项(teri}ls 转换到再认知项,从知识的认识论范畴转换到诸如“答谢”这样的社会范畴。阿尔图塞提醒 我们,潘诺夫斯基与图像的关系开始于与大写他者的社会性相遇,他并且指出谱像学是一门 为了把这个他者吸收进一个同质的“统一的”透视之中的科学。潘诺夫斯基则提醒我们,阿 图塞关于意识形态所举的当时当地的例证,即小写主体(们)与小写主体(们)的招呼都 被展现在由最高主权的大写主体(们)所构筑的镜子殿堂内,并指出意识形态批判正处于变 成另一种谱像学的危险之中。这些提醒并不能使我们摆脱这一难题,但是可能有助于我们在 看到难题时认出它。 17乔纳查·拉利:《观者之技:论19世纪的视微与现代性》(Cambridge,MA MIT Press, 1990) 以下页码皆出自此书。克拉利确也注意到,还是存在他的研究所没有 覆盖到的“视觉的实践”,但他把这些实践刻画为“边缘的及局部的形式,抵抗、歪曲或有 缺陷地构建着主导型视觉实践”,从而他也就毫不留情地将它们同化于他的“主导模式”(第 7页)。这种阐述的问题在于,视觉经验中的所有异质性预先就注定要落人一种“主导/抵 抗”或“普瑞/局部”的模式,并且(更本质的是)对于克拉利将观者作为“主导模式”这 一个案,从来就没有真正论证过。他有关19世纪观者的描述肯定会从最近有关早期电影观 众的研究中受益,尤其是Charles Musser的《美国电影史,第一卷:电影的兴起:907年自 的美国银幕》(NewYork:Macmillan,1990)以及Miriam Hansen的《巴别塔与巴比伦:美 国默片的观众》(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991)。 18此文下面的部分主要依据我的论文《谱像学与意识形态:潘诺夫斯基、阿尔图塞以
显然,如果图像转向要实现潘诺夫斯基所梦想的批判谱像学,我们需要拆散这块壁毡,而不 只是细加阐述而已。 态,也许我们可以打碎那些镜子并把被压迫的小写主体拯救出那个法力无边的大写主体。 那么,我们有此能力吗?这种“所有意识形态的形式结构”是否像潘诺夫斯基的透视一样, 也是一种特异的历史形成,将会随着生产关系、再生产以及自它们演化而来的社会关系的改 变而时过境迁?或者,它是否(也像潘诺夫斯基的透视一样)是一种普遍的自然结构,将诸 多社会形态及所有历史时期吸收进它的应用范围?如果阿尔图塞采取第一种选择(即作为具 体的历史形态的那一模式),那么他便放弃了他对科学和普遍性的主张;基督教意识形态的 结构可能并不能完全按“伦理的、法律的、政治的、美学的意识形态等等”被复制。这一“等 等”可能包括着与宗教迥异的各种形态,而宗教意识形态本身可能会随历史与文化而变化。 如果阿尔图塞采取第二种选择,坚持镜反模式普遍的科学通性,他就像潘诺夫斯基一样变成 了一个谱像学家,具有一种意识形态而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潘诺夫斯基和阿尔图塞的招呼,怎么也胜过科学与历史的死胡同,胜过意识形态与谱像 学的一种致命的镜映;我们如何才能展示这种招呼?除了在街上扶帽致意外,法国的这位马 克思主义哲学家与德国的那位康德主义艺术史家还能彼此做些什么呢?他们能否像阿尔图 塞那戏剧性的说法,从关着的门两边彼此“招呼”,并且指望对方有所表示,有所应答,而 不会产生成为“日常警察的”怀疑对象这种错误认识?也许不会。从我们迄今为止所描绘出 来的共同空间来看,他们所占据的这一共同空间只不过是把认知场景放置在他们反思的中心。 认知作为意识形态与谱像学之间的联系,其主要重要性在于它对两门“科学”都从认识论的 “认知的”根基(小写主体对客体的知识)转换到一种伦理的、政治的和阐释的根基(小写 主体对小写主体、甚至也许是大写主体对大写主体的知识)。判断的范畴从认知项(teri}ls) 转换到再认知项,从知识的认识论范畴转换到诸如“答谢”这样的社会范畴。阿尔图塞提醒 我们,潘诺夫斯基与图像的关系开始于与大写他者的社会性相遇,他并且指出谱像学是一门 为了把这个他者吸收进一个同质的“统一的”透视之中的科学。潘诺夫斯基则提醒我们,阿 尔图塞关于意识形态所举的当时当地的例证,即小写主体(们)与小写主体(们)的招呼都 被展现在由最高主权的大写主体(们)所构筑的镜子殿堂内,并指出意识形态批判正处于变 成另一种谱像学的危险之中。这些提醒并不能使我们摆脱这一难题,但是可能有助于我们在 看到难题时认出它。 17 乔纳森·克拉利:《观者之技:论 19 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Cambridge,MA: MIT Press,1990);以下页码皆出自此书。克拉利确也注意到,还是存在他的研究所没有 覆盖到的“视觉的实践”,但他把这些实践刻画为“边缘的及局部的形式,抵抗、歪曲或有 缺陷地构建着主导型视觉实践”,从而他也就毫不留情地将它们同化于他的“主导模式”(第 7 页)。这种阐述的问题在于,视觉经验中的所有异质性预先就注定要落人一种“主导/抵 抗”或“普遍/局部”的模式,并且(更本质的是)对于克拉利将观者作为“主导模式”这 一个案,从来就没有真正论证过。他有关 19 世纪观者的描述肯定会从最近有关早期电影观 众的研究中受益,尤其是 Charles Musser 的《美国电影史,第一卷:电影的兴起:1907 年前 的美国银幕》(NewYork:Macmillan,1990)以及 Miriam Hansen 的《巴别塔与巴比伦:美 国默片的观众》(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18 此文下面的部分主要依据我的论文《谱像学与意识形态:潘诺夫斯基、阿尔图塞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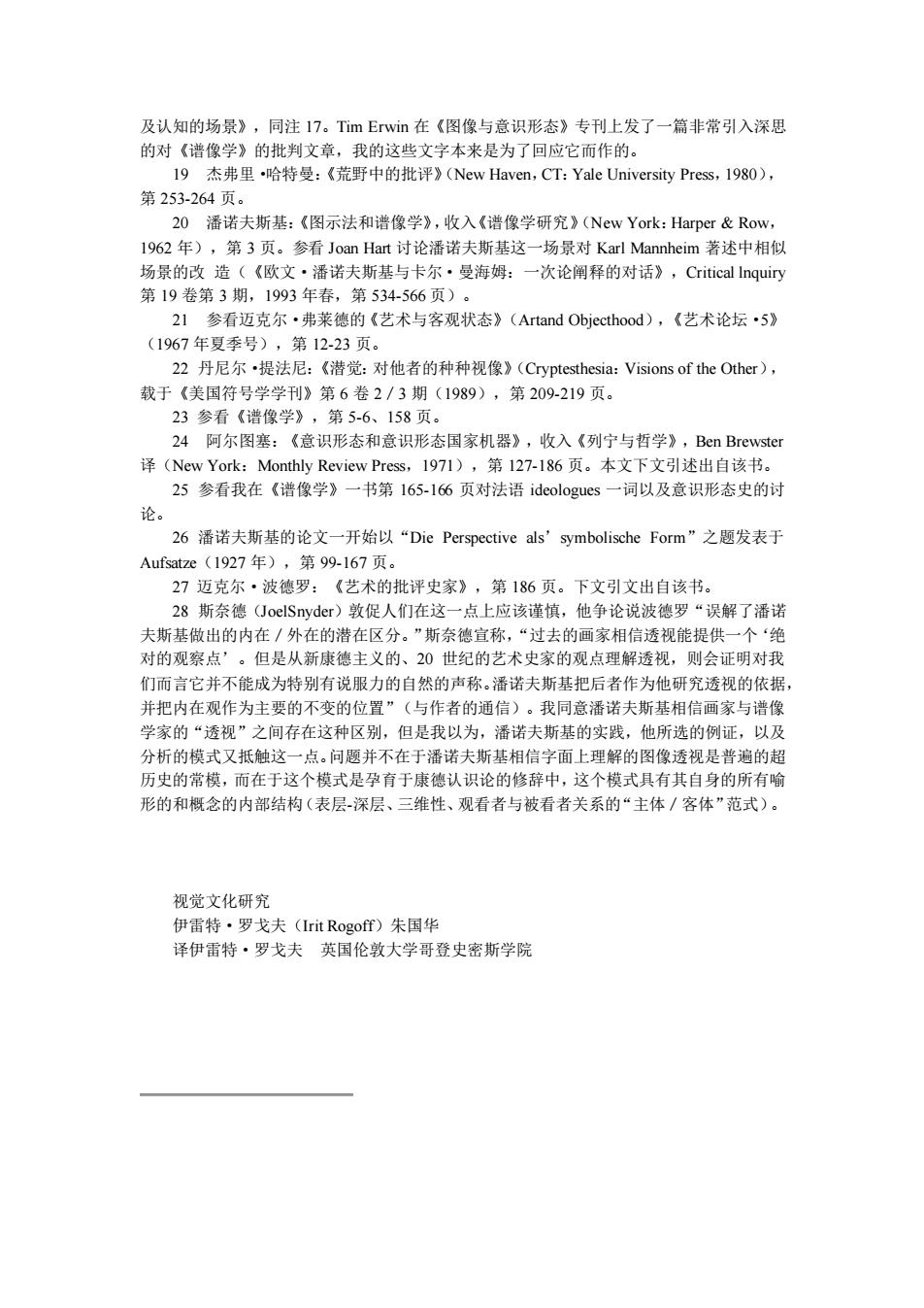
及认知的场景》,同注1门。Tim Erwin在《图像与意识形态》专刊上发了一篇非常引入深思 的对《谱像学》的批判文章,我的这些文字本来是为了回应它而作的 19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O), 第253-264页。 20潘诺夫斯基:《图示法和谱像学》,收入《谱像学研究》(New York:Harper&Row, 1962年),第3页。参看Joan Hart讨论潘诺夫斯基这一场景对Karl Mannheim著述中相似 场景的改造(《欧文·潘诺夫斯基与卡尔·曼海姆: 一次论阐释的对话》,Critical Inquiry 第19卷第3期,1993年春 ,第534566页) 21参看迈克尔·弗莱德的《艺术与客观状态》(Artand Objecthood),《艺术论坛·5》 (1967年夏季号),第12-23页。 22丹尼尔·提法尼:《潜觉:对他者的种种视像》(Cryptesthesia:Visions of the Other) 载于《美国符号学学刊》第6卷2/3期(1989),第209-219页。 23 《谱像学 5-6、158页 24阿尔图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收入《列宁与哲学》,Ben Brewste 译(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1),第127-186页。本文下文引述出自该书。 25参看我在《谱像学》一书第165-166页对法语ideologues一词以及意识形态史的讨 论。 26潘诺夫斯基的论文一开始以“Die Perspective als''symbolische Form”之题发表于 Aufsatze(1927年),第99-167页 27迈克尔·波德罗:《艺术的批评史家》,第186页。下文引文出自该书。 28斯奈德(JoelSnyder)敦促人们在这一点上应该谨慎,他争论说波德罗“误解了潘诺 夫斯基做出的内在/外在的潜在风分。”断奈德宣称,“过去的画家相信诱视能提供一个‘单 对的观察点· 。但是从新康德主义的、0世纪的艺术史家的观点理解透视,则会证明对我 们而言它并不能成为特别有说服力的自然的声称。潘诺夫斯基把后者作为他研究透视的依据 并把内在观作为主要的不变的位置”(与作者的通信)。我同意潘诺夫斯基相信画家与增像 学家的“透视”之间存在这种区别,但是我以为,潘诺夫斯基的实践,他所选的例证,以及 分析的模式又抵触这一点。问题并不在于潘诺夫斯基相信字面上理解的图像透视是普遍的超 历史的常模,而在于这个模式是孕有于康德认识论的修辞中,这个模式具有其自身的所有购 形的和概念的内部结构(表层深层、三维性、观看者与被看者关系的“主体 视觉文化研究 伊雷特·罗戈夫(Irit Rogoff)朱国华 译伊雷特·罗戈夫英国伦敦大学哥登史密斯学院
及认知的场景》,同注 17。Tim Erwin 在《图像与意识形态》专刊上发了一篇非常引入深思 的对《谱像学》的批判文章,我的这些文字本来是为了回应它而作的。 19 杰弗里·哈特曼:《荒野中的批评》(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1980), 第 253-264 页。 20 潘诺夫斯基:《图示法和谱像学》,收入《谱像学研究》(New York:Harper & Row, 1962 年),第 3 页。参看 Joan Hart 讨论潘诺夫斯基这一场景对 Karl Mannheim 著述中相似 场景的改 造(《欧文·潘诺夫斯基与卡尔·曼海姆:一次论阐释的对话》,Critical lnquiry 第 19 卷第 3 期,1993 年春,第 534-566 页)。 21 参看迈克尔·弗莱德的《艺术与客观状态》(Artand Objecthood),《艺术论坛·5》 (1967 年夏季号),第 12-23 页。 22 丹尼尔·提法尼:《潜觉:对他者的种种视像》(Cryptesthesia:Visions of the Other), 载于《美国符号学学刊》第 6 卷 2/3 期(1989),第 209-219 页。 23 参看《谱像学》,第 5-6、158 页。 24 阿尔图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收入《列宁与哲学》,Ben Brewster 译(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1),第 127-186 页。本文下文引述出自该书。 25 参看我在《谱像学》一书第 165-166 页对法语 ideologues 一词以及意识形态史的讨 论。 26 潘诺夫斯基的论文一开始以“Die Perspective als’symbolische Form”之题发表于 Aufsatze(1927 年),第 99-167 页。 27 迈克尔·波德罗:《艺术的批评史家》,第 186 页。下文引文出自该书。 28 斯奈德(JoelSnyder)敦促人们在这一点上应该谨慎,他争论说波德罗“误解了潘诺 夫斯基做出的内在/外在的潜在区分。”斯奈德宣称,“过去的画家相信透视能提供一个‘绝 对的观察点’。但是从新康德主义的、20 世纪的艺术史家的观点理解透视,则会证明对我 们而言它并不能成为特别有说服力的自然的声称。潘诺夫斯基把后者作为他研究透视的依据, 并把内在观作为主要的不变的位置”(与作者的通信)。我同意潘诺夫斯基相信画家与谱像 学家的“透视”之间存在这种区别,但是我以为,潘诺夫斯基的实践,他所选的例证,以及 分析的模式又抵触这一点。问题并不在于潘诺夫斯基相信字面上理解的图像透视是普遍的超 历史的常模,而在于这个模式是孕育于康德认识论的修辞中,这个模式具有其自身的所有喻 形的和概念的内部结构(表层-深层、三维性、观看者与被看者关系的“主体/客体”范式)。 视觉文化研究 伊雷特·罗戈夫(Irit Rogoff)朱国华 译伊雷特·罗戈夫 英国伦敦大学哥登史密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