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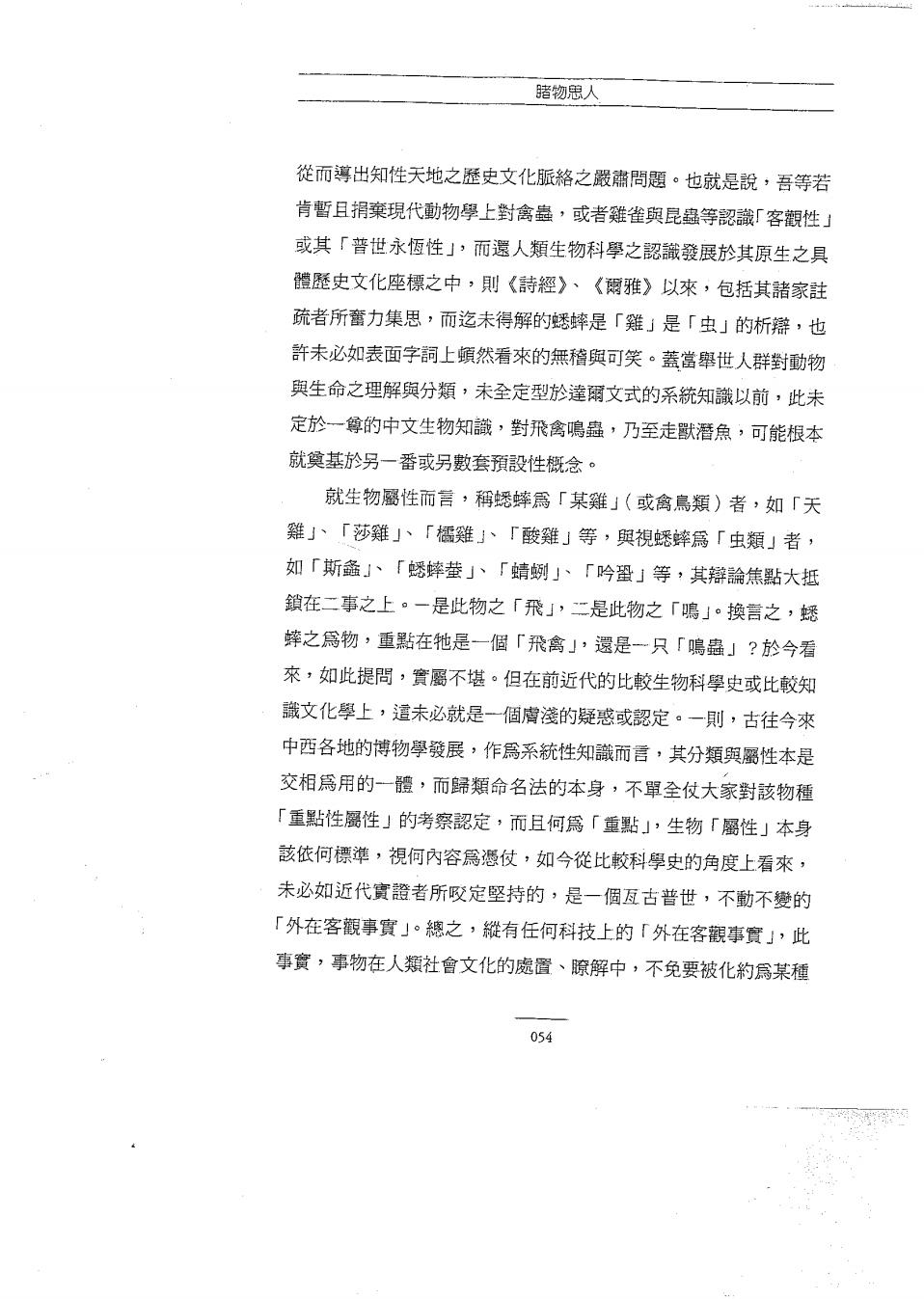
睹物思人 從而導出知性天地之歷史文化脈絡之嚴肅間題。也就是說,吾等若 肯暫且捐棄現代動物學上對禽蟲,或者雞雀與昆蟲等認藏「客觀性」 或其「普世永恆性」,而還人類生物科學之認識發展於其原生之具 體歷史文化座標之中,則《詩經》、《爾雅》以來,包括其諸家註 疏者所奮力集思,而迄未得解的蟋蟀是「雞」是「虫」的析辯,也 許未必如表面字詞上顫然看來的無稽與可笑·蓋當舉世人群對動物 與生命之理解與分類,未全定型於達爾文式的系統知藏以前,此未 定於一算的中文生物知藏,對飛禽鳴蟲,乃至走默潛魚,可能根本 就莫基於另一番或另敷套預設性概念。 就生物屬性而言,稱蟋蟀爲「某雞」(或禽鳥類)者,如「天 雞」~「莎雞」、「櫺雞」、「酸雞」等,與視蟋蟀爲「虫麵」者, 如「斯螽」、「蟋蟀蛬」、「靖蛚」、「吟蛩」等,其辯論焦點大抵 鎖在二事之上。一是此物之「飛」,二是此物之「鳴」·换言之,蟋 蟀之爲物,重點在牠是一個「飛禽」,還是一只「鳴蟲」?於今看 來,如此提間,寶屬不堪。但在前近代的比較生物科學史或比較知 藏文化學上,這未必就是一個膚淺的疑惑或認定。一則,古往今來 中西各地的博物學發展,作爲系統性知識而言,其分類與屬性本是 交相爲用的一醴,而歸類命名法的本身,不單全仗大家對該物種 「重點性屬性」的考察認定,而且何爲「重點」,生物「屬性」本身 蔽依何標準,視何內容篇憑仗,如今從比較科學史的角度上看來, 未必如近代實證者所咬定堅持的,是一個亙古普世,不動不變的 「外在客觀事實」總之,縱有任何科技上的「外在客觀事寶」,此 事竇,事物在人類社會文化的處置、瞭解中,不免要被化約爲某種 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