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加载图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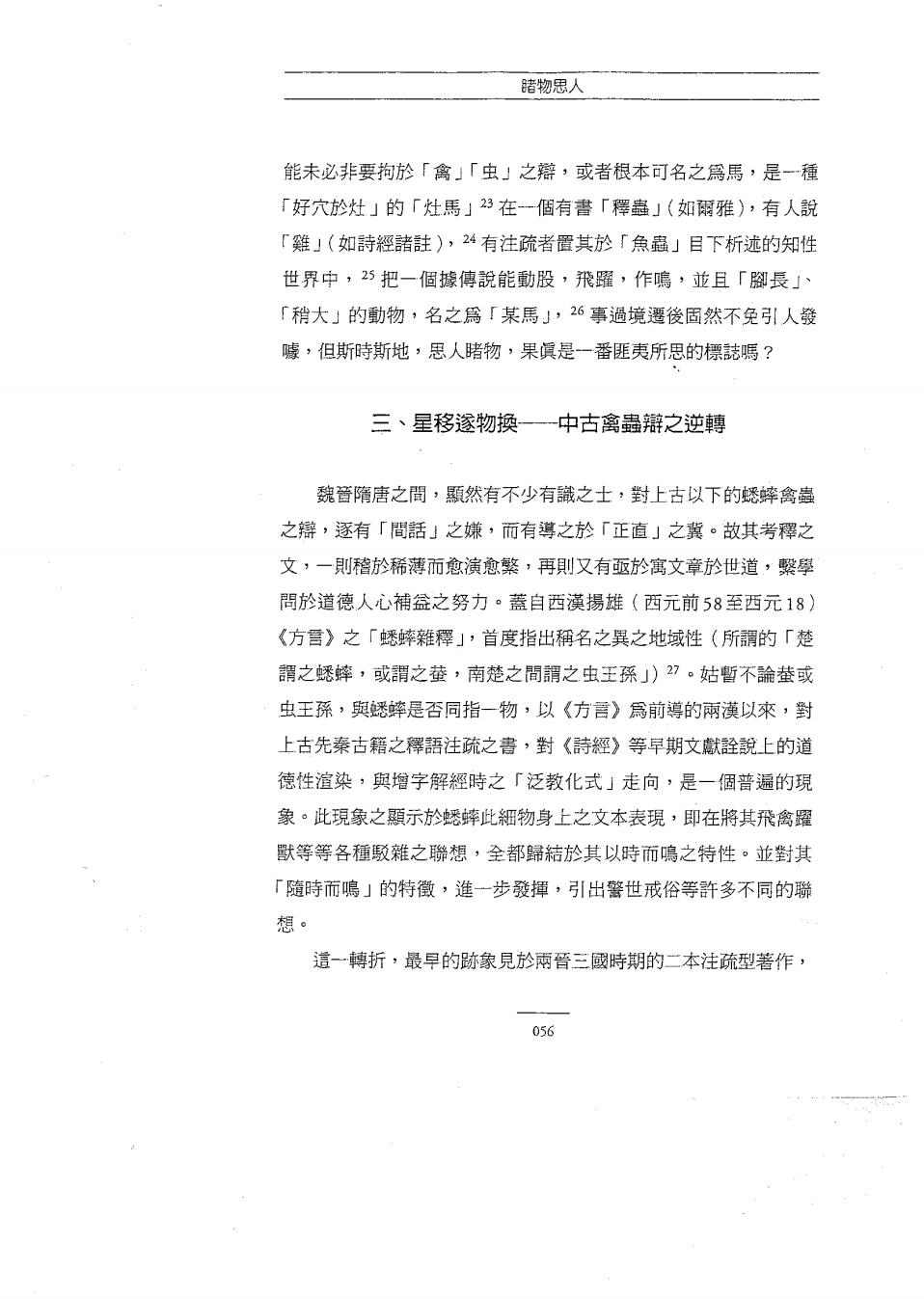
睹物思人 能未必非要拘於「禽」「虫」之幕,或者根本可名之篇馬,是種 「好穴於灶」的「灶馬」23在一個有書「釋蟲」(如爾雅),有人說 「雞」(如詩經藷註),24有注疏者置其於「魚蟲」目下析远的知性 世界中,25把一個據傳說能動股,飛躍,作鳴,並且「腳長」、 「稍大」的動物,名之爲「某馬」,26事過境遷後固然不免引人發 噱,但斯時斯地,思人睹物,果眞是一番匪夷所思的標誌嗎? 三、星移逐物换—中古禽蟲辩之逆轉 魏晉隋唐之間,顯然有不少有識之士·對上古以下的蟋蟀禽蟲 之辯,逐有「間話」之嫌,而有導之於「正直」之冀。故其考釋之 文,一則稽於稀薄而愈演愈繁,再則又有亟於寓文章於世道,繫學 間於道德人心補盒之努力。蓋自西漢揚雄(西元前58至西元18) 《方鲁》之「蟋蟀雜釋」,首度指出稱名之異之地域性(所謂的「楚 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之間謂之虫王孫」)27。姑暫不論蛬或 虫王孫,與蟋蟀是否同指一物,以《方言》爲前導的两漢以來,對 上古先秦古籍之釋語注疏之書,對《詩經》等早期文獻詮說上的道 德性渲染,與增字解經時之「泛教化式」走向,是一個普遍的現 象·此現象之顯示於蟋蟀此細物身上之文本表現,即在將其飛禽躍 獸等等各種駁雜之聯想,全都歸結於其以時而鳴之特性。並對其 「隨時而鳴」的特徵,進一步發揮,引出警世戒俗等許多不同的聯 想。 這一轉折,最早的胁象見於雨晉三國時期的二本注疏型著作, 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