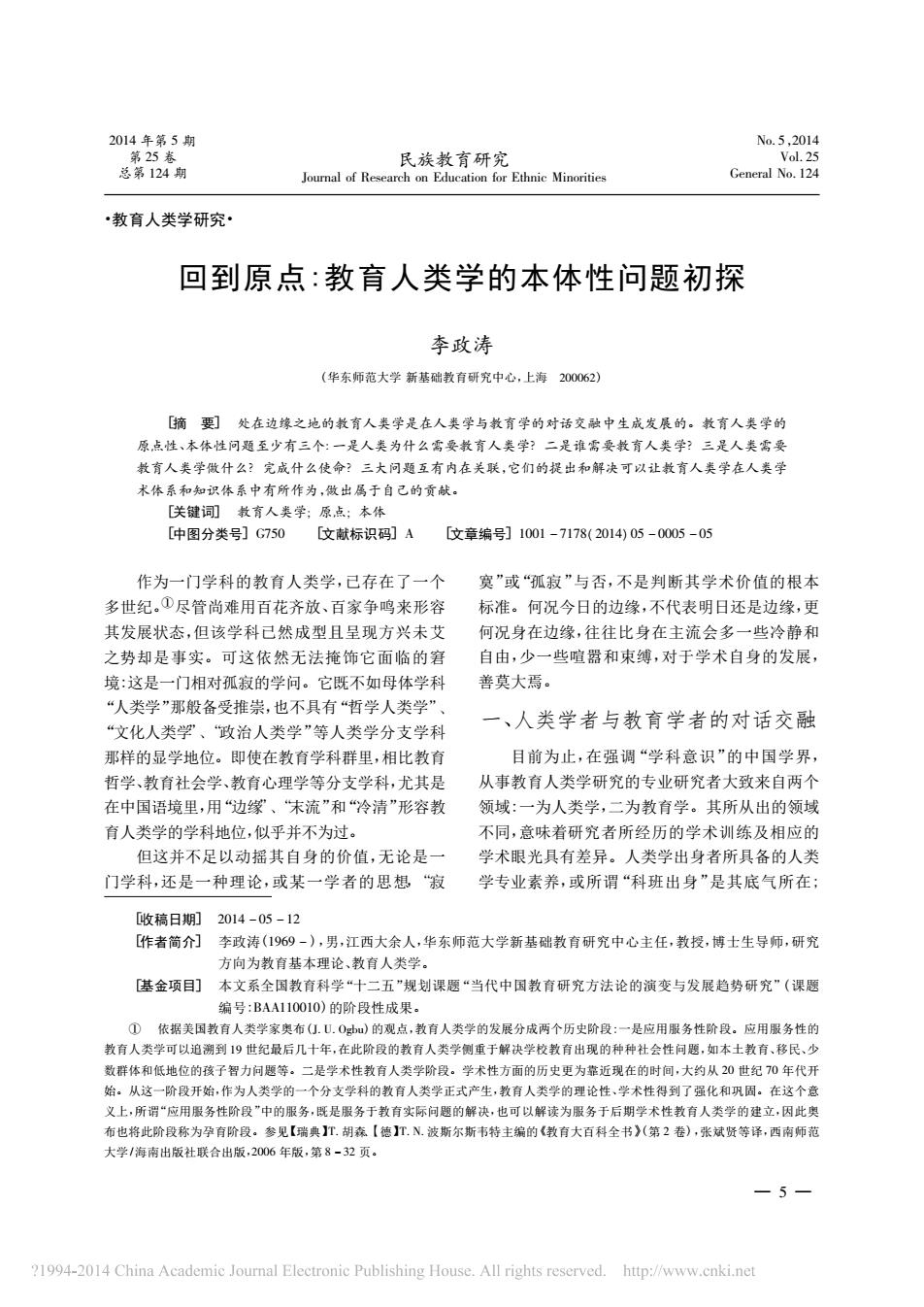
2014年第5期 民族教有研究 Joumal of Research Educationo Ethnic Minorities 教育人类学研究, 回到原点:教育人类学的本体性问题初探 李政涛 (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有研究中心,上海200062) 摘夏处在边球之地的牧育人类学是在人类学与教育学的对话交融中生成发展的。教育人类学的 原点性、本休性问题至少有三个:一是人类为什么需要教有人类学:二是谁需要教育人类学:三是人奏需要 教育人类学微什么?完成什么使命:三大问题互有内在关联,它们的提出和解决可以让教育人类学在人类学 术体系和知识体系中有所作为,微出属于自己的贡能。 送键词牧育人类学:原点:本体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178(2014)05-0005-05 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人类学,己存在了一个 突”或“孤寂”与否,不是判断其学术价值的根本 多世纪。①尽管尚难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形容 标准。何况今日的边缘,不代表明日还是边缘,更 其发展状态,但该学科已然成型且呈现方兴未艾 何况身在边缘,往往比身在主流会多一些冷静和 之势却是事实。可这依然无法掩饰它面临的窘 自由,少一些喧嚣和束缚,对于学术自身的发展, 境:这是一门相对孤寂的学问。它既不如母体学科 善莫大焉。 “人类学”那般备受推崇,也不具有“哲学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等人类学分支学科 一、人类学者与教育学者的对话交融 那样的显学地位。即使在教育学科群里,相比教育 目前为止,在强调“学科意识”的中国学界, 哲学,教有社会学教育心理学等分支学科,尤其是 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专业研究者大致来自两个 在中国语境里,用“边缘 末流”和“冷清”形容载 领城: 一为人类学,二为教育学。其所从出的领域 育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似乎并不为过。 不同,意味着研究者所经历的学术训练及相应的 但这并不足以动摇其自身的价值,无论是一 学术眼光只有差异。人类学出身者所只备的人类 门学科,还是一种理论,或某一学者的思想“寂 学专业素养,或所谓“科班出身”是其底气所在 [收稿日期2014-05 作者简介」李政涛(1969 -),男,江西大余人,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有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 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人类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当代中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演变与发展趋势研究”(课题 编号:BAA110010)的阶段性成 依据美国教有人类 的 ,教有人类学的发服分成两个 历史阶段 一是应用服务性阶段。 应用服务性的 始。从这一阶段开始,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教有人类学正式产生,教有人类学的 理论性多性到了化 用调。在这个 义上,所调“应用图多性阶段”中的民务,降是置多于教百实际问题的解决,也可以解速为服务于后期学术性教育人类学的建立,因此 布也将此阶段称为孕有阶段。参见【瑞典工.胡森【德江.X被斯尔斯韦特主编的《锁育大百科全书》(第2卷),张斌贤等译,西南师范 大学/海南出版社联合出版,2006年版,第8-32页, 5 194-014 China Academie Joum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2014 年第 5 期 第 25 卷 总第 124 期 民族教育研究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 No. 5,2014 Vol. 25 General No. 124 [收稿日期] 2014 - 05 - 12 [作者简介] 李政涛( 1969 - ) ,男,江西大余人,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 方向为教育基本理论、教育人类学。 [基金项目]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当代中国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演变与发展趋势研究”( 课题 编号: BAA110010) 的阶段性成果。 ① 依据美国教育人类学家奥布( J. U. Ogbu) 的观点,教育人类学的发展分成两个历史阶段: 一是应用服务性阶段。应用服务性的 教育人类学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在此阶段的教育人类学侧重于解决学校教育出现的种种社会性问题,如本土教育、移民、少 数群体和低地位的孩子智力问题等。二是学术性教育人类学阶段。学术性方面的历史更为靠近现在的时间,大约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 始。从这一阶段开始,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教育人类学正式产生,教育人类学的理论性、学术性得到了强化和巩固。在这个意 义上,所谓“应用服务性阶段”中的服务,既是服务于教育实际问题的解决,也可以解读为服务于后期学术性教育人类学的建立,因此奥 布也将此阶段称为孕育阶段。参见【瑞典】T. 胡森、【德】T. N. 波斯尔斯韦特主编的《教育大百科全书》( 第 2 卷) ,张斌贤等译,西南师范 大学/海南出版社联合出版,2006 年版,第 8 - 32 页。 ·教育人类学研究· 回到原点: 教育人类学的本体性问题初探 李政涛 ( 华东师范大学 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上海 200062) [摘 要] 处在边缘之地的教育人类学是在人类学与教育学的对话交融中生成发展的。教育人类学的 原点性、本体性问题至少有三个: 一是人类为什么需要教育人类学? 二是谁需要教育人类学? 三是人类需要 教育人类学做什么? 完成什么使命? 三大问题互有内在关联,它们的提出和解决可以让教育人类学在人类学 术体系和知识体系中有所作为,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 教育人类学; 原点; 本体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 7178( 2014) 05 - 0005 - 05 作为一门学科的教育人类学,已存在了一个 多世纪。①尽管尚难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来形容 其发展状态,但该学科已然成型且呈现方兴未艾 之势却是事实。可这依然无法掩饰它面临的窘 境: 这是一门相对孤寂的学问。它既不如母体学科 “人类学”那般备受推崇,也不具有“哲学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等人类学分支学科 那样的显学地位。即使在教育学科群里,相比教育 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等分支学科,尤其是 在中国语境里,用“边缘”、“末流”和“冷清”形容教 育人类学的学科地位,似乎并不为过。 但这并不足以动摇其自身的价值,无论是一 门学科,还是一种理论,或某一学者的思想,“寂 寞”或“孤寂”与否,不是判断其学术价值的根本 标准。何况今日的边缘,不代表明日还是边缘,更 何况身在边缘,往往比身在主流会多一些冷静和 自由,少一些喧嚣和束缚,对于学术自身的发展, 善莫大焉。 一、人类学者与教育学者的对话交融 目前为止,在强调“学科意识”的中国学界, 从事教育人类学研究的专业研究者大致来自两个 领域: 一为人类学,二为教育学。其所从出的领域 不同,意味着研究者所经历的学术训练及相应的 学术眼光具有差异。人类学出身者所具备的人类 学专业素养,或所谓“科班出身”是其底气所在; — 5 —

教育学出身者则有更多对教育自身的了解与体 么使命? 验,在强调“亲历性”和“体验性”因而具有典型 “体知之学”特征的人类学那里,这或许也是一种 二、为什么需要教育人类学 代势。与所有教育学交叉学科一样,两大学科背 以往阐述教育人类学的提问方式,常常以 景的研究者在基于差异的“平等对话”中“取长补 “什么是教育人类学”或“教育人类学是什么”为 短、互动共生”,构成了教育人类学发展的动力 代表,与此“内涵性质”的提问方式不同,我们转 源泉。 而进行“意义”和“价值”性质的追问:教育人类等 最典型的个案莫如“人种志”和“民族志”的 这门学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名称争议。同一个文词(E山m 学出身的可 如此转变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启发。这位终 两种译法。 生孜孜于“存在”问题的大哲,之所以能将“存在 究者主张用民族志,教育学出身的学者则习惯于 这一古老问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来源于 用“人种志”。①排除使用者的个人偏好因素,选 两种转换 是将作为名词意义的“存在”转换为 择背后的学术训练和专业背景更为关键:有民族 动词性质的“存在”,即“去存在”:二是从“存在是 学学术训练和专业背景、深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 什么”转换为“存在有什么意义”,并以此作为探 研究语 和制度等 问题的研究者,倾向于采月用 究的逻辑起点,其深意在于:只有确定了一物存在 民族志”的概念。有哲学人类学的学术背景、且 的意义,才能明了其内涵,价值、意义决定了内涵 讲入学校语境尤其是讲入课堂和班级生话内部的 物的存在有何种价值与意义,就有何种内涵 研究者,由于其研究对象民族背景和差异不鲜明 同理,只有预先明确“教人类学有何存在 研究预设里也没有进行民族文化特征背景的比 的价值与意义”,方能领悟“教育人类学是什么” 分析,可能就更倾向于用“人种志 笔者曾以 才能展开对各种或基本或具体的概念和问题的探 为,相对而言,“人种志”的含义更为广泛,也更接 讨,无此前提,任何劳心劳力的苦思冥想和田野操 沂“人类学”的本意高:“人的改变之道”,而不是“民 作都可能沦为空无。 族的改变之”。“民族志”容易被误解为只是以 “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与人类学家 为此,教育人类学的宇宙来源于这一“原点 的对话,尤其是对 词的词源学分 问题”的爆发:为什么需要教育人类学? 此问题的用意是想探问:既然人类己存在种 析,2使笔者形成了新的理解和认识:至少“人科 志”的使用中内含“种族问题”,其而可能蕴含若 种学科、学说和学问,为什么还会出现命名为“教 “种族歧视”的嫌疑。笔者陡然警醒,由此丰富并 育人类学”的存在?它究竟为何产生?为何有 清晰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认识 在?能够满足何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笔者长年从事“教育 基 本理论”方向的研究 此问题还预设了一种差异分析:有此学科和 习惯于关注和思考基本问题或本体性的问题。因 无此学科、有此学说和无此学说,究竟有何不同? 此,当讲入教有人举学世界之初,扑面而来的问颗 此问题更内蕴了一种判断或评价标准:教育 都与本体性间题有关。学科意义上的本体性问题 人类学及其研究者所做之事、所言之语、所做之员 往往是涉及学科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本源性质的 献,是否为该学科所独有?如果聚焦于某一公共 问题,因而是原点性问题,研究中的所有具体问题 问题,如“学习”问题、“跨文化教育”问题,不从事 既原发其中,也需回归其中。 此学科研究之人,也能讲出专业教育人类学学考 教育人类学的本体性问题至少有三个:一是 所讲的观点或结论,那么,教育人类学者还有何存 人类为什么需要教育人类学?二是谁需要教有人 在的必要?这一学科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类学?三是人类需要教有人类 干什么? 完成什 任何价值和意义都有相对而,都是相对王 ①例如:冯增俊著《做有人类学教程》.人民教有出版社205年版,李政海著《有人类学引论上海教有出板社2008年板。两 本书中都采用的是“人种志”】 6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m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
教育学出身者则有更多对教育自身的了解与体 验,在强调“亲历性”和“体验性”因而具有典型 “体知之学”特征的人类学那里,这或许也是一种 优势。与所有教育学交叉学科一样,两大学科背 景的研究者在基于差异的“平等对话”中“取长补 短”、“互动共生”,构成了教育人类学发展的动力 源泉。 最典型的个案莫如“人种志”和“民族志”的 名称争议。同一个英文词( Ethnography) 出现了 两种译法。目前来看,人类学或民族学出身的研 究者主张用民族志,教育学出身的学者则习惯于 用“人种志”。① 排除使用者的个人偏好因素,选 择背后的学术训练和专业背景更为关键: 有民族 学学术训练和专业背景、深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 研究语言和制度等问题的研究者,倾向于采用 “民族志”的概念。有哲学人类学的学术背景、且 进入学校语境尤其是进入课堂和班级生活内部的 研究者,由于其研究对象民族背景和差异不鲜明, 研究预设里也没有进行民族文化特征背景的比较 分析,可能就更倾向于用“人种志”。笔者曾以 为,相对而言,“人种志”的含义更为广泛,也更接 近“人类学”的本意: “人的改变之道”,而不是“民 族的改变之道”。“民族志”容易被误解为只是以 “少数民族”地区为研究对象。通过与人类学家 的对话,尤其是对 Ethnography 一词的词源学分 析,②使笔者形成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至少“人种 志”的使用中内含“种族问题”,甚而可能蕴含着 “种族歧视”的嫌疑。笔者陡然警醒,由此丰富并 清晰了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认识。 笔者长年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方向的研究, 习惯于关注和思考基本问题或本体性的问题。因 此,当进入教育人类学世界之初,扑面而来的问题 都与本体性问题有关。学科意义上的本体性问题 往往是涉及学科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本源性质的 问题,因而是原点性问题,研究中的所有具体问题 既原发其中,也需回归其中。 教育人类学的本体性问题至少有三个: 一是 人类为什么需要教育人类学? 二是谁需要教育人 类学? 三是人类需要教育人类学干什么? 完成什 么使命? 二、为什么需要教育人类学 以往阐述教育人类学的提问方式,常常以 “什么是教育人类学”或“教育人类学是什么”为 代表,与此“内涵性质”的提问方式不同,我们转 而进行“意义”和“价值”性质的追问: 教育人类学 这门学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何在? 如此转变是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启发。这位终 生孜孜于“存在”问题的大哲,之所以能将“存在” 这一古老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来源于 两种转换: 一是将作为名词意义的“存在”转换为 动词性质的“存在”,即“去存在”; 二是从“存在是 什么”转换为“存在有什么意义”,并以此作为探 究的逻辑起点,其深意在于: 只有确定了一物存在 的意义,才能明了其内涵,价值、意义决定了内涵。 一物的存在有何种价值与意义,就有何种内涵。 同理,只有预先明确“教育人类学有何存在 的价值与意义”,方能领悟“教育人类学是什么”, 才能展开对各种或基本或具体的概念和问题的探 讨,无此前提,任何劳心劳力的苦思冥想和田野操 作都可能沦为空无。 为此,教育人类学的宇宙来源于这一“原点 问题”的爆发: 为什么需要教育人类学? 此问题的用意是想探问: 既然人类已存在种 种学科、学说和学问,为什么还会出现命名为“教 育人类学”的存在? 它究竟为何产生? 为何存 在? 能够满足何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此问题还预设了一种差异分析: 有此学科和 无此学科、有此学说和无此学说,究竟有何不同? 此问题更内蕴了一种判断或评价标准: 教育 人类学及其研究者所做之事、所言之语、所做之贡 献,是否为该学科所独有? 如果聚焦于某一公共 问题,如“学习”问题、“跨文化教育”问题,不从事 此学科研究之人,也能讲出专业教育人类学学者 所讲的观点或结论,那么,教育人类学者还有何存 在的必要? 这一学科还有什么存在价值? 任何价值和意义都具有相对面,都是相对于 — 6 — ① ② 例如: 冯增俊著《教育人类学教程》,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李政涛著《教育人类学引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两 本书中都采用的是“人种志”。 笔者曾经就此问题分别咨询过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和巴战龙,他们一致认定应使用“民族志”,而不是“人种志”。后者对 Ethnography 进行了词源学的梳理,认证了“民族志”更适合其英语本意

某种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若以教育学理论和教育 方式在猎奇者看来比较新奇,也不只是因为这种 实践为相对面,教育人类学有何意义? 知识对于在不发达国家工作的人大有裨益,而是 在德国教直学界,对“教官人举学”的重视是 因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能帮助我们明白 其学术传统之一,无论研究者从事何种教育学分 自己的习惯和风俗。”回 支学科的研究方向,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我 这样的传统几乎不会考虑那些身处田野之地 的教育人类学基础是什?“我”如何理解人? 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群的需要,所谓的“主体”只属 有没有自己的人性论? 于研究者自身,即便采用“主位研究法”的研另 与“文学”纯人文学科相比,教有学的“人学 者,仍状沿有的变其“为已”而不品“为怕”的终极 特性更为明显,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教育,自始至终 目的。即使加博厄断这般以“拯救潮消浙文 是直面人,为了人和在人的发展中的活动。是否 化”为己任的人类学家,也是基于自我文化跟为 了解人,是否能够洞察人,成为所有以教育学为 的观照,而且其念兹在兹的依然是“文化”,而不 之人的必备本领。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学科比 是文化中的“人”。 “教育人类学”更有优势、更有资格传承和放大 显而易见,教有人类学的产生最初来自于作 “人的改变之道”这一人类学的学术台趣。它的 为理论研究著的教人举学家自身的看要,或品 所有研究都是对教育学研究需要“目中有人”、需 为了满足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或是视为谋生手 要以对人的解读和把握为起点等基本原则的具体 段、扬名工具,或是为了学科建设和理论探索:为 体现和转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育人 了成为书伯意义上的“以教育人类学为业”之人 类学既是教育学理论研究,也是教育实践的共有 抑或将此与自我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将学术与 基石 生命联通起来等,无论是处在何种需要层次,都上 若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将“相对面 ”加以延伸 “己”有关,而与“他”无关 我们还可以追问:有教育人类学和没有教育人类 在教育政策学逐渐成为当下中国教育学科 学,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什么不同?人类的学术 中显学的大背景下,置身于行政平台上的教育决 世界、知识体系有什么不同?同样,人类学的世 策者,自然也成为教育人类学的需要者。这一需 界、民族学的师域,因为有了数有人学的存在 要并非新生事物,费孝通先生当年诸多有关“乡 又将有什么不同? 土中国”的田野研究,早就被置于决策者的案头 如果教有人类学能对上述向题都有清晰明确 之上。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出版后 一度 的回答,①将成为须臾不可动摇的学科磐石。 某些地方的行政官员集体阅读,几乎达到了人手 ·册。作为当代中国教育人类学代表人物之一的 三、谁需要教育人类学 碳早,在其成名作《文化变迁与双善教 这是一个长久被遗忘的问题,它的另一种 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 达方式是“为谁的教有人类学” 书最后一,就有编辑的如下宜传语 “本书 在人类学的传统之中,拥有一个不言而喻的 国内第一部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 答案“为己”的人类学,即为满足研究者及其所 中国具有异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教育进行的细致 从属文化的需要而在在的人类学 离我远去” 研究。其研究结果将为有关部门在制定少数民能 后在“异域民族”与“他者文化”之地的“参与 双语教育政策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我们 察”,不过是为了返归本我的文化,人类学家相 然对此乐观其成,基于实的田野基础上的决策 信,这样的反观有助于对自己文化的清晰认识。 总比坐在办公室的摇椅里玄想形成的决策更为可 弗思的观点领有代表性“作为一位人类学者,我 靠。而且在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在真正的田 将注重那些生活方式和西方文明不同的人民的习 野工作基出上形成的民族志文本,能够带来只靠 惯和风俗。我注重他们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 通过调查统计进而层层上报后生成的量化数据 ·参见李玫涛著《敏育人类学引论》,上海教有出版社2008年饭, 一章第一节中提到人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 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www.cnki.ne
某种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若以教育学理论和教育 实践为相对面,教育人类学有何意义? 在德国教育学界,对“教育人类学”的重视是 其学术传统之一,无论研究者从事何种教育学分 支学科的研究方向,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我” 的教育人类学基础是什么? “我”如何理解人? 有没有自己的人性论? 与“文学”等人文学科相比,教育学的“人学” 特性更为明显,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教育,自始至终 是直面人、为了人和在人的发展中的活动。是否 了解人,是否能够洞察人,成为所有以教育学为业 之人的必备本领。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学科比 “教育人类学”更有优势、更有资格传承和放大 “人的改变之道”这一人类学的学术旨趣。它的 所有研究都是对教育学研究需要“目中有人”、需 要以对人的解读和把握为起点等基本原则的具体 体现和转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育人 类学既是教育学理论研究,也是教育实践的共有 基石。 若以上述分析为基础将“相对面”加以延伸, 我们还可以追问: 有教育人类学和没有教育人类 学,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有什么不同? 人类的学术 世界、知识体系有什么不同? 同样,人类学的世 界、民族学的领域,因为有了教育人类学的存在, 又将有什么不同? 如果教育人类学能对上述问题都有清晰明确 的回答,①将成为须臾不可动摇的学科磐石。 三、谁需要教育人类学 这是一个长久被遗忘的问题,它的另一种表 达方式是“为谁的教育人类学”。 在人类学的传统之中,拥有一个不言而喻的 答案: “为己”的人类学,即为满足研究者及其所 从属文化的需要而存在的人类学。“离我远去” 后在“异域民族”与“他者文化”之地的“参与观 察”,不过是为了返归本我的文化,人类学家相 信,这样的反观有助于对自己文化的清晰认识。 弗思的观点颇有代表性: “作为一位人类学者,我 将注重那些生活方式和西方文明不同的人民的习 惯和风俗。我注重他们并不只是因为他们的生活 方式在猎奇者看来比较新奇,也不只是因为这种 知识对于在不发达国家工作的人大有裨益,而是 因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能帮助我们明白 自己的习惯和风俗。”[1] 这样的传统几乎不会考虑那些身处田野之地 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群的需要,所谓的“主体”只属 于研究者自身,即便采用“主位研究法”的研究 者,仍然没有改变其“为己”而不是“为他”的终极 目的。即使如博厄斯这般以“拯救濒临消逝文 化”为己任的人类学家,也是基于自我文化眼光 的观照,而且其念兹在兹的依然是“文化”,而不 是文化中的“人”。 显而易见,教育人类学的产生最初来自于作 为理论研究者的教育人类学家自身的需要,或是 为了满足对异域文化的好奇心,或是视为谋生手 段、扬名工具,或是为了学科建设和理论探索; 为 了成为韦伯意义上的“以教育人类学为业”之人, 抑或将此与自我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将学术与 生命联通起来等,无论是处在何种需要层次,都与 “己”有关,而与“他”无关。 在教育政策学逐渐成为当下中国教育学科群 中显学的大背景下,置身于行政平台上的教育决 策者,自然也成为教育人类学的需要者。这一需 要并非新生事物,费孝通先生当年诸多有关“乡 土中国”的田野研究,早就被置于决策者的案头 之上。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出版后,一度被 某些地方的行政官员集体阅读,几乎达到了人手 一册。作为当代中国教育人类学代表人物之一的 滕星,在其成名作《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 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 一书最后一页,就有编辑的如下宣传语: “本书是 国内第一部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对 中国具有异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教育进行的细致 研究。其研究结果将为有关部门在制定少数民族 双语教育政策方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我们自 然对此乐观其成,基于扎实的田野基础上的决策, 总比坐在办公室的摇椅里玄想形成的决策更为可 靠。而且在这样一个“大数据”时代,在真正的田 野工作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志文本,能够带来只靠 通过调查统计进而层层上报后生成的量化数据难 — 7 — ① 笔者曾经对此做了初步的尝试性回答。参见李政涛著《教育人类学引论》,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一章第一节中提到人 类社会需要教育人类学

以带来的“真实”。这种定性意义上的真实,往往 理导致的谴遮掩掩、推三阻四等诸多行为也接踵 比定量意义上的“真实”更值得信任,前者根源于 而至.既然“你”的研究只对“你”有益,而对 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特有优势:严格的长期循环 “我”无益,我何必.随后,是否接纳研究者前 式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来“打捞”,给子他们多少“可捞之物” ,成为研 除了理论研究者和决策者之外,还有谁需要 对象对研究者的一种“恩國”。 教育人类学?在已有的教育人类学,乃至整体人 基于“纳流”取向的田野工作,研究著的形象 类学系统中,很少将作为田野研究对象或参与观 如同“江湖术土”和“谋士”,摇着羽。,☑着烟斗 察对象的被研究者,如校长、教师和学生等作为需 品者茶水,随时观察实践中的动态和每个细节,随 要满足的对象。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 后发表各种感概和评论。他的心态是悠闲的、赏 的视野 他们”有没 我 ”的需 玩的,仿佛在看一幅窗外的风景,无论或美或丑 们”的研究是否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以及他们 都与己无关,只是自己“窗外”的风最而己. 的生活或者人生是否能够因为我们的研究而发生 两种取向共同的特点是“旁观 ,是以“局 某种改变? 人”的身份,把“田野”作为旁观的对象,可以捕提 在部分理论研究者看来,这些问题不是“我 它的资源、观察和平说它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 们“的问题,它们违背 “价值中立 的原则 研分 否需要解决和怎么解决,不是“我”的问题,只是 者不应也不能干预研究对象的生活。然而,当 “你”的问题,因为这不是“我”的需要,而是“你 “我们”讲入田野,讲入他们的生活世界并与其其 的需要。 同生活时,我们”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参 与这种“密观著”立场相对的是“介入著” 与现空”,己经不可避龟地 种入和干预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介入和干预为何目的 场,笔者曾经指出,前者是传统典型的“人类学立 具有何种性质?四 场”,后者即所谓“教育学立场”。现在看来,这 种对人类学立场与教有学立场的截然区分,可能 如上问颗与研究立场及价值取向有关。长 是一种人为的对立,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都可能 以来,进入田野的目的是“为己”的“打捞”和“纳 凉”回 存在这两种立场,都可能在主张“贴地深度”研究 基于“打捞”取向的田野工作,将“实践”视》 的同时,在“是否介入”和“如何介入”等方面裹 不前。只不时人类学的传统取向更加倾向于基于 个资料库和捕鱼场,研究者带着“渔网”和各科 “诱饵”,还有“灵敏的嗅觉与视觉”,“驾临”教自 “局外人”的“旁观”,而不是基于“局内人”的“ 田野,通过“问卷、“访谈”、“搜集各种口头和纸 入”。但对此角色及其立场的困惑、反思和质 面素材”等方式,捕捉有助于完成“课题 也时有发生。 论文”和 究报告的 小鱼类 ,回 向题的根本依然需要回到“介入”的目的,同 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点“战利品”,总结“打捞 样是做“贴地深度介入式”研究,这样的“介入”是 成果”。至于这次“打捞活动”对于所去学校及教 为己”,还是“为他”,或是兼而有习 “为他”之 师有何影响,基本不在其视野范围之内,这是一种 目的回答的是如下问题:教有人类学的研究是否 纯粹自我”的研究活动。面对这样的“打捞”,研 需要通过介入真实改变教师和学生的日常教育生 究对象初期会予以“配合”,散开“渔场 ,让“打 活?包括改变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思维方式及 者”无限“畅捞”,但拥有“实践智慧”的他们,迟早 行为: 会意识到自己被利用的工具角色,因而由厌烦心 一旦教育人类学将上述问题纳入自身思考和 and C Not Talking Pust Each Othe gv Ed 32(3)373 参见瓦尔·科里克一佩斯克著《“自己的民族社区内“进行民族志研究 位检的局内人的经验》,载【大利亚】林恩·休 ”和“局外人”自 题的反思。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
以带来的“真实”。这种定性意义上的真实,往往 比定量意义上的“真实”更值得信任,前者根源于 人类学民族志研究的特有优势: 严格的长期循环 式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 除了理论研究者和决策者之外,还有谁需要 教育人类学? 在已有的教育人类学,乃至整体人 类学系统中,很少将作为田野研究对象或参与观 察对象的被研究者,如校长、教师和学生等作为需 要满足的对象。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进入研究者 的视野: “他们”有没有对“我们”的需要? “我 们”的研究是否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 以及他们 的生活或者人生是否能够因为我们的研究而发生 某种改变? 在部分理论研究者看来,这些问题不是“我 们”的问题,它们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原则: 研究 者不应也不能干预研究对象的生活。然而,当 “我们”进入田野,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并与其共 同生活时,“我们”通过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参 与观察”,已经不可避免地是一种介入和干预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 这些介入和干预为何目的? 具有何种性质?① 如上问题与研究立场及价值取向有关。长期 以来,进入田野的目的是“为己”的“打捞”和“纳 凉”。[2] 基于“打捞”取向的田野工作,将“实践”视为 一个资料库和捕鱼场,研究者带着“渔网”和各种 “诱饵”,还有“灵敏的嗅觉与视觉”,“驾临”教育 田野,通过“问卷”、“访谈”、“搜集各种口头和纸 面素材”等方式,捕捉有助于完成“课题”、“专 著”、“论文”和“研究报告”的“大小鱼类”,回家 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清点“战利品”,总结“打捞 成果”。至于这次“打捞活动”对于所去学校及教 师有何影响,基本不在其视野范围之内,这是一种 “纯粹自我”的研究活动。面对这样的“打捞”,研 究对象初期会予以“配合”,敞开“渔场”,让“打捞 者”无限“畅捞”,但拥有“实践智慧”的他们,迟早 会意识到自己被利用的工具角色,因而由厌烦心 理导致的遮遮掩掩、推三阻四等诸多行为也接踵 而至.既然“你”的研究只对“你”有益,而对 “我”无益,我何必.随后,是否接纳研究者前 来“打捞”,给予他们多少“可捞之物”,成为研究 对象对研究者的一种“恩赐”。 基于“纳凉”取向的田野工作,研究者的形象 如同“江湖术士”和“谋士”,摇着羽扇,叼着烟斗, 品着茶水,随时观察实践中的动态和每个细节,随 后发表各种感慨和评论。他的心态是悠闲的、赏 玩的,仿佛在看一幅窗外的风景,无论或美或丑, 都与己无关,只是自己“窗外”的风景而已. 两种取向共同的特点是“旁观”,是以“局外 人”的身份,把“田野”作为旁观的对象,可以捕捉 它的资源、观察和评说它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是 否需要解决和怎么解决,不是“我”的问题,只是 “你”的问题,因为这不是“我”的需要,而是“你” 的需要。 与这种“旁观者”立场相对的是“介入者”立 场,笔者曾经指出,前者是传统典型的“人类学立 场”,后者即所谓“教育学立场”。[3]现在看来,这 种对人类学立场与教育学立场的截然区分,可能 是一种人为的对立,实际上任何一个学科都可能 存在这两种立场,都可能在主张“贴地深度”研究 的同时,在“是否介入”和“如何介入”等方面裹足 不前。只不过人类学的传统取向更加倾向于基于 “局外人”的“旁观”,而不是基于“局内人”的“介 入”。但对此角色及其立场的困惑、反思和质疑 也时有发生。② 问题的根本依然需要回到“介入”的目的,同 样是做“贴地深度介入式”研究,这样的“介入”是 “为己”,还是“为他”,或是兼而有之? “为他”之 目的回答的是如下问题: 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是否 需要通过介入真实改变教师和学生的日常教育生 活? 包括改变教师的教育教学观念、思维方式及 行为? 一旦教育人类学将上述问题纳入自身思考和 — 8 — ① ② 这些问题的背后涉及教育理论研究( 者) 和实践( 者) 的角色差异,其实也是理论取向和实践取向的差异。可 参 见: Lorie Hammond and George Spidler. Not Talking Past Each Other: Cultural Role in Education Research. Anthropology£ Education Quarterly 32( 3) : 373 - 378,2001. Linda Harklau and Rachel Norwood. Negtotiating Researcher Roles in Ethnograhic Program Evaluation: A Postmodern Lens. Anthropology£ Education Quarterly 36( 2) : 278 - 288,2005. 参见瓦尔·科里克 - 佩斯克著《“自己的民族社区内”进行民族志研究———一位尴尬的局内人的经验》,载【澳大利亚】林恩·休 谟、简·穆拉克《人类学家在田野》( 龙菲、徐大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06 - 122 页。虽然这里的“局内人”和“局外人”的 划分标准是研究者自身的文化身份,而不是“旁观”或是“介入”,但已经可以从中一瞥当代人类学家对介入问题的反思

解决的范畴,可能将使教育人类学发生一种重大 的文化背景,包括文化差异、文化变迁、文化冲突 转向:从“为己”的教育人类学转向“为他”的教育 与融合、洞察促进生命发展的教育实践活动等,并 人类学。 在此基础上,洞察文化、教有与人的生命发展的内 不过,尽管存在如上立场和取向的差异,仍领 在关联及其连接过程。它涉及的是一个基本而 不能轻易作出具有孰优孰劣甚至等级性质的判 题:什么样的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及其过程最有利 断,采取何种研究立场和取向,是每个研究者自已 于人的生命的成长与发展 的选择。我们倡导某一种取向,并不意味若对其 它欲探究的不是单纯的某一“文化逻辑” 他取向存在价值的否定和排斥,相反,尊重每一种 “教育逻辑”,或“生命成长逻辑”,而是一种关系 研究立场是保持学术活力的基本源泉。 罗辑,即文化与教育之于生命成长的关系罗辑 四、人类需要教育人类学做什么 教育人类学就是为了这一问题及其思考逻辑的提 出和解决而来的,这是只有它才能完成的特殊 这是一个涉及教育人类学使命和责任的原点 使命」 性质的问题。它与前面两大原点问题有颇多共同 在特殊的意义上,人类需要教育人类学面对 之处:教育人举学且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与为谁服 不同地域和所处时代的特殊问题,既致力于寻费 务、满足哪类主体的需要有关 而主体的定位及 地方性教育知识,也努 力回应时代精神和时代需 其需要决定了教有人类学的使命和责任,承担何 要。对当下的中国教有而言,面临者两大急迫的 种使命与责任,又影响到教育人类学存在价值的 现实向题:一是民族关系问题中的文化矛后和文 深度和广度。 化融合,以及文化认同、国家认同问题:二是教育 正如每个人降临在此世都是有使命的 一门 的转型与变革问题,中国教有转型与变革远未完 学科也同样如此。教有人类学的使命可在“普 成,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如何介入教育改革,真实推 遍”和“特殊 两个层面上展开,总体展现出只有 动教有改革,推动教师和学生实现真实的生命成 教育人类学才能做出的学术贡献。 长,或许是其可能承担的责任。 在普遍的意义上,人类需要借助“教育人类 教育人类学履行上述使命的过程,其实就是 学”这门学科解决一个普遍且根本的问题:文化 回应如下问颗的过程:教有人类学可以对什么在 教育和人的三角关系】 它需要研 者通过洞察 所作为?答案无非是:它可以对人的生命发展有 的生命发展状态,来洞察人性、洞察人的生命发展 所作为,能够对所处时代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雷蒙德·吊思(章孝通).人文类型[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 [2】杨小版.有理论工作者的实践立场及其表现0].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4) [3]李政德.论“教育田野“研究的特质一兼论田野工作中人类学立场和散育学立场的差异U].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7.(6) Returning to the Origin:On Ontology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LI Zheng-tao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New Basie Education.East China Nomal Univerity.) [Abstracet]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was formed and developed as the result of the integr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About its origin and ontology,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questions:1 Why do humn being ee i)Who needs 3)What do ma being eed it or o forh hat purpose?Thethre questions are related with each other.Through proposing and solving these questions,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can make contributions to both academic and knowledge systems. [Key words]educational anthropology:origin:ontology (债任编辑娜木罕) 9 9-014 China Academie Jour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http://www.cnki.ne
解决的范畴,可能将使教育人类学发生一种重大 转向: 从“为己”的教育人类学转向“为他”的教育 人类学。 不过,尽管存在如上立场和取向的差异,仍然 不能轻易作出具有孰优孰劣甚至等级性质的判 断,采取何种研究立场和取向,是每个研究者自己 的选择。我们倡导某一种取向,并不意味着对其 他取向存在价值的否定和排斥,相反,尊重每一种 研究立场是保持学术活力的基本源泉。 四、人类需要教育人类学做什么 这是一个涉及教育人类学使命和责任的原点 性质的问题。它与前面两大原点问题有颇多共同 之处: 教育人类学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与为谁服 务、满足哪类主体的需要有关。而主体的定位及 其需要决定了教育人类学的使命和责任,承担何 种使命与责任,又影响到教育人类学存在价值的 深度和广度。 正如每个人降临在此世都是有使命的。一门 学科也同样如此。教育人类学的使命可在“普 遍”和“特殊”两个层面上展开,总体展现出只有 教育人类学才能做出的学术贡献。 在普遍的意义上,人类需要借助“教育人类 学”这门学科解决一个普遍且根本的问题: 文化、 教育和人的三角关系。它需要研究者通过洞察人 的生命发展状态,来洞察人性、洞察人的生命发展 的文化背景,包括文化差异、文化变迁、文化冲突 与融合、洞察促进生命发展的教育实践活动等,并 在此基础上,洞察文化、教育与人的生命发展的内 在关联及其连接过程。它涉及的是一个基本问 题: 什么样的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及其过程最有利 于人的生命的成长与发展? 它欲探究的不是单纯的某一“文化逻辑”、 “教育逻辑”,或“生命成长逻辑”,而是一种关系 逻辑,即文化与教育之于生命成长的关系逻辑。 教育人类学就是为了这一问题及其思考逻辑的提 出和解决而来的,这是只有它才能完成的特殊 使命。 在特殊的意义上,人类需要教育人类学面对 不同地域和所处时代的特殊问题,既致力于寻获 地方性教育知识,也努力回应时代精神和时代需 要。对当下的中国教育而言,面临着两大急迫的 现实问题: 一是民族关系问题中的文化矛盾和文 化融合,以及文化认同、国家认同问题; 二是教育 的转型与变革问题,中国教育转型与变革远未完 成,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如何介入教育改革,真实推 动教育改革,推动教师和学生实现真实的生命成 长,或许是其可能承担的责任。 教育人类学履行上述使命的过程,其实就是 回应如下问题的过程: 教育人类学可以对什么有 所作为? 答案无非是: 它可以对人的生命发展有 所作为,能够对所处时代有所作为。 [参考文献] [1] 雷蒙德·弗思( 费孝通译) . 人文类型[M]. 北京: 华夏出版社,2001: 3. [2] 杨小微. 教育理论工作者的实践立场及其表现[J]. 教育研究与实验,2006,( 4) . [3] 李政涛. 论“教育田野”研究的特质———兼论田野工作中人类学立场和教育学立场的差异[J]. 教育研究与实验, 2007,( 6) . Returning to the Origin: On Ontology of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LI Zheng-tao (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New Basic Educa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was formed and developed as the result of the integration of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About its origin and ontology,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questions: 1) Why do human beings need it? 2) Who needs it? 3) What do human beings need it for or for what purpose? The three questions are related with each other. Through proposing and solving these questions,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can make contributions to both academic and knowledge systems. [Key words]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origin; ontology 〔责任编辑 娜木罕〕 —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