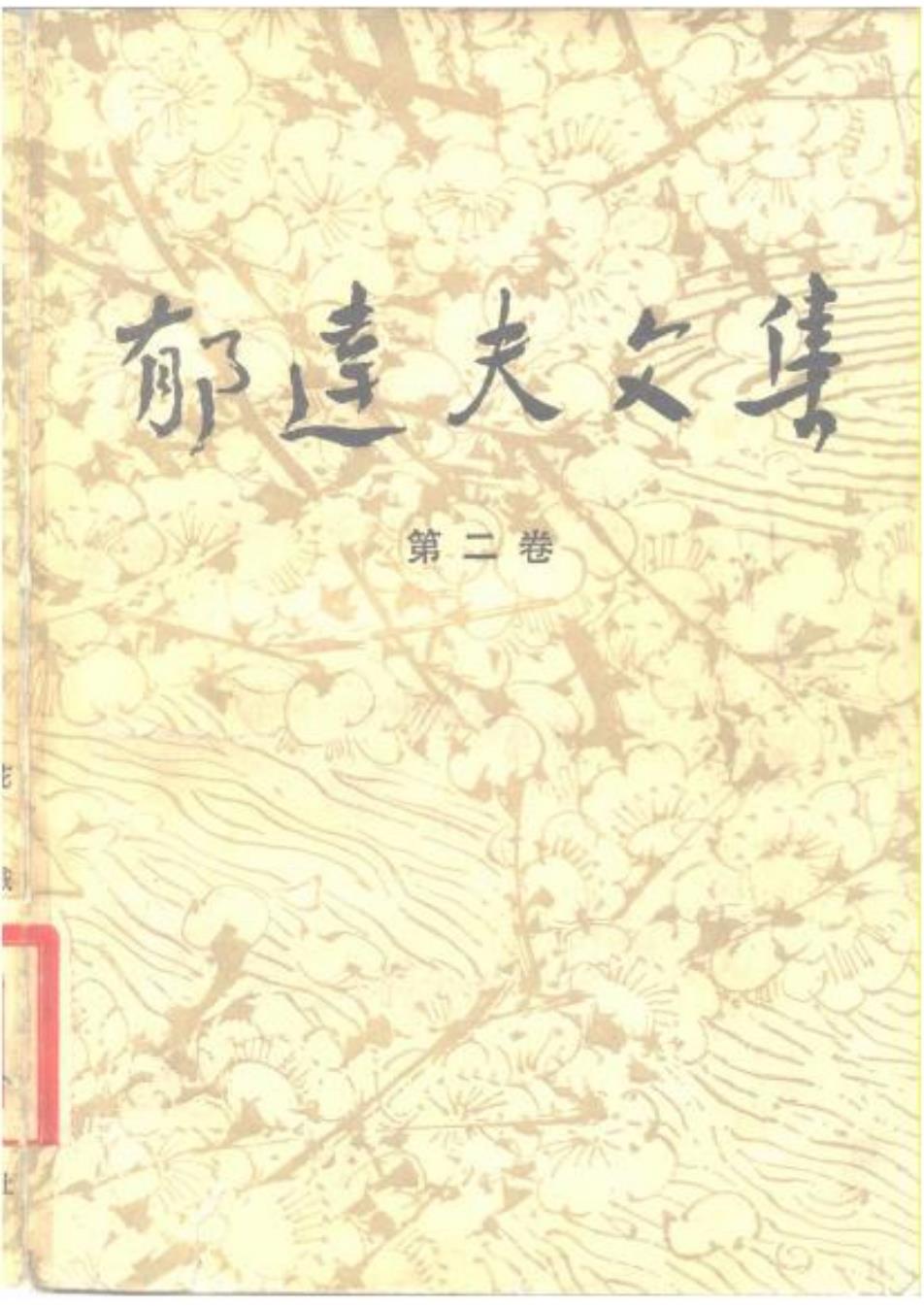
解连夫球 第二卷

迷·羊 、·糖湾夫养 世玉意喜:增江 《迷羊”一九二八年收封面

目 录 迷羊 二诗人 …94 逃走… …114 在寒风里… ……122 纸币的跳跃… ……141 杨梅烧酒… …146 十三夜… …155 屋楼 …170 她是一个弱女子 …210 马缨花开的时候 …301 东梓关… …308 迟桂花…… …318 碧浪湖的秋夜 …351 瓢儿和尚…… …368 迟暮……37门 唯命论者 386 否n1, …394 孤独(独幕剧) 4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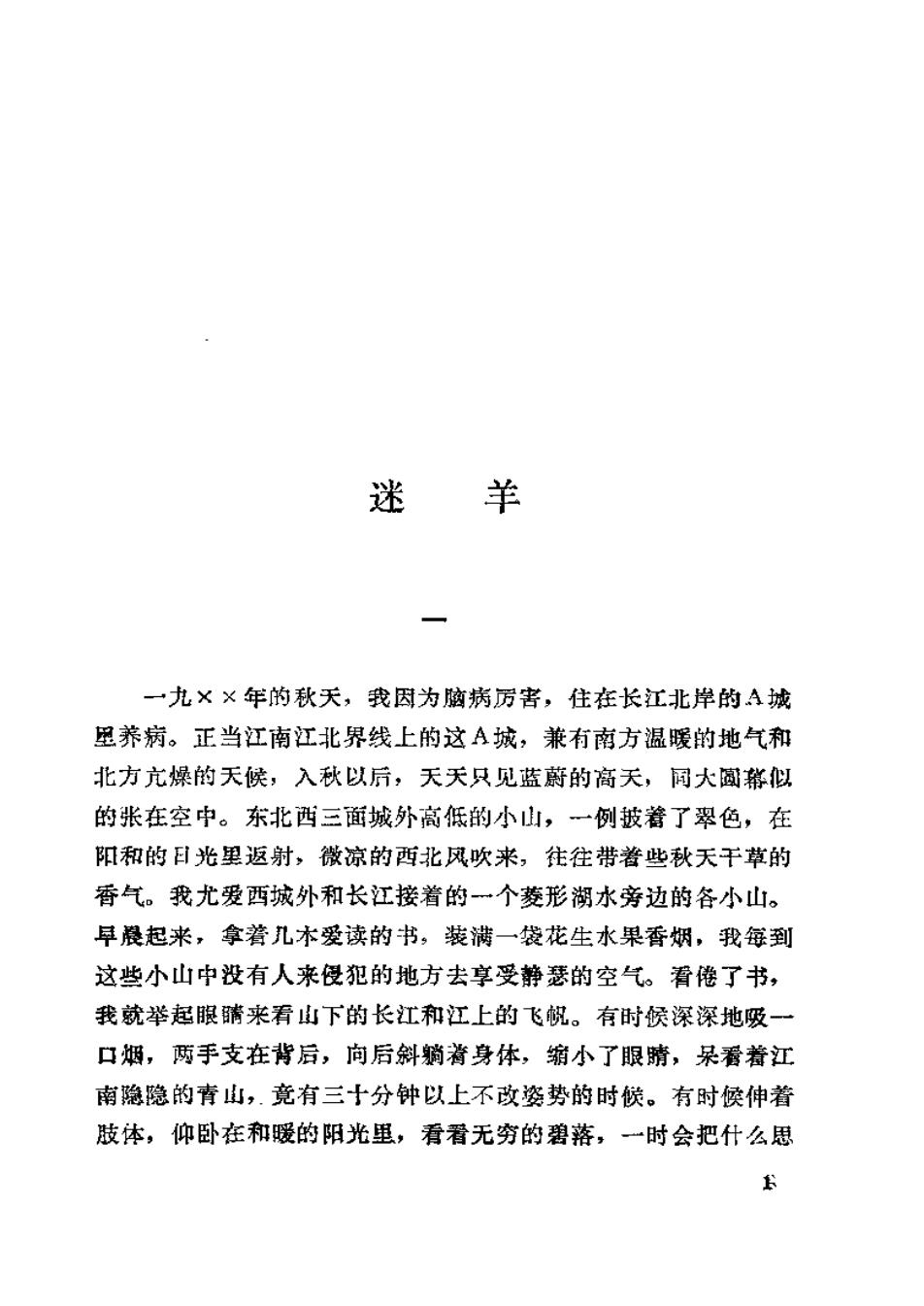
迷 羊 一九××年的秋天,我因为脑病厉苦,住在长江北岸的A城 里养病。正当江南江北界线上的这A城,兼有南方温暖的地气和 北方亢燥的天候,入秋以后,天天只见蓝蔚的高天,同大圆锵似 的张在空中。东北西三面城外高低的小山,一例披着了翠色,在 阳和的目北里返射,微凉的西北风吹来,往往带着些秋天干草的 香气。我尤爱西城外和长江接着的一个菱形湖水旁边的各小山。 卓稳起来,拿着儿木爱读的书。装满一袋龙生水果香烟,我每到 这些小山中没有人来侵犯的地方去享受静瑟的空气。看倦了书, 我就举起眼猜来看山下的长江和江上的飞帆。有时候深深地吸-一 口烟,两手支在背后,向后斜躺着身体,缩小了眼睛,呆看着江 南隐隐的青山,.竞有三十分钟以上不改姿势的时候。有时候伸着 肢体,仰卧在和暖的阳光里,看看无穷的碧落,一时会把什么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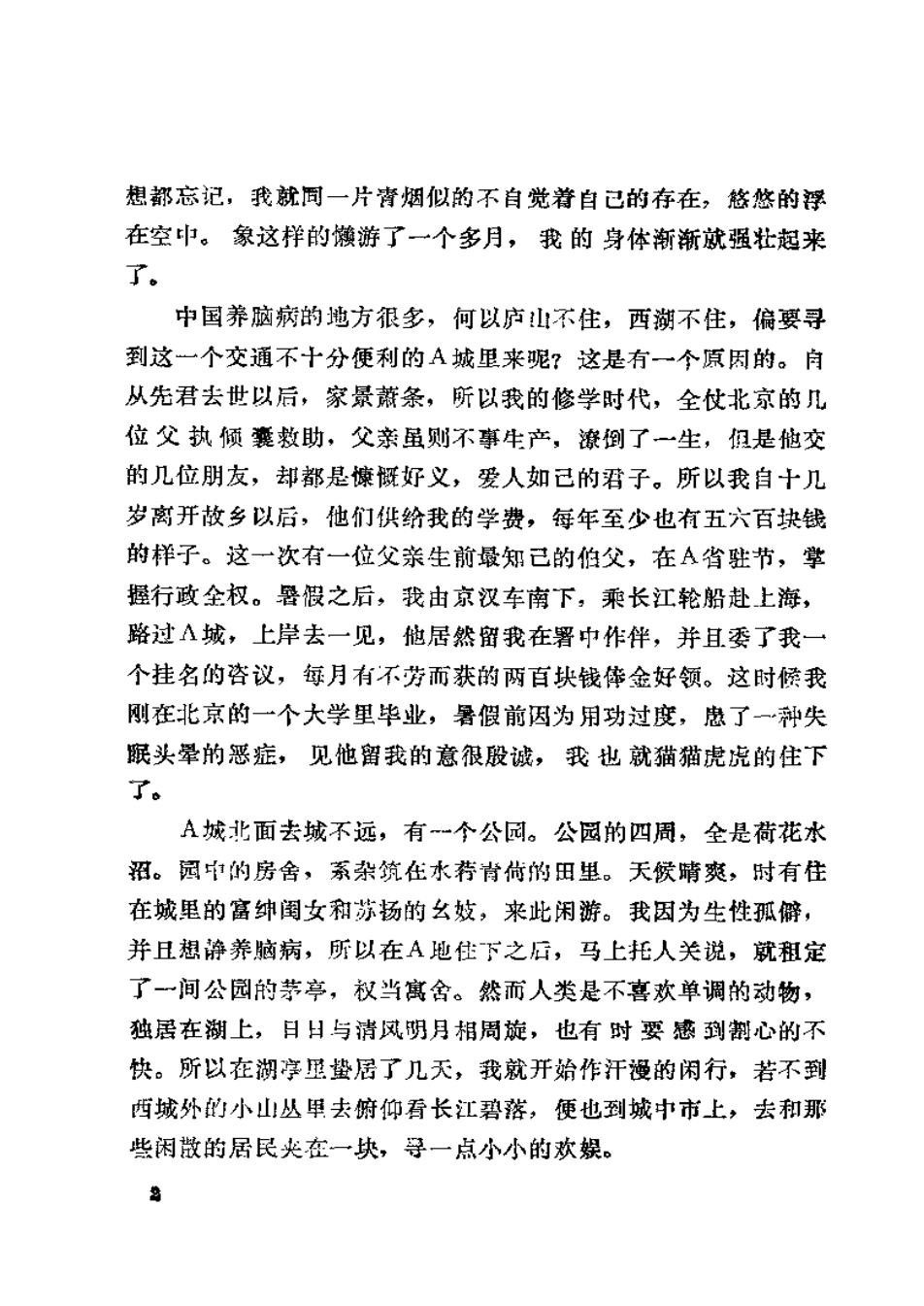
想都忘记,我就同一片青烟似的不自觉着自己的存在,格悠的浮 在空中。象这样的獭游了一个多月,我的身体渐渐就强社起来 了。 中国养脑病的地方很多,何以庐山不住,西湖不住,倫要寻 到这一个交通不十分便利的A城里来呢?这是有一今原因的。自 从先君去世以后,家景萧条,所以我的修学时代,全仗北京的几 位父执倾夔数助,父亲虽则不事生产,潦倒了一生,但是他交 的几位朋友,却都是慷慨好义,爱人如已的君子。所以我自十几 岁离开故乡以后,他们供给我的学费,每年至少也有五六百块钱 的样子。这一次有一位父亲生前最知已的伯父,在A省驻节,掌 趣行政全权。暑假之后,我由京汉车南下,乘长江轮船赴上海, 路过A城,上岸去一见,他居然留我在署中作伴,并且委了我一 个挂名的咨议,每月有不劳而获的两百块钱体金好领。这时使我 刚在北京的一个大学里毕业,暑假前因为用功过度,患了一种失 眠头晕的恶症,见他留我的意很殷减,我也就猫猫虎虎的住下 了。 A城北面去城不远,有个公园。公园的四周,全是荷花水 沼。园中的房舍,系杂筑在水荇青荷的田里。天饺晴爽,时有住 在城里的富绅闺女和苏扬的幺妓,来此闲游。我因为生性孤僻, 并且想静养脑病,所以在A地住下之后,马上托人关说,就粗定 了一间公园的茅亭,权当寓舍。然而人类是不喜欢单调的动物, 独居在湖上,日H与请风明月相周旋,也有时要感到割心的不 快。所以在湖层里蛰居了几天,我就开始作汗漫的闲行,若不到 西城外的小山丛甲去俯仰看长江碧落,便也到城中市上,去和那 些闲散的居民夹在一块,等一点小小的欢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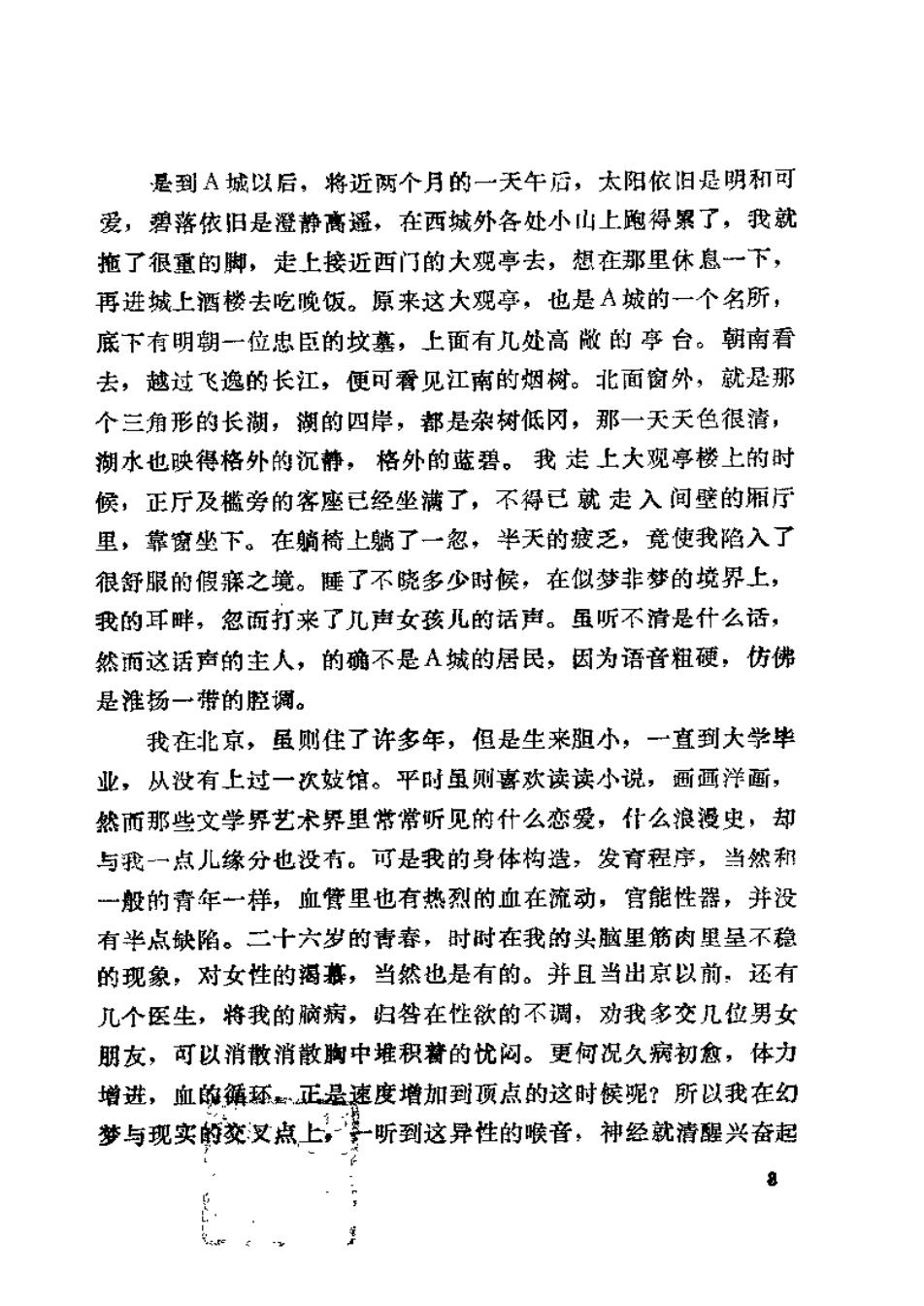
是到A城以后,将近两个月的一天午:,太阳依旧是明和可 爱,碧落依旧是澄静离遥,在西城外各处小山上跑得累了,我就 拖了很重的脚,走上接近西门的大观亭去,想在那里休息一下, 再进城上酒楼去吃晚饭。原来这大观亭,也是A城的一个名所, 底下有明朝一位忠臣的坟墓,上面有儿处高敞的亭台。朝南看 去,越过飞逸的长江,便可香见江南的烟树。北面窗外,就是那 个三角形的长湖,湖的四岸,都是杂树低冈,那一天天色很清, 湖水也映得格外的沉静,格外的蓝碧。我走上大观亭楼上的时 候,正厅及槛旁的客座已经坐满了,不得已就走入间壁的厢厅° 里,靠窗坐下。在躺椅上躺了一忽,半天的疲乏,凳使我陷入了 很舒服的假寐之凳。睡了不晓多少时候,在似梦非梦的境界上, 我的耳畔,忽面打来了儿声女孩儿的话声。虽听不消是什么话, 然而这话声的主人,的确不是A城的居民,因为语音粗硬,仿佛 是淮扬一带的腔调。 我在北京,虽则住了许多年,但是生来胆小,一直到大学毕 业,从没有上过一次效馆。平时虽则喜欢读读小说,画画洋画, 然而那些文学界艺术界里常常听见的什么恋爱,什么浪没史,却 与我一点儿缘分也没有。可是我的身体构造,发育程序,当然和 一般的青年一样,血管里也有热烈的血在流动,宫能性器,并没 有半点缺陷。二十六岁的青春,时时在我的头脑里筋肉里呈不稳 的现象,对女性的海舞,当然也是有的。并且当出京以前,还有 几个医生,将我的脑病,归咎在性欲的不调,劝我多交几位男女 朋友,可以消散消散胸中堆积菁的忧闷。更何祝久病初愈,体力 增进,血的循环正是速度增加到顶点的这时候呢?所以我在幻 梦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听到这异性的喉音,神经就清醒兴奋起 8

来了, 从躺椅上站起,很急速地擦了一擦眼睛,走到隔-一重门的正 厅里的时候,我看见厅前门外回廊的槛上,凭立著几个服色奇异 的年轻的幼妇。 她画朝着槛外,在看扬子江里的船只和江上的斜阳,背形 服饰,一眼看来,都是差不多的。她们大约都只有十七八岁的年 纪,下面着的,是刚在流行的大脚裤,颜色仿佛全是玄色,上面 的衣服,却不一样。第二眼再仔细看时,我才知道她们共有三 人,一个是穿紫色大团花缎的圆角夹衫,一个穿的是深蓝素缎, 还有一个是穿着黑华丝葛的薄棉袄的。中间的那个穿蓝素缎的, 偶然间把头回望了一望,我看出了一个小小椭圆形的嫩脸,和她 的同伴说笑后尚未收敛起的笑容。她很不经意地把头朝回去了, 但我却在脑门上受了一次大大的棒击。这清冷的A城内,拢总不 过于数家人家,除了几个妓馆乳的放荡的么妓面外,从未见过有 这样豁达的女子,这样可爱的少女,套无拘束地,三五成群,当 这个晴和的个后,米这个不人流行的名所,赏玩风光的。我一时 风魔了理性,不知不觉,竞在她们的背后,正厅的中间,呆立了 几分钟。 茶博上打了一块手功过来,问我要不要吃点点心,同时她们 也朝转来向我有了,我才张红了脸,慌慌张张的对茶博士说, “要一点!要一点!有什么好吃的?”大约因为我的样子太仓皇了 吧?茶律士:和她们都笑了起来。我更急得没法,便回身走回厢厅 的座里去。临走时向正厅上各座位匆匆的管了一眼,我只见满地 的花生瓜子的残皮,和几张桌上空空的杂乱摆着的几只茶壶茶 碗,这时候许多游客都已经散了。“大约在这一座亭台里说连未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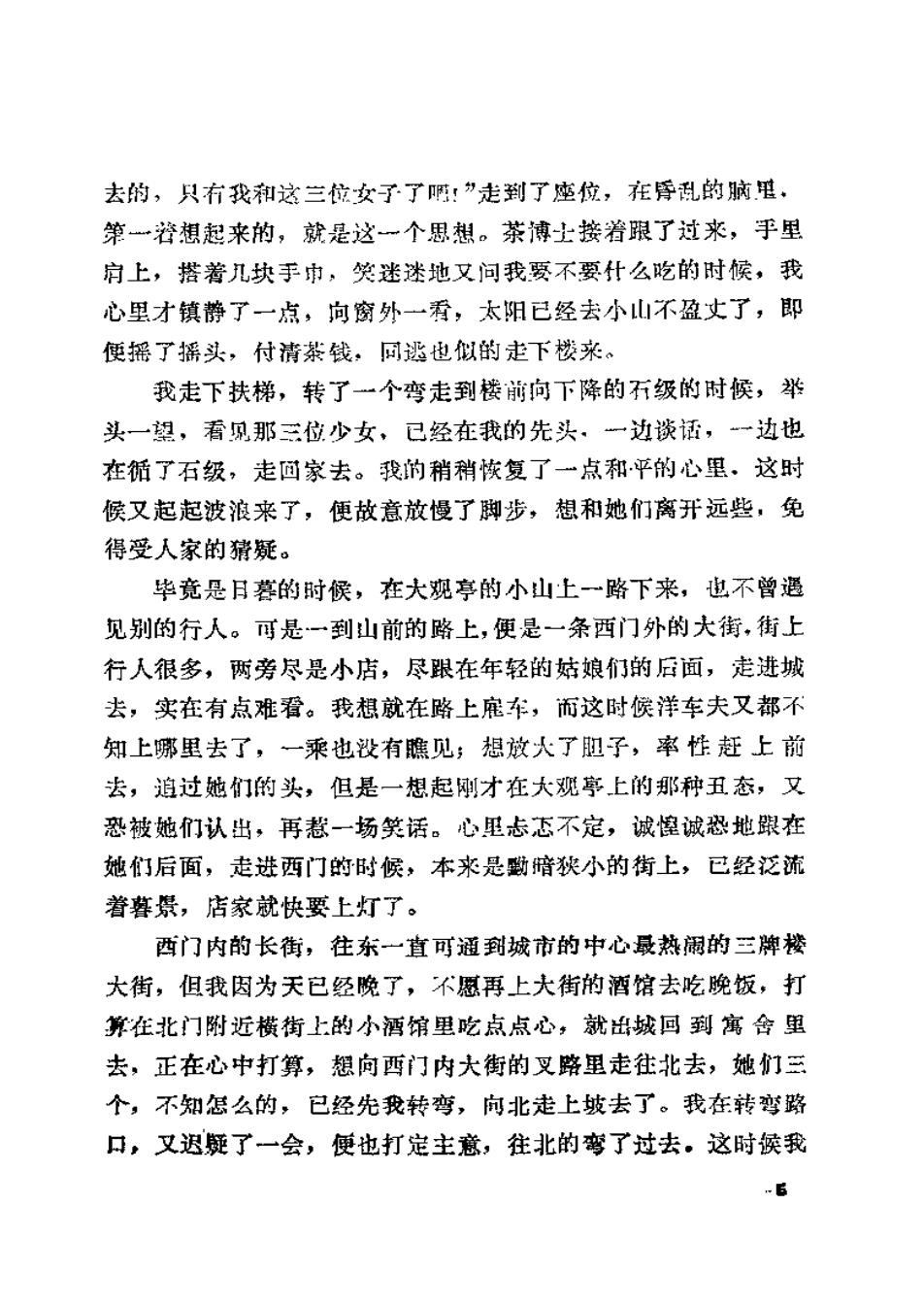
去的,只有我和这三位女了了!”走到了座位,在季乱的脑里, 第…着想起来的,就是这一个思想。茶博上接着跟了过来,手里 肩上,搭着九块手中,笑迷迷地又问我要不要什么吃的时候,我 心里才镇静了一点,向窗外一看,太阳已经去小山不盈丈了,即 便摇了摇头,付清茶钱,阿可逃也似的走下楼来。 我走下扶梯,转了一个弯走到楼前向下降的行级的时候,举 头一望,看见那三位少女,已经在我的先头、一边谈话,“一边也 在循了石级,走回家去。我的稍稍恢复了一点和平的心里、这时 候又起起波浪来了,便故意放慢了脚步,想和她们离升远些,免 得受人家的猜凝。 毕竞是月暮的时候,在大观亭的小山上一路下来,电不曾遇 见别的行人。可是一到山前的路上,便是一条西门外的大街,街上 行人很多,两旁尽是小店,尽跟在年轻的姑娘们的后面,走进城 去,实在有点难看。我想就在路上雇车,而这时候洋车夫又都不 知上哪里去了,一乘也没有瞧儿;想放人了胆子,率性赶上前 去,追过她们的头,但是一想起种才在大观亭上的那种丑态,又 恐被她们认出,再惹一场笑话。心里忐忑不定,诚憧诚恐地跟在 她们后面,走进西门的时候,本来是勤暗狭小的街上,已经泛流 着暮景,店家就快要上灯了。 西门内的长街,往东一直可通到城市的中心最热闹的三牌楼 大街,但我因为天已经晚了,不恩再上夫街的酒馆去吃晚饭,打 算在北门附近横街上的小酒馆里吃点点心,就出城回到寓舍里 去,正在心中打算,想向西门内夫街的叉路里走往北去,她们三 个,不知怎么的,已经先我转弯,向北走上坡去了。我在转弯路 口,又迟疑了一会,便也打定主意,往北的弯了过去。这时侯我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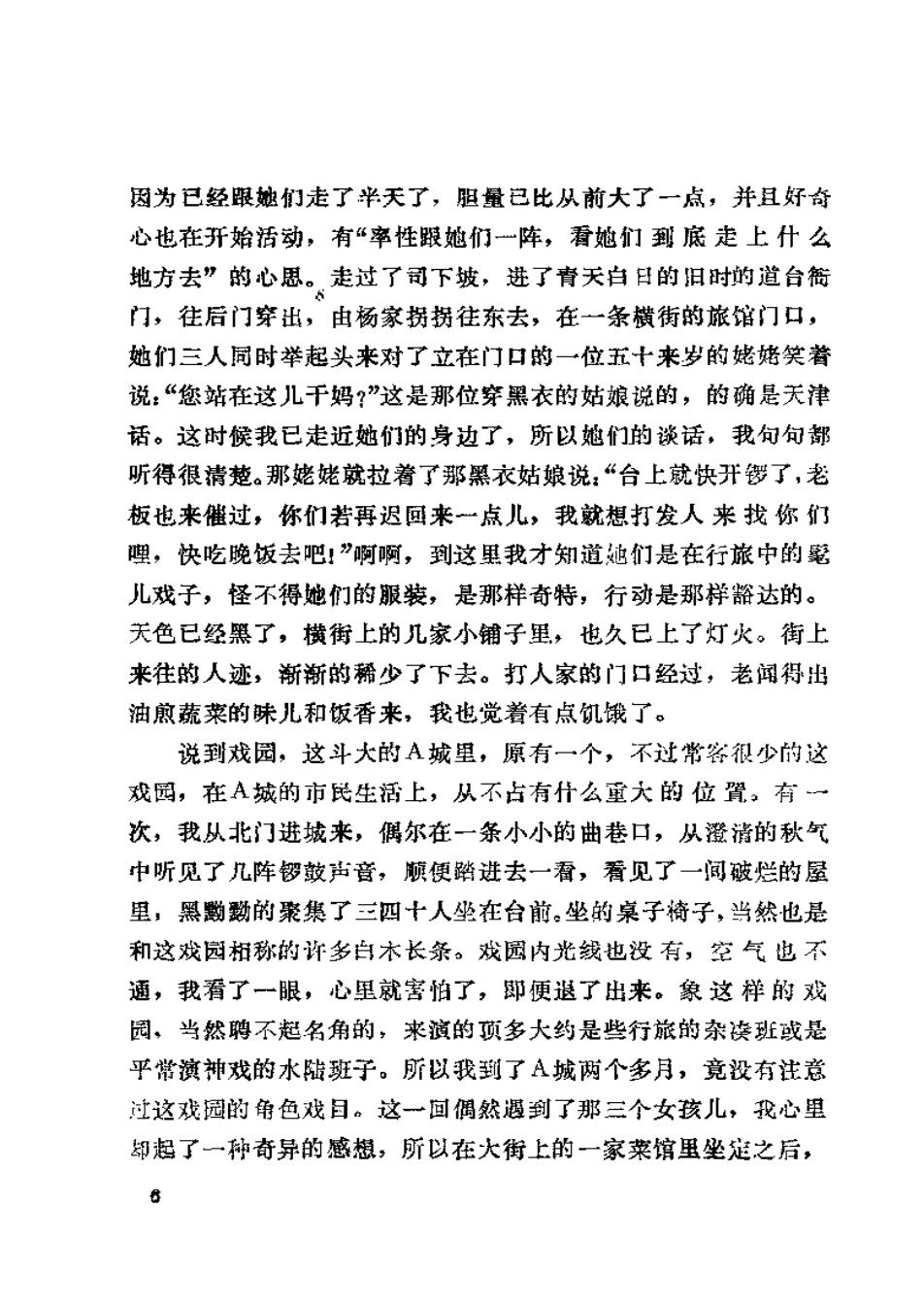
因为已经跟越们走了半天了,胆量已比从前大了一点,并且好奇 心也在开始活动,有“率性跟她们一阵,看她们到底走上什么 地方去”的心思。走过了司下坡,进了青天白甘的旧时的道台衙 门,往后门穿出,由杨家拐拐往东去,在一条横街的旅馆门口, 她们三人同时举起头来对了立在门口的一位五十来岁的姥焰笑着 说:“您站在这儿干妈?”这是那位穿黑衣的姑娘说的,的确是天津 话。这时候我已走近她们的身边了,所以她们的谈话,我句句都 听得很清楚。那姥姥就拉着了那黑衣姑娘说:“台上就快开锣了,老 板也来催过,你们若再迟回来一点儿,我就想打发人来找你们 哩,快吃晚饭去吧!”啊啊,到这里我才知道她们是在行旅中的笔 儿戏子,柽不得她们的服装,是那样奇特,行动是那样豁达的。 关色已经黑了,横街上的儿家小铺子里,也久已上了灯火。街上 来往的人迹,渐渐的稀少了下去。打人家的门口经过,老闻得出 油煎蔬菜的味儿和饭香来,我也觉着有点饥饿了。 说到龙园,这斗大的A城里,原有一个,不过常客很少的这 戏园,在A城的市民生活上,从不占有什么重大的位置,有一 次,我从北门进城来,偶尔在一条小小的曲巷口,从澄清的秋气 中听见了儿阵锣鼓声音,颜便踏进去一看,看见了一间破烂的屋 里,黑勒勤的聚集了三四十人坐在台前。坐的桌子椅子,当然也是 和这戏园相称的许多白木长条。戏园内光线也没有,空气也不 通,我看了一眼,心里就害怕了,即便退了出来。象这祥的戏 园,当然聘不超名角的,来演的顶多大约是些行旅的杂楼班或是 平常演神戏的水陆班子。所以我到了A城两个多月,竟没有注意 过这戏园的角色戏目。这一回偶然遇到了那三个女孩儿,我心里 知起了一种奇异的感想,所以在大街上的一家菜馆里坐定之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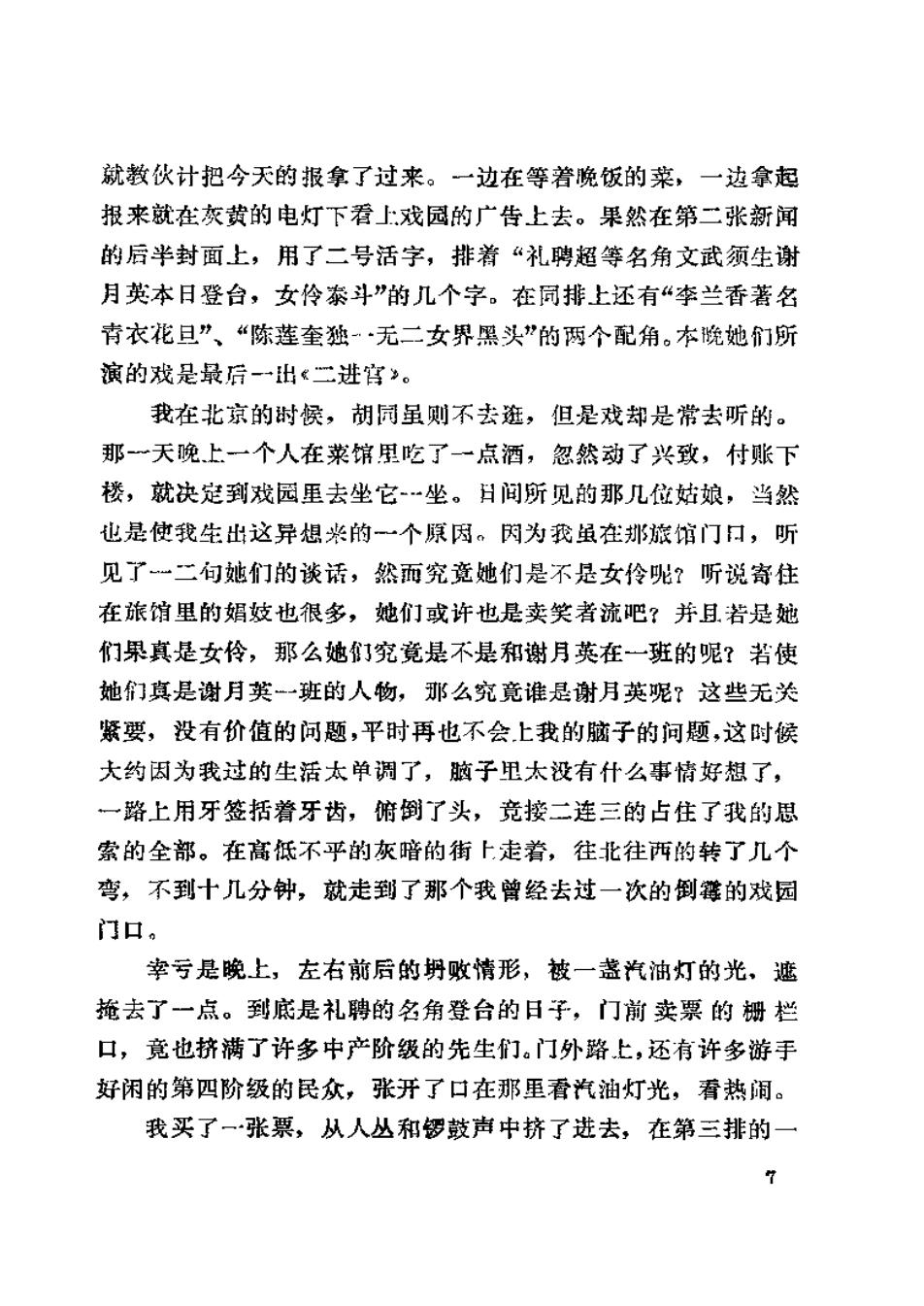
就教伙计把今天的报拿了过来。一边在等着晚饭的菜,一边拿起 报来就在灰黄的电灯下看上戏园的广告上去。果然在第二张新闻 的后半封面上,用了二号活字,排着“礼聘超等名角文武须生谢 月英本日登台,女伶泰斗”的几个字。在同排上还有“李兰香著名 青衣花旦”、“陈莲奎独·无二女界黑头”的两个配角。本晚她们所 演的戏是最后-一出《二进宫。 我在北京的时候,胡同虽则不去逛,但是戏却是常去听的。 那一天晚上一个人在莱馆里吃了一点酒,忽然动了兴致,付账下 楼,就决定到戏园里去坐它一坐。日间所见的那几位姑娘,当然 也是使我生出这异想柴的一个原因。闪为我虽在排旅馆门口,听 见了一二句她们的谈话,然面究竟她们是不是女伶呢?听说寄住 在旅馆里的娟妓也很多,她J或许也是卖笑者流吧?并且若是她 们果真是女怜,那么她钉究竞是不是和谢月英在一班的呢?若使 她们真是谢月英“一班的人物,那么究竞谁是谢月英呢?这些无关 紧要,没有价值的问题,平时再也不会上我的脑子的问题,这时候 大约因为我过的生活太单调了,脑子里太没有什么事情好想了, 一路上用牙签括着牙齿,俯倒了头,竞接二连三的占住了我的思 索的全部。在高低不乎的灰暗的街上走着,往北往西的转了几个 弯,不到十几分钟,就走到了那个我曾经去过一次的倒篝的戏园 门口。 率亏是晚上,左右前后的坍败情形,被一盏汽油灯的光、遮 掩去了一点。到底是礼聘的名角登台的日子,门前卖票的栅栏 口,竟也挤满了许多中产阶缀的先生们。门外路上,还有许多游手 好闲的第四阶级的民众,张开了口在那里看汽油灯光,看热闹。 我买了一·张票,从人丛和锣鼓声中挤了进去,在第三排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