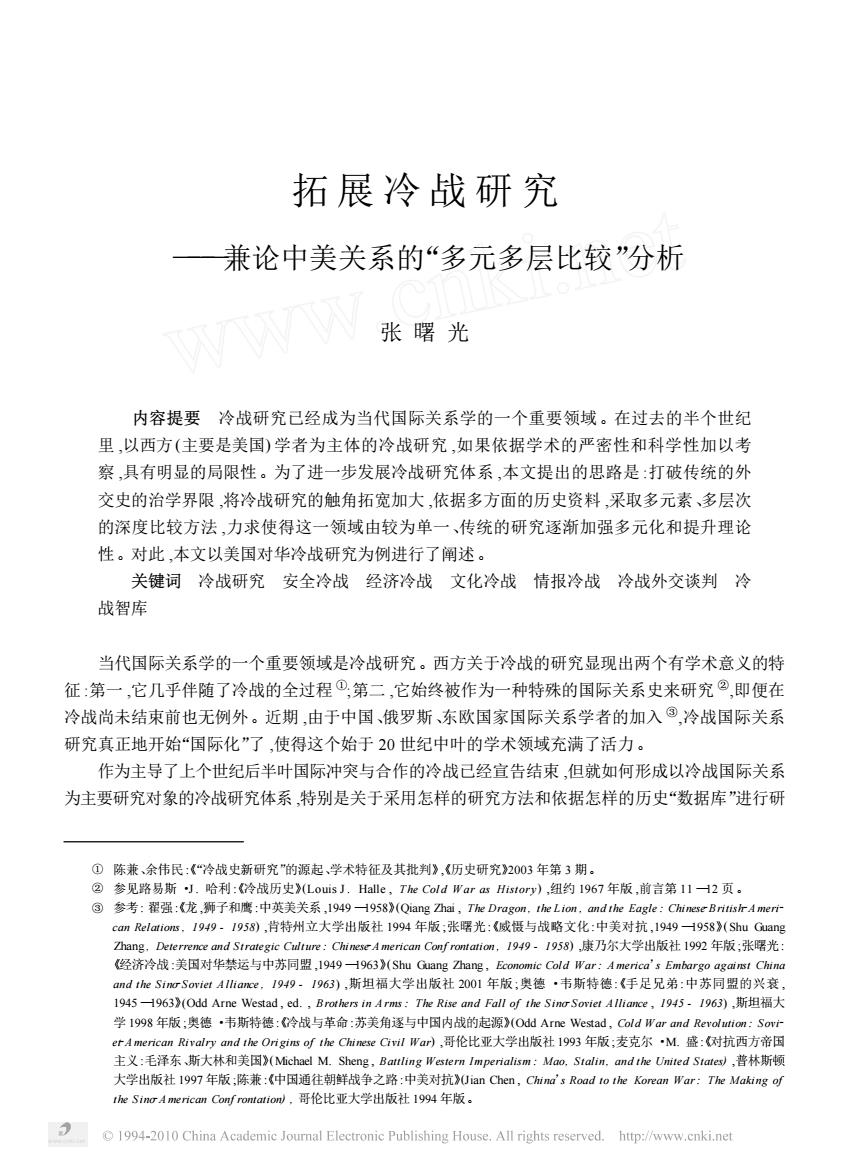
拓展冷战研究 兼论中美关系的“多元多层比较”分析 张曙光 内容提要冷战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里,以西方(主要是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如果依据学术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加以考 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为了进一步发展冷战研究体系,本文提出的思路是:打破传统的外 交史的治学界限,将冷战研究的触角拓宽加大,依据多方面的历史资料,采取多元素、多层次 的深度比较方法,力求使得这一领域由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逐渐加强多元化和提升理论 性。对此,本文以美国对华冷战研究为例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冷战研究安全冷战经济冷战文化冷战情报冷战冷战外交谈判冷 战智库 当代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冷战研究。西方关于冷战的研究显现出两个有学术意义的特 征:第一,它几乎伴随了冷战的全过程①,第二,它始终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史来研究②,即便在 冷战尚未结束前也无例外。近期,由于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的加入®,冷战国际关系 研究真正地开始“国际化”了,使得这个始于20世纪中叶的学术领域充满了活力。 作为主导了上个世纪后半叶国际冲突与合作的冷战己经宣告结束,但就如何形成以冷战国际关系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冷战研究体系特别是关于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和依据怎样的历史“数据库”进行研 ①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年第3期。 ②参见路易斯J.哈利:《冷战历史》(LouisJ.Hale,The Cold War as History),纽约1967年版,前言第11H2页。 ③参考:翟强:《龙,狮子和度:中英美关系,l949H9s8》(Qiang Zhai,The Dragon,the Lion,and the Eagle:Chinese Britis Ameri- can Relations,.1949-1958),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曙光:《威慑与战略文化:中美对抗,1949一958》(Shu Guang Zhang,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Chinese A merican Conf rontation,1949-1958),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张曙光: 《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禁运与中苏同盟,l949H963》(Shu Guang Zhang,Economic Cold War:America's Embargo agairs1 China and the Sino Soviet A1 liance,1949-I963),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奥德·韦斯特德:《手足兄弟:中苏同盟的兴衰, 1945H963》(Odd Arne Westad,ed.,Brothers in Arm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 Soviet A1 liance,1945-1963),斯坦福大 学1998年版;奥德,韦斯特德:《怜战与革命:苏美角逐与中国内战的起源》(Odd Arne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r er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麦克尔M.盛:《对抗西方帝国 主义:毛泽东斯大林和美因》(Michael M.Sheng,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普林斯顿 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陈兼:《中国通往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0 ian Chen,China's Road1 o the Korean War:The Making of 1 e Sino A merican Conf rontatio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拓 展 冷 战 研 究 ———兼论中美关系的“多元多层比较”分析 张 曙 光 内容提要 冷战研究已经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 里 ,以西方(主要是美国) 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 ,如果依据学术的严密性和科学性加以考 察 ,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为了进一步发展冷战研究体系 ,本文提出的思路是 :打破传统的外 交史的治学界限 ,将冷战研究的触角拓宽加大 ,依据多方面的历史资料 ,采取多元素、多层次 的深度比较方法 ,力求使得这一领域由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逐渐加强多元化和提升理论 性。对此 ,本文以美国对华冷战研究为例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 冷战研究 安全冷战 经济冷战 文化冷战 情报冷战 冷战外交谈判 冷 战智库 当代国际关系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冷战研究。西方关于冷战的研究显现出两个有学术意义的特 征 :第一 ,它几乎伴随了冷战的全过程 ①;第二 ,它始终被作为一种特殊的国际关系史来研究 ②,即便在 冷战尚未结束前也无例外。近期 ,由于中国、俄罗斯、东欧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的加入 ③,冷战国际关系 研究真正地开始“国际化”了 ,使得这个始于 20 世纪中叶的学术领域充满了活力。 作为主导了上个世纪后半叶国际冲突与合作的冷战已经宣告结束 ,但就如何形成以冷战国际关系 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冷战研究体系 ,特别是关于采用怎样的研究方法和依据怎样的历史“数据库”进行研 ① ② ③ 陈兼、余伟民《: “冷战史新研究”的源起、学术特征及其批判》《, 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 期。 参见路易斯 ·J. 哈利《: 冷战历史》(Louis J. Halle , The Col d W ar as History ) ,纽约 1967 年版 ,前言第 11 —12 页。 参考: 翟强《: 龙 ,狮子和鹰:中英美关系 ,1949 —1958》(Qiang Zhai , The Dragon , the Lion , and the Eagle : Chinese2B ritish2A meri2 can Relations , 1949 - 1958) ,肯特州立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张曙光《: 威慑与战略文化:中美对抗 ,1949 —1958》(Shu Guang Zhang , Deterrence and Strategic Culture : Chinese2A merican Conf rontation , 1949 - 1958) ,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张曙光: 《经济冷战:美国对华禁运与中苏同盟 ,1949 —1963》(Shu Guang Zhang , Economic Col d War: A 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2Soviet Alliance , 1949 - 1963)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奥德 ·韦斯特德《: 手足兄弟:中苏同盟的兴衰 , 1945 —1963》(Odd Arne Westad , ed. , B rothers in A rms :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2Soviet Alliance , 1945 - 1963) ,斯坦福大 学 1998 年版;奥德 ·韦斯特德《: 冷战与革命:苏美角逐与中国内战的起源》(Odd Arne Westad , Col d War and Revolution : Sovi2 et2A 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 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麦克尔 ·M. 盛《: 对抗西方帝国 主义:毛泽东、斯大林和美国》(Michael M. Sheng ,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普林斯顿 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陈兼《: 中国通往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Jian Chen ,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2A merican Conf rontation) ,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拓展冷战研究 59 究,国内外学者们仍未形成共识。一个为发展冷战研究体系而值得尝试的方法是:打破传统的外交史的 治学界限将冷战研究的触角拓宽加大,依据多方面的历史资料,采取多层次、国际性和跨文化的深度比 较方法,力求使得这一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领域逐渐转向多元化与跨学科,并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①。 一、传统冷战研究的局限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以西方,主要是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国际关系研究,如果依据学术的严 密性和科学性加以考察,具有明显的理论与方法上的局限性。 首先,他(她)们的分析或多或少均具有时代的政治化倾向。冷战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1946年即 以美苏各自领衔的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的对抗展开。此后不久,以美国为 代表的西方学者便开始研究冷战的起源。关于“起源”的研究和争论主导了冷战研究的30年,其间出 现了三个主要学派,即:“传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部分地由于要在政治上支持美国坚持冷 战的战略,传统派宣称:苏联应该对冷战的爆发与延长负责,而美国只是为了对战后国际体系“负责 任"”而不得已应战。根据他(她)们的研究,苏联由于其传统“不安全”意识的主导、“集权”制度的制约、 “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领导人“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等“非理性”因素,在对外政策中长期 推行“霸权”与“扩张”,因而造成对美国与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安全的威胁,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国家 利益,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得已以“非战争”的方式对抗苏联②。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 中,随着冷战的不断扩大与深入,特别是由于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而引发国内反战、反权势、反 传统文化的社会运动,传统派关于美国介入冷战的观点受到质疑,进而产生了冷战研究的“修正派”。 一方面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另一方面出于美国人对“阴谋”的好奇,修正派认为:美国的“产业和 金融寡头”是冷战出现的罪魁祸首。他(她)们的研究指出,美国政府领导层出于满足国内“垄断寡头” 的经济利益需要,利用美国二战后所拥有的特殊的国际政治地位,企图构建“世界经济霸权秩序”,推 行“开放式的帝国主义”的政策。美国的冷战政策与举措,如援助土耳其、希腊“反共”的杜鲁门主义、 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加强西半球政治稳定的第四点计划和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无一例外被认 为是经济驱动的结果③。形成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后修正派”也未能逃脱美国政 治回归现实、回归传统的制约。基于美国首批解密的冷战初期外交、军事和国家安全档案与 ①美国国家级“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为了推动对“冷战国际关系史”的研究,于1995年成立了“冷战国 际关系史研究项目”。美因的哈佛大学、俄亥俄大学以及英国的伦敦大学也分别成立了“冷战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机构。 ②参见阿瑟·施莱辛格:《冷战的起源》(Arthur Schlesinger,Jr.,“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外交》(Foreign Affairs) 第46卷,1967年;乔治,F.凯南:《美国外交:1900H950》(George F.Kennan,American Diplomacy:1900-1950),芝加 哥大学出版社1951年版;威廉·H.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因:合作与冲突,1941H946》(William H.McNeill,A meri- ca,Britain and Russia: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I941-I946),牛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③参看:威廉·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刷》(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纽约19s8年 版:沃尔特,拉夫伯:《新帝国》(Walter LaFeber,The New Empire),康乃尔大学出版社I963年版;沃尔特·拉夫伯:《美因, 俄国和冷战,l945-1996》,(Walter LaFeber,A 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1945-1996),纽约1996年版;加布里 埃尔·科尔科:《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Gabriel Kolko,The Root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波士顿1969年版;加布里 埃尔·科尔科和乔伊斯·科尔科:《权力的限度》(Gabriel Kolko and Joyce Kolko,The Limits of Power),纽约l972年版;劳 埃德·加德纳:《幻觉的建构者》(Lloyd Gardner,Architects of Illusion),芝加哥1970年版,理查德·巴内特:《战争的根源》 (Richard Barnet,Roots of War),纽约1972年版。 1994-2010 China Academie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究 ,国内外学者们仍未形成共识。一个为发展冷战研究体系而值得尝试的方法是 :打破传统的外交史的 治学界限 ,将冷战研究的触角拓宽加大 ,依据多方面的历史资料 ,采取多层次、国际性和跨文化的深度比 较方法 ,力求使得这一较为单一、传统的研究领域逐渐转向多元化与跨学科 ,并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 ①。 一、传统冷战研究的局限性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以西方 ,主要是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国际关系研究 ,如果依据学术的严 密性和科学性加以考察 ,具有明显的理论与方法上的局限性。 首先 ,他(她) 们的分析或多或少均具有时代的政治化倾向。冷战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的 1946 年即 以美苏各自领衔的两大阵营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诸方面的对抗展开。此后不久 ,以美国为 代表的西方学者便开始研究冷战的起源。关于“起源”的研究和争论主导了冷战研究的 30 年 ,其间出 现了三个主要学派 ,即“: 传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部分地由于要在政治上支持美国坚持冷 战的战略 ,传统派宣称 :苏联应该对冷战的爆发与延长负责 ,而美国只是为了对战后国际体系“负责 任”而不得已应战。根据他(她) 们的研究 ,苏联由于其传统“不安全”意识的主导“、集权”制度的制约、 “国际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驱动、领导人“机会主义”倾向的影响等“非理性”因素 ,在对外政策中长期 推行“霸权”与“扩张”,因而造成对美国与所有“非共产主义”国家安全的威胁 ,美国为了维护自身国家 利益 ,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不得已以“非战争”的方式对抗苏联 ②。到了上个世纪 60 年代 中 ,随着冷战的不断扩大与深入 ,特别是由于美国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而引发国内反战、反权势、反 传统文化的社会运动 ,传统派关于美国介入冷战的观点受到质疑 ,进而产生了冷战研究的“修正派”。 一方面受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响 ,另一方面出于美国人对“阴谋”的好奇 ,修正派认为 :美国的“产业和 金融寡头”是冷战出现的罪魁祸首。他(她) 们的研究指出 ,美国政府领导层出于满足国内“垄断寡头” 的经济利益需要 ,利用美国二战后所拥有的特殊的国际政治地位 ,企图构建“世界经济霸权秩序”,推 行“开放式的帝国主义”的政策。美国的冷战政策与举措 ,如援助土耳其、希腊“反共”的杜鲁门主义、 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加强西半球政治稳定的第四点计划和大西洋公约组织等 ,无一例外被认 为是经济驱动的结果 ③。形成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的“后修正派”也未能逃脱美国政 治 ———回归现实、回归传统 ———的制约。基于美国首批解密的冷战初期外交、军事和国家安全档案与 拓展冷战研究 59 ① ② ③ 美国国家级“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为了推动对“冷战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于 1995 年成立了“冷战国 际关系史研究项目”。美国的哈佛大学、俄亥俄大学、以及英国的伦敦大学也分别成立了“冷战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机构。 参见阿瑟 ·施莱辛格《: 冷战的起源》(Art hur Schlesinger , Jr. ,“The Origins of t he Cold War”) 《, 外交》( Forei gn A f f airs) 第 46 卷 ,1967 年 ;乔治 ·F. 凯南《: 美国外交 :1900 —1950》( George F. Kennan , A merican Di plomacy : 1900 - 1950) ,芝加 哥大学出版社 1951 年版 ;威廉 ·H. 麦克尼尔《: 美国、英国和俄国 :合作与冲突 ,1941 —1946》(William H. McNeill , A meri2 ca , B ritain and Russia :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 lict , 1941 - 1946)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参看 :威廉 ·威廉斯《: 美国外交的悲剧》(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 The Tragedy of A merican Di plomacy ) ,纽约 1958 年 版;沃尔特 ·拉夫伯《: 新帝国》(Walter LaFeber , The New Em pire) ,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63 年版 ;沃尔特 ·拉夫伯《: 美国 , 俄国和冷战 ,1945 - 1996》,(Walter LaFeber , A merica , Russia , and the Col d W ar , 1945 - 1996) ,纽约 1996 年版 ;加布里 埃尔 ·科尔科《: 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源》( Gabriel Kolko , The Roots of A merican Forei gn Policy ) ,波士顿 1969 年版 ;加布里 埃尔 ·科尔科和乔伊斯 ·科尔科《: 权力的限度》( Gabriel Kolko and Joyce Kolko , The L imits of Power) ,纽约 1972 年版 ;劳 埃德 ·加德纳《: 幻觉的建构者》(Lloyd Gardner , A rchitects of Illusion) ,芝加哥 1970 年版 ; 理查德 ·巴内特《: 战争的根源》 (Richard Barnet , Roots of W ar) ,纽约 1972 年版

60 世界历史 2007年第3期 文献①,后修正派强调战后国际政治结构“不平衡”是冷战爆发并延续的“病根”,并指出,美苏两国决 策者均应对冷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同于修正派的“单一元素”论,后修正派从华盛顿 战略思考的错位、国内政治对理性决策的制约、官僚机制的惰性和狭隘、决策者的个人局限性、甚至情 报的虚假和不确定性等方面,论证了美国政府的冷战战略思考和实施的非理性②。 其次,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显现出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无疑,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 冷战对外政策应该是冷战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然而,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对抗或合作一关系 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基点。如果一味地强调美国对外行为的“主导性”不仅与史实不符,也无 益于冷战研究的学术体系化。例如,上个世纪70年代后,冷战学者受到“区域研究”的启发,开始依据 美国公布的外交档案研究美国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政策,推动了冷战研究的学术化。然而,随 之产生却是以“美国针对(U.S.-Toward)”为鲜明特征的一批成果③。尽管对美国的政策褒贬不一, 但无一例外均不考虑政策对象国(无论是盟国或友邦,还是对手国)的政策思考与行为对美国政策的 影响,尽管有研究表明这种影响甚至“操纵(Manipulate)”了某个时期美国针对某个事件的政策。结 果,“美国中心”倾向严重制约了冷战研究朝着客观与科学的方向发展,由于不重视甚至忽略掌握别国 语言、利用别国资料、了解别国文化的重要性,以致“区域研究”最终走向衰败。值得庆幸的是,冷战于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结束后,原“共产主义阵营”学者的加盟和来自“对方”的档案文献的有限公开©使 得对冷战的研究日趋国际化:这些“国际型”的学者能够熟练使用“对方国”语言,有幸接触“对方国”刚 刚解密的档案和文献,并能够将冷战的经历放在一个互动的环境中描述与分析⑤。 再者,由美国外交史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表现出方法—历史描述和解读的单一性。无 疑,史学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最大可能地占有和利用与课题相关的第一手或第二手的历史资料,冷 战外交史研究也不例外,然而,由于大多数美国与西方冷战学者对其他学术领域的理论知之甚少甚至 不屑一顾,以致目前的主流成果仍表现出明显的重实证、轻理论以及重描述、轻分析的研究倾向。其 结果是:冷战的“叙述”完全受制于外交档案的公布周期和更新程度(大致按美国联邦档案30年后解 密的周期),大都处于“不断修正”、缓慢推进的状态:冷战研究议题和议程的设定基本与国际关系和国 ①在修正派的政治压力下,美因开始有选择地公开档案,当时最具政治影响的是“五角大楼文献”(The Pentagon Papers)。 ②参见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美国和冷战的起源,l941H947》(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1 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2年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俄罗斯、苏联和美国》0 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United States)),纽约1978年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遇制h战略》(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长期的和平》0 ohn Lewis Gad dis,The Long Peace),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约翰·路易斯·加迪斯:《我们现在明白了:冷战史再思考》(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梅尔文·莱弗勒:《权力的优势》(Me- yn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 ③参见盖尔·伦德斯坦德:《美因对东欧不作为政策,l943H947》(Geir Lundestad,The American Nor Policy Towards Eastern E©e,1943-1947),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罗伯特·麦克马洪:《殖民主义与冷战: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独立,1945一 1949)(Robert McMahon,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1945 -I949),康乃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罗伯特·麦克马洪:《边缘国家的冷战: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Robert MeMahon,The Cold War on the Periphery:The United States,India and Pakista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④为了推动苏联和东欧国家涉及冷战的档案文献的解密,位于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立 了“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项目”,并不断地公布最新解密的档案与文献,www,cwihp.si.edu。 ⑤如:奥德,韦斯特德(Odd Arne Westad)、卡特因,韦瑟比(Katryn Weathersby)、大卫·沃尔夫(David Wolf)、弗拉迪斯拉夫 ·朱布克(Vladislav Zubok)、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伊利亚·盖杜克(ya Gaiduk)、克里斯琴·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陈兼(Jian Chen)、翟强(Qiang Zhai)、张屠光(Shu Guang Zhang)等。 1994-2010 China Academie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文献 ①,后修正派强调战后国际政治结构“不平衡”是冷战爆发并延续的“病根”,并指出 ,美苏两国决 策者均应对冷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同于修正派的“单一元素”论 ,后修正派从华盛顿 战略思考的错位、国内政治对理性决策的制约、官僚机制的惰性和狭隘、决策者的个人局限性、甚至情 报的虚假和不确定性等方面 ,论证了美国政府的冷战战略思考和实施的非理性 ②。 其次 ,以美国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显现出强烈的“美国中心”倾向。无疑 ,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 冷战对外政策应该是冷战国际关系研究的主题 ,然而 ,民族国家之间的互动 ———对抗或合作 ———关系 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基点。如果一味地强调美国对外行为的“主导性”,不仅与史实不符 ,也无 益于冷战研究的学术体系化。例如 ,上个世纪 70 年代后 ,冷战学者受到“区域研究”的启发 ,开始依据 美国公布的外交档案研究美国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政策 ,推动了冷战研究的学术化。然而 ,随 之产生却是以“美国针对(U. S.2Toward) ”为鲜明特征的一批成果 ③。尽管对美国的政策褒贬不一 , 但无一例外均不考虑政策对象国(无论是盟国或友邦 ,还是对手国) 的政策思考与行为对美国政策的 影响 ,尽管有研究表明这种影响甚至“操纵 (Manip ulate) ”了某个时期美国针对某个事件的政策。结 果“, 美国中心”倾向严重制约了冷战研究朝着客观与科学的方向发展 ,由于不重视甚至忽略掌握别国 语言、利用别国资料、了解别国文化的重要性 ,以致“区域研究”最终走向衰败。值得庆幸的是 ,冷战于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结束后 ,原“共产主义阵营”学者的加盟和来自“对方”的档案文献的有限公开 ④使 得对冷战的研究日趋国际化 :这些“国际型”的学者能够熟练使用“对方国”语言 ,有幸接触“对方国”刚 刚解密的档案和文献 ,并能够将冷战的经历放在一个互动的环境中描述与分析 ⑤。 再者 ,由美国外交史学者为主体的冷战研究 ,表现出方法 ———历史描述和解读 ———的单一性。无 疑 ,史学研究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最大可能地占有和利用与课题相关的第一手或第二手的历史资料 ,冷 战外交史研究也不例外 ,然而 ,由于大多数美国与西方冷战学者对其他学术领域的理论知之甚少甚至 不屑一顾 ,以致目前的主流成果仍表现出明显的重实证、轻理论以及重描述、轻分析的研究倾向。其 结果是 :冷战的“叙述”完全受制于外交档案的公布周期和更新程度(大致按美国联邦档案 30 年后解 密的周期) ,大都处于“不断修正”、缓慢推进的状态 ;冷战研究议题和议程的设定基本与国际关系和国 60 世 界 历 史 200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④ ⑤ 在修正派的政治压力下 ,美国开始有选择地公开档案 ,当时最具政治影响的是“五角大楼文献”( The Pentagon Papers) 。 参见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美国和冷战的起源 ,1941 —1947》(John Lewis Gaddis , The United S tates and the Ori gins of the Col d W ar , 1941 - 1947)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2 年版 ;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俄罗斯、苏联和美国》(John Lewis Gaddis , Russia , the S oviet Union , and the United S tates) ,纽约 1978 年版 ;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遏制战略》(John Lewis Gaddis , S 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长期的和平》(John Lewis Gad2 dis , The L ong Peace)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约翰 ·路易斯 ·加迪斯《: 我们现在明白了 :冷战史再思考》(John Lewis Gaddis ,We N ow Know : Rethinking Col d W ar History ) ,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梅尔文 ·莱弗勒《: 权力的优势》(Mel2 vyn P. Leffler , A Preponderance of Power)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参见盖尔 ·伦德斯坦德《: 美国对东欧不作为政策 ,1943 —1947》( Geir Lundestad , The A merican Non2Policy Towards Eastern Europe , 1943 - 1947)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78 年版;罗伯特 ·麦克马洪《: 殖民主义与冷战:美国与印度尼西亚独立 ,1945 — 1949》(Robert McMahon , Colonialism and the Col d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truggle f or Indonesian Independence , 1945 - 1949) ,康乃尔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罗伯特 ·麦克马洪《: 边缘国家的冷战:美国、印度和巴基斯坦》(Robert McMahon , The Col d War on the Peri phery : The United States , India and Pakistan)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为了推动苏联和东欧国家涉及冷战的档案文献的解密 ,位于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术交流中心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成立 了“冷战国际关系史研究项目”,并不断地公布最新解密的档案与文献 ,www. cwihp . si. edu。 如 :奥德 ·韦斯特德(Odd Arne Westad) 、卡特因 ·韦瑟比( Katryn Weat hersby) 、大卫 ·沃尔夫(David Wolff) 、弗拉迪斯拉夫 ·朱布克(Vladislav Zubok) 、马克 ·克雷默(Mark Kramer) 、伊利亚 ·盖杜克( Ilya Gaiduk) 、克里斯琴 ·奥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 、陈兼(Jian Chen) 、翟强(Qiang Zhai) 、张曙光(Shu Guang Zhang) 等

拓展冷战研究 61 际问题研究不接轨,总是在“断代”(从小罗斯福到尼克松时代)和“地域”(对苏、对华、对北约等)之间 转圈:冷战研究的成果由于缺乏分析的系统性和深度,很难与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机 制等其他研究领域“跨界”对话、相得益彰。令人欣慰的是,随着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之间的不断 交叉越来越多的非外交史专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参与冷战的研究①为冷战研究如何体系化、理论 化提供了借鉴。 最后,以美国学者为主导的西方冷战国际关系研究还呈现出研究视角的简单与狭隘特征。以美 国冷战学者为例。大多数研究冷战的美国学者都是外交史“出身”,而作为史学子学科的外交史从一 开始就具有所谓“精英”学科的属性:始于19世纪后期的外交史研究,大都为退休外交官或外交官后 裔“闲时玩耍”的载体:于是,高层(内部)决定战争、和解、结盟、外交谈判、军备等政治性课题成为研究 的主要对象。现代冷战外交史的研究,尽管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如加上了经济外交、情报战、隐蔽 行动、宣传战、心理战等),但由于坚持国际关系就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研究的焦点仍然集中 于精英群体、政府机构和强势政治势力,结果忽略了构建冷战国际关系的其他重要方面,如非官方沟 通、体育教育文化艺术交流、非政府组织影响、族群社团活动、学术界争论、舆论领袖操控等。随着上 个世纪90年代欧洲学者加盟冷战研究,权力虽然仍被作为国际关系的“硬通货”(Hard currency),但 己经开始探索“政府政府”的关系与“政府社会”、“社会社会”、“政府市民”以及“文化一文化” 等关系的关联与互动②,“国际史”的视角逐步为西方与美国学者所接受。 据此,未来的冷战研究应考虑从多元、多层的角度出发,应用和深度比较分析的方法。 二、多元多层比较分析:以美国对华冷战研究为例 冷战的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会将重心放在对外政策的战略设计与政策决策上,然而,即便是属 于“最高机密”的决策行为也会在某个时间段就某个议题表现出某种或多种特点。若要根据这些特点得 出普遍的、一般的、甚至理论性的结论,这就要求冷战研究既要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判断与基本 假设相结合,也应对驱动、制约和与决策存在关联关系的多种因素进行多个层面的深度比较分析。例 如,研究者可以对长达40余年的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战略思考与政策决策行为分出多个分析面,并将 影响决策行为所有可能的因素放在一个较长的时空段内进行验证和比较分析,以求“论从史出”。实际 上,不少的学者(主要是外交史学者)己经开始进行此类尝试,并取得了应该引起注意的初步成果。 现存研究成果根据对冷战国际关系多元和多层属性的研究,发现至少存在着4个类别的冷战,其 中,美国对华冷战也可依此进行深度比较分析。 第一,安全冷战。冷战的一个要害是安全问题,大国的冷战安全战略和国防政策基本是围绕安全 这一主线展开的。安全冷战决策的参照系到底是什么?决策的逻辑又是什么?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 安全决策?有研究表明③(1)美国对“利益”与“威胁”的认知与界定出现严重混淆,更多地以“威胁” ①如:德勃拉·拉森:《過制的起源》(Deborah Welch Larson,Origins of Containment),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加迪 斯·史密斯:《道德理性和权力》(Gaddis Smith,Morality,Reason,.and Power),纽约l986年版。 ②位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的西蒙·弗兰萨(Simon Fraser))大学1979年开始T刊发《国际历史评论》(The1 nternational His- tory Review)季刊,经过20余年的努力,作为惟一以推动“因际史"研究的英文学术刊物,业已在多达48个国家发行。 ③参见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H972》,上海外语教有出版社2002年版;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 策:一般性思考》,《学术季刊2001年第2期。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际问题研究不接轨 ,总是在“断代”(从小罗斯福到尼克松时代) 和“地域”(对苏、对华、对北约等) 之间 转圈 ;冷战研究的成果由于缺乏分析的系统性和深度 ,很难与国际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国际组织与机 制等其他研究领域“跨界”对话、相得益彰。令人欣慰的是 ,随着人文与社会科学不同领域之间的不断 交叉 ,越来越多的非外交史专业的学者开始关注并参与冷战的研究 ①,为冷战研究如何体系化、理论 化提供了借鉴。 最后 ,以美国学者为主导的西方冷战国际关系研究还呈现出研究视角的简单与狭隘特征。以美 国冷战学者为例。大多数研究冷战的美国学者都是外交史“出身”,而作为史学子学科的外交史从一 开始就具有所谓“精英”学科的属性 :始于 19 世纪后期的外交史研究 ,大都为退休外交官或外交官后 裔“闲时玩耍”的载体 ;于是 ,高层(内部) 决定战争、和解、结盟、外交谈判、军备等政治性课题成为研究 的主要对象。现代冷战外交史的研究 ,尽管扩大了研究对象的范围(如加上了经济外交、情报战、隐蔽 行动、宣传战、心理战等) ,但由于坚持国际关系就是“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 ,研究的焦点仍然集中 于精英群体、政府机构和强势政治势力 ,结果忽略了构建冷战国际关系的其他重要方面 ,如非官方沟 通、体育教育文化艺术交流、非政府组织影响、族群社团活动、学术界争论、舆论领袖操控等。随着上 个世纪 90 年代欧洲学者加盟冷战研究 ,权力虽然仍被作为国际关系的“硬通货”( Hard currency) ,但 已经开始探索“政府 —政府”的关系与“政府 —社会”“、社会 —社会”“、政府 —市民”以及“文化 —文化” 等关系的关联与互动 ②“, 国际史”的视角逐步为西方与美国学者所接受。 据此 ,未来的冷战研究应考虑从多元、多层的角度出发 ,应用和深度比较分析的方法。 二、多元多层比较分析 :以美国对华冷战研究为例 冷战的研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仍会将重心放在对外政策的战略设计与政策决策上 ,然而 ,即便是属 于“最高机密”的决策行为也会在某个时间段就某个议题表现出某种或多种特点。若要根据这些特点得 出普遍的、一般的、甚至理论性的结论 ,这就要求冷战研究既要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的总体判断与基本 假设相结合 ,也应对驱动、制约和与决策存在关联关系的多种因素进行多个层面的深度比较分析。例 如 ,研究者可以对长达 40 余年的美国针对中国的冷战战略思考与政策决策行为分出多个分析面 ,并将 影响决策行为所有可能的因素放在一个较长的时空段内进行验证和比较分析 ,以求“论从史出”。实际 上 ,不少的学者(主要是外交史学者)已经开始进行此类尝试 ,并取得了应该引起注意的初步成果。 现存研究成果根据对冷战国际关系多元和多层属性的研究 ,发现至少存在着 4 个类别的冷战 ,其 中 ,美国对华冷战也可依此进行深度比较分析。 第一 ,安全冷战。冷战的一个要害是安全问题 ,大国的冷战安全战略和国防政策基本是围绕安全 这一主线展开的。安全冷战决策的参照系到底是什么 ? 决策的逻辑又是什么 ? 到底有哪些因素影响 安全决策 ? 有研究表明 ③: (1) 美国对“利益”与“威胁”的认知与界定出现严重混淆 ,更多地以“威胁” 拓展冷战研究 61 ① ② ③ 如 :德勃拉 ·拉森《: 遏制的起源》(Deborah Welch Larson , Ori gins of Containment)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加迪 斯 ·史密斯《: 道德、理性和权力》( Gaddis Smit h , Moralit y , Reason , and Power) ,纽约 1986 年版。 位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 的西蒙 ·弗兰萨(Simon Fraser) 大学 1979 年开始刊发《国际历史评论》( The I nternational His2 tory Review) 季刊 ,经过 20 余年的努力 ,作为惟一以推动“国际史”研究的英文学术刊物 ,业已在多达 48 个国家发行。 参见张曙光《: 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 :1949 —1972》,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 ;张曙光《: 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 策 :一般性思考》《, 学术季刊》2001 年第 2 期

62 世界历史 2007年第3期 定“利益”:(2)美国对其“盟友”的所谓“政治信誉”或战略“可信度”,成为影响战略决策者们“认知威 肋”"的重要“坐标系(Index)”,从而导致了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中“人为夸大”利益或威胁的现象;(3)作 为主导对华战略决策“话语”框架的美国式“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使得“理性选择”常常成为空谈 与幻想,因为“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与思维阻碍了“现实政策”的选择:(4)军政关系“恶化”使得华盛顿 的对华战略思考“误区”环生,特别是由于军方对其传统上对军事战略的咨询、决策、实施、评估“专利 权"”的极力维护,致使判断片面、政策失当:(5)美国对华战略决策中的“个人烙印”甚大,参与各个环节 决策者的教育程度、职业背景、政治可信度、行政能力与经验以及政治利益等诸因素,造成战略态势不 连贯、具体政策相互矛盾,以致给对手传递出“偏差”、“错误”的信息而造成对手误判;(6)美国式的“战 略文化”对华战略决策呈负面影响,主要反映在认知、判断“威胁”的性质与程度,以及决定是否动用武 力、动武的方式与冲突程度这两个战略关键层面上,常常“忽略”甚至“否认”中美双方由于“文化价值 观”以及“历史意识”不同而可能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 第二,经济冷战。为政治目的开展的所谓“经济外交”,是美国、苏联等大国冷战期间对外关系的 一个重要政策面。那么,经济冷战又是如何形成的?其运行具备哪些规律?例如,美国针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经济武器”使用,呈现出从短暂的“正面经济外交(Positive economic diplomacy)”如杜 鲁门早期的经贸经援“诱惑"政策很快转向历时数十年的“负面经济外交(Negative economic di- plomacy)”的轨迹。后者包括对“军事战略物资”"的禁运,对双边、多边贸易的封锁,对中国对外经贸的 制裁,对任何形式的对华金融、物资、技术援助的堵截。牵涉面之宽,持续时间之长,均属罕见。对此 的研究结果表明:(1)美国将自身的经济科技力量作为其对外政治运作的重要实力基础与战略资源: (2)美国对外决策者明确地要求经济利益服从国家安全利益:(3)美国频繁使用经济外交是“实力的傲 慢”使然;(4)美国在考虑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时,实施“经济武器”常常是在既不能“动武”(风险成本 过大)又无法“无所作为”(效益成本过小)的两难间作出的必然选择①。 第三,文化冷战。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现代化”制度能否成为推动民族国家对外利益的政治 武器?西方大国的冷战实践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美国上个世纪50年代对华“文化战略”的重点是堵截新中 国取得西方“文化和知识资源”,具体体现在通过联邦调查局、移民归化局以及部分“半官方”组织对中国留 学生进行“劝说”、“威吓”、“感化”,为他们提供工作研究便利等,以阻挠数万留美中国学生的回国②。与此同 时,至60年代初,美国通过“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科技发展项目加强了对台湾知识分子、“文化人”教育、 新闻传播界的“攻心战”,培植“现代化台湾人"”的主体意识。在60年代至70年代间,美对华“文化武器”又 翻新花样把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体育的“有限交流”当作“胁迫”北京放弃与美对抗的“奖励诱饵”,使其 成为“改善中美冲突关系的“试探动作”。出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感,美国的官方与非官方机构有计划、有配 合地打文化牌是美冷战思维与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层面。 第四,情报冷战。冷战期间,大国的战略情报分析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参与,使得“非战非和”的大 国关系错综复杂。通过对1949-1972年间的美国有关中国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简称NIE)、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简称SNIE)以及每 周情报简报(Weekly Intelligence Briefing,简称WB)的比较分析,不难发现③:(I)美国对华情报分 析对最高决策层影响甚大,其分析、判断与建议常常被直接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案;(2)情报分析 ①参见张曙光:《经济冷战:美因对华禁运与中苏同盟,1949H963》。 ②参见李洪山:《文化冷战与中美关系》,上海外田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因际研讨会论文, 2001年4月10H1日,上海。 ③参见李小兵:《美国对华情报分析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因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 研讨会论文,2001年4月10H1日,上海。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定“利益”; (2) 美国对其“盟友”的所谓“政治信誉”或战略“可信度”,成为影响战略决策者们“认知威 胁”的重要“坐标系(Index) ”,从而导致了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中“人为夸大”利益或威胁的现象 ; (3) 作 为主导对华战略决策“话语”框架的美国式“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使得“理性选择”常常成为空谈 与幻想 ,因为“意识形态”化的话语与思维阻碍了“现实政策”的选择 ; (4) 军政关系“恶化”使得华盛顿 的对华战略思考“误区”环生 ,特别是由于军方对其传统上对军事战略的咨询、决策、实施、评估“专利 权”的极力维护 ,致使判断片面、政策失当 ; (5) 美国对华战略决策中的“个人烙印”甚大 ,参与各个环节 决策者的教育程度、职业背景、政治可信度、行政能力与经验以及政治利益等诸因素 ,造成战略态势不 连贯、具体政策相互矛盾 ,以致给对手传递出“偏差”“、错误”的信息而造成对手误判 ; (6) 美国式的“战 略文化”对华战略决策呈负面影响 ,主要反映在认知、判断“威胁”的性质与程度 ,以及决定是否动用武 力、动武的方式与冲突程度这两个战略关键层面上 ,常常“忽略”甚至“否认”中美双方由于“文化价值 观”以及“历史意识”不同而可能采取“不同”的战略行为。 第二 ,经济冷战。为政治目的开展的所谓“经济外交”,是美国、苏联等大国冷战期间对外关系的 一个重要政策面。那么 ,经济冷战又是如何形成的 ? 其运行具备哪些规律 ? 例如 ,美国针对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经济武器”使用 ,呈现出从短暂的“正面经济外交(Positive economic diplomacy) ”———如杜 鲁门早期的经贸、经援“诱惑”政策 ———很快转向历时数十年的“负面经济外交(Negative economic di2 plomacy) ”的轨迹。后者包括对“军事战略物资”的禁运 ,对双边、多边贸易的封锁 ,对中国对外经贸的 制裁 ,对任何形式的对华金融、物资、技术援助的堵截。牵涉面之宽 ,持续时间之长 ,均属罕见。对此 的研究结果表明 : (1) 美国将自身的经济科技力量作为其对外政治运作的重要实力基础与战略资源 ; (2) 美国对外决策者明确地要求经济利益服从国家安全利益 ; (3) 美国频繁使用经济外交是“实力的傲 慢”使然 ; (4) 美国在考虑应对所谓“中国威胁”时 ,实施“经济武器”常常是在既不能“动武”(风险成本 过大) 又无法“无所作为”(效益成本过小) 的两难间作出的必然选择 ①。 第三 ,文化冷战。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现代化”制度能否成为推动民族国家对外利益的政治 武器 ? 西方大国的冷战实践给出了肯定的答案。美国上个世纪 50 年代对华“文化战略”的重点是堵截新中 国取得西方“文化和知识资源”,具体体现在通过联邦调查局、移民归化局以及部分“半官方”组织对中国留 学生进行“劝说”“、威吓”“、感化”,为他们提供工作研究便利等 ,以阻挠数万留美中国学生的回国②。与此同 时 ,至60 年代初 ,美国通过“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科技发展项目加强了对台湾知识分子“、文化人”、教育、 新闻传播界的“攻心战”,培植“现代化台湾人”的主体意识。在 60 年代至 70 年代间 ,美对华“文化武器”又 翻新花样 ,把文化、艺术、教育、卫生、体育的“有限交流”当作“胁迫”北京放弃与美对抗的“奖励诱饵”,使其 成为“改善”中美冲突关系的“试探动作”。出于自身的文化优越感 ,美国的官方与非官方机构有计划、有配 合地打文化牌 ,是美冷战思维与战略的一个重要政策层面。 第四 ,情报冷战。冷战期间 ,大国的战略情报分析及其对政策制定的参与 ,使得“非战非和”的大 国关系错综复杂。通过对 1949 - 1972 年间的美国有关中国的国家情报评估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简称 NIE) 、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 简称 SNIE) 以及每 周情报简报(Weekly Intelligence Briefing ,简称 WIB) 的比较分析 ,不难发现 ③: (1) 美国对华情报分 析对最高决策层影响甚大 ,其分析、判断与建议常常被直接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决议案 ; (2) 情报分析 62 世 界 历 史 200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参见张曙光《: 经济冷战 :美国对华禁运与中苏同盟 ,1949 —1963》。 参见李洪山《: 文化冷战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 , 2001 年 4 月 10 —11 日 ,上海。 参见李小兵《: 美国对华情报分析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 研讨会论文 ,2001 年 4 月 10 —11 日 ,上海

拓展冷战研究 63 家们在判断中国“使用武力”可能时,往往从中国的军事能力去演绎中国的战略意愿,否认“能力”与 “意愿”并不具有必然的关联关系;(3)美国对华情报分析的材料来源极为有限(相当一个时期,主要依 赖设在香港的“大陆报刊分析点”与台湾“大陆情报网防,误读、误导现象严重,以致在尼克松、基辛格 时期受贬:(4)美国对华情报分析“军政对立”现象明显,国务院、中情局、海陆空军各情报系统,常常各 持己见,让高层决策无所适从;(⑤)情报分析人员的“中国训练”十分欠缺,基本不了解中国政治文化传 统与变化,故表现出严重的文化偏执倾向。 此外,冷战中大国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具有不同的界面,彼此关联。美国对华的冷战战略与政 策起码显现出如下6个应该受到重视的分析层面。 第一,冷战外交谈判。冷战冲突的一个特点是:对抗并未完全排斥外交谈判。从1949到1972 年,中美在亚洲的对抗虽然时间长且危机四伏,但两个“殊死相搏”的大国却维持着长期的“非正式”谈 判。这种谈判机制为何存在?更重要的是,这种谈判对中美从对抗走向缓和起何作用?“黄华司徒 雷登”和位于板门店、日内瓦、华沙、巴黎、北京、纽约的中美谈判实践表明①:首先,此时期的中美接触 并非实质性的外交谈判,由于出自揣摩对方意图的需要,双方看重的是对话和传达“信息”(美国务院 所有关于“谈判”的文件,均使用“对话[Tlks]”一词),而不是指望通过接触解决双边冲突:其次,此时 期的中美“对话”并非对称性交往,中方受到北京最高决策者的直接指挥,而美方则隶属“部门”(国务 院)工作,很少得到总统乃至“国安会”的关注,即便是国务院内也未成立专门研究、指导班子,以致情 况报告多、政策建议少:再次此时期的中美“谈判”表现出文化磨合过程,特别是美国代表,由于对中 国政治文化缺乏了解、加之文化偏执倾向严重,常常将中方的“严正立场”与“原则声明”不是认作“顽 固不化”、“死要面子”便是解读为“阴谋诡计”、“耍花腔”、“无诚意”,结果失去不少与北京“深入沟通” 的机会:最后,此时期中美“交流”的最主要作用为“预设管道”,一旦政治机会成熟,便可由有限“对话” 提升为“实质谈判”(起码基辛格对这一“预设管道”的存在感到欣慰)。中美间这种打打谈谈、谈谈打 打、边打边谈,反映了冷战遏制与接触的基本特征。 第二,冷战专家。冷战过程的长期性产生了一批专长于冷战的“专家”,他们有些是职业外交与国 防官员,有些则是弃学从政者。无论是出于职业要求还是个人追求这些专家构成了制约大国冷战对 外政策的一个特殊群体。例如,美国对华政策很大程度受国务院内的所谓“中国通”影响。由于40年 代末麦卡锡主义对国务院内中国通主要指那些对中国有研究并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外交官的 清洗,该院内负责中国事务官员的背景、作用发生变化。通过对历届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中国科科 长、“政策计划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以及他们政策提案的研究,可以发现②:国务院中负责远东与 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己从“专家型”变为“职业型”,其作用也从单纯提供“专业”咨询变为运作具体政 策,从研究型的“通”"变成了操作性的“手”。这一变化的政策意义十分鲜明:首先,这些“中国手(China Hands)”的中国知识贫乏,判断、提议源于想当然者甚多,因此误判不断:其次,由于对台湾“消息源” 的依赖,他们更易受到台湾的蓄意操纵和影响(其中罗伯逊最为突出):再次,考虑到自身“仕途”,他们 更关注“顶头上司”的意图,并刻意去迎合(如艾奇逊时期的腊斯克、基辛格时期的洛德):最后,由于国 安会是核心政策的决策机构,国务院的“中国手”们更侧重政策的操作与评估。 ①参见夏亚峰:《与敌人谈判:冷战时期中美对话》(Yafeng Xia,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ChineseA merican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②参见高铮:《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与中美关系》,上海外田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 研讨会论文,2001年4月10H11日.上海。 ③“中国手"的概念最初由凯恩提出,参看凯恩:《中因手:美国外交官员以及他们的遭遇》(E.J.Kahn,Jr.,The China Hand本: A merica's Foreign Service Of ficers and What Befell Them),纽约I975年版。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家们在判断中国“使用武力”可能时 ,往往从中国的军事能力去演绎中国的战略意愿 ,否认“能力”与 “意愿”并不具有必然的关联关系 ; (3) 美国对华情报分析的材料来源极为有限(相当一个时期 ,主要依 赖设在香港的“大陆报刊分析点”与台湾“大陆情报网”) ,误读、误导现象严重 ,以致在尼克松、基辛格 时期受贬 ; (4) 美国对华情报分析“军政对立”现象明显 ,国务院、中情局、海陆空军各情报系统 ,常常各 持己见 ,让高层决策无所适从 ; (5) 情报分析人员的“中国训练”十分欠缺 ,基本不了解中国政治文化传 统与变化 ,故表现出严重的文化偏执倾向。 此外 ,冷战中大国的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具有不同的界面 ,彼此关联。美国对华的冷战战略与政 策起码显现出如下 6 个应该受到重视的分析层面。 第一 ,冷战外交谈判。冷战冲突的一个特点是 :对抗并未完全排斥外交谈判。从 1949 到 1972 年 ,中美在亚洲的对抗虽然时间长且危机四伏 ,但两个“殊死相搏”的大国却维持着长期的“非正式”谈 判。这种谈判机制为何存在 ? 更重要的是 ,这种谈判对中美从对抗走向缓和起何作用 ?“黄华 —司徒 雷登”和位于板门店、日内瓦、华沙、巴黎、北京、纽约的中美谈判实践表明 ①:首先 ,此时期的中美接触 并非实质性的外交谈判 ,由于出自揣摩对方意图的需要 ,双方看重的是对话和传达“信息”(美国务院 所有关于“谈判”的文件 ,均使用“对话[ Talks]”一词) ,而不是指望通过接触解决双边冲突 ;其次 ,此时 期的中美“对话”并非对称性交往 ,中方受到北京最高决策者的直接指挥 ,而美方则隶属“部门”(国务 院) 工作 ,很少得到总统乃至“国安会”的关注 ,即便是国务院内也未成立专门研究、指导班子 ,以致情 况报告多、政策建议少 ;再次 ,此时期的中美“谈判”表现出文化磨合过程 ,特别是美国代表 ,由于对中 国政治文化缺乏了解、加之文化偏执倾向严重 ,常常将中方的“严正立场”与“原则声明”不是认作“顽 固不化”“、死要面子”,便是解读为“阴谋诡计”“、耍花腔”“、无诚意”,结果失去不少与北京“深入沟通” 的机会 ;最后 ,此时期中美“交流”的最主要作用为“预设管道”,一旦政治机会成熟 ,便可由有限“对话” 提升为“实质谈判”(起码基辛格对这一“预设管道”的存在感到欣慰) 。中美间这种打打谈谈、谈谈打 打、边打边谈 ,反映了冷战遏制与接触的基本特征。 第二 ,冷战专家。冷战过程的长期性产生了一批专长于冷战的“专家”,他们有些是职业外交与国 防官员 ,有些则是弃学从政者。无论是出于职业要求还是个人追求 ,这些专家构成了制约大国冷战对 外政策的一个特殊群体。例如 ,美国对华政策很大程度受国务院内的所谓“中国通”影响。由于 40 年 代末麦卡锡主义对国务院内中国通 ———主要指那些对中国有研究并曾在中国工作过的外交官 ———的 清洗 ,该院内负责中国事务官员的背景、作用发生变化。通过对历届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中国科科 长“、政策计划委员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以及他们政策提案的研究 ,可以发现 ②:国务院中负责远东与 中国事务的高级官员已从“专家型”变为“职业型”,其作用也从单纯提供“专业”咨询变为运作具体政 策 ,从研究型的“通”变成了操作性的“手”。这一变化的政策意义十分鲜明 :首先 ,这些“中国手(China Hands) ”③的中国知识贫乏 ,判断、提议源于想当然者甚多 ,因此误判不断 ;其次 ,由于对台湾“消息源” 的依赖 ,他们更易受到台湾的蓄意操纵和影响(其中罗伯逊最为突出) ;再次 ,考虑到自身“仕途”,他们 更关注“顶头上司”的意图 ,并刻意去迎合(如艾奇逊时期的腊斯克、基辛格时期的洛德) ;最后 ,由于国 安会是核心政策的决策机构 ,国务院的“中国手”们更侧重政策的操作与评估。 拓展冷战研究 63 ① ② ③ 参见夏亚峰《: 与敌人谈判 :冷战时期中美对话》( Yafeng Xia , 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 : Chinese2A merican Talks during the Col d W ar) ,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参见高铮《: 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 研讨会论文 ,2001 年 4 月 10 —11 日 ,上海。 “中国手”的概念最初由凯恩提出 ,参看凯恩《: 中国手 :美国外交官员以及他们的遭遇》( E. J. Kahn , Jr. , The China Hands : A merica’s Forei gn S ervice Of f icers and W hat Be f ell Them) ,纽约 1975 年版

64 世界历史 2007年第3期 第三,冷战结盟。冷战使得世界政治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分化。冷战期间的盟友关系又具有怎样 的不同于其它不同国际关系形态的特征?根据传统的权力平衡逻辑,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德、日) 无疑只能“跟着美国跑”。然而,美国的盟友们对华盛顿对华政策的影响表明盟国对美国的“主动”影 响也不容忽视①。首先,美国盟国将自身利益置于“同盟”利益之上。由于集体防务与经济重建需要 美国长期大量的投入,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英国从二战一结束便致力于“锁定”华盛顿的“欧洲为主、 亚洲为次”的战略取向,伦敦的历届政府附和并参与了美国在亚洲的“危机处理”,但其“集体行动”始 终以避免“美国陷入亚洲”为原则。日本也屡次向华盛顿施压,以求不使东京的“区域防务”负担过重、 对外经济利益受损。其次美国决策者十分看重欧洲主要盟国对其“中国政策”的反应。这一点在文 官身上表现最为强烈。从艾奇逊、杜勒斯、腊斯克邦迪、麦克拉马拉到基辛格,均不同程度地出于对 盟国的“担忧”与“顾虑”,说服总统与军方不得对中国“冒险”,以“避免自由世界分崩离析”。再次,美 国的“亚洲盟友”有明显的“搭车”倾向。特别是南韩与台湾。由于深谙美国朝野十分在乎所谓“政治 信誉”的价值,它们不断以此“要挟”运作华盛顿“一步步走向亚洲泥潭”。 第四,冷战“内线”。冷战建构了一种特别的国内政治生态,使得内政外交的互动强度加大,分野也 变得模糊了。在考察美国对外关系史时,学者通常忽略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干预作用”。尽管基于理性 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利益应高于任何政党利益”的考虑,美国冷战期间确立了在对外政策上“两党一 致”的原则,但白宫在进行针对中国的战略思考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反映在国会中的政党之争, 如共和党控制的第80届国会对杜鲁门所谓“同情共产党中国”的压力,迫使民主党政府在朝鲜冒险②。 在对华政策上完全意识形态化了的“两党政治”,无疑影响了美国与对外与国防有关的高级行政主管委 任机制设立(如构建新闻总署、“美国之音、国防情报局等)、预算分配(对台军援拨款)、法案制定(《福摩 萨(台湾》决议案》、《台湾关系法》等)及军事行动允准等国家行为。另一方面,白宫也会有意利用国会为 其对华政策服务。例如,艾森豪威尔曾多次以国会为筹码抵制英国、日本、法国要求美国“克制”对华敌 意的压力:肯尼迪、约翰逊甚至尼克松均曾试图建立“国会对话管道”,以此试探北京的对美意图。这种 白宫与国会山之间的互动,起码是美国对华政策运作的一个不容轻视的决策层面。 第五,冷战“智库(Think-Tank)”。由非官方机构针对对外政策实施咨询的“智库”的出现实际上 是冷战的产物。在西方大国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区域研究的加强与普及,“智库”与对外政 策制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例如,美国的涉及对华政策的智库包括“半官方”研究机构(如兰德公司、 企业研究所、东西方中心、大西洋理事会、对外关系委员会)、“非赢利基金会(如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 会、亨利·卢斯基金会等)”"以及设在大学的“区域研究”(Area Studies)组织(如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康纳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如果对其稍作比较,就会发现这些“智库”在冷战期间至少发 挥了五方面的作用③(1)确定政策“议程”:通过学者的专项研究报告,提出“热点”问题,建议政策的 中长期研究议题排序与计划安排:(2)“聚焦”舆论:通过发表论文、演说、答记者问等形式,引导媒体, 炒作“热点”,如60年代关于“接触中国”与“遏制中国”争论的公开化;(3)教育动员:主要通过为年轻 学者和博士生符合智库“思想”的研究项目提供研究资助(如博士后和博士论文奖学金)、组织专业人 ①参见翟强:《美国的盟国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因语大学、上海因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论 文,2001年4月10H1日,上海。 ②参见许光秋: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 2001年4月10H1日,上海。 ③参见王建伟:《美国的智库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 论文,2001年4月10H1日,上海。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第三 ,冷战结盟。冷战使得世界政治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分化。冷战期间的盟友关系又具有怎样 的不同于其它不同国际关系形态的特征 ? 根据传统的权力平衡逻辑 ,美国的主要盟国(英、法、德、日) 无疑只能“跟着美国跑”。然而 ,美国的盟友们对华盛顿对华政策的影响表明盟国对美国的“主动”影 响也不容忽视 ①。首先 ,美国盟国将自身利益置于“同盟”利益之上。由于集体防务与经济重建需要 美国长期大量的投入 ,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英国从二战一结束便致力于“锁定”华盛顿的“欧洲为主、 亚洲为次”的战略取向 ,伦敦的历届政府附和并参与了美国在亚洲的“危机处理”,但其“集体行动”始 终以避免“美国陷入亚洲”为原则。日本也屡次向华盛顿施压 ,以求不使东京的“区域防务”负担过重、 对外经济利益受损。其次 ,美国决策者十分看重欧洲主要盟国对其“中国政策”的反应。这一点在文 官身上表现最为强烈。从艾奇逊、杜勒斯、腊斯克、邦迪、麦克拉马拉到基辛格 ,均不同程度地出于对 盟国的“担忧”与“顾虑”,说服总统与军方不得对中国“冒险”,以“避免自由世界分崩离析”。再次 ,美 国的“亚洲盟友”有明显的“搭车”倾向。特别是南韩与台湾。由于深谙美国朝野十分在乎所谓“政治 信誉”的价值 ,它们不断以此“要挟”、运作华盛顿“一步步走向亚洲泥潭”。 第四 ,冷战“内线”。冷战建构了一种特别的国内政治生态 ,使得内政外交的互动强度加大 ,分野也 变得模糊了。在考察美国对外关系史时 ,学者通常忽略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干预作用”。尽管基于理性 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利益应高于任何政党利益”的考虑 ,美国冷战期间确立了在对外政策上“两党一 致”的原则 ,但白宫在进行针对中国的战略思考时 ,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受制于反映在国会中的政党之争 , 如共和党控制的第 80 届国会对杜鲁门所谓“同情共产党中国”的压力 ,迫使民主党政府在朝鲜冒险 ②。 在对华政策上完全意识形态化了的“两党政治”,无疑影响了美国与对外与国防有关的高级行政主管委 任、机制设立(如构建新闻总署“、美国之音、国防情报局等) 、预算分配(对台军援拨款) 、法案制定《( 福摩 萨〈台湾〉决议案》《、台湾关系法》等)及军事行动允准等国家行为。另一方面 ,白宫也会有意利用国会为 其对华政策服务。例如 ,艾森豪威尔曾多次以国会为筹码抵制英国、日本、法国要求美国“克制”对华敌 意的压力;肯尼迪、约翰逊甚至尼克松均曾试图建立“国会对话管道”,以此试探北京的对美意图。这种 白宫与国会山之间的互动 ,起码是美国对华政策运作的一个不容轻视的决策层面。 第五 ,冷战“智库( Think2Tank) ”。由非官方机构针对对外政策实施咨询的“智库”的出现实际上 是冷战的产物。在西方大国 ,特别是随着上个世纪 60 年代区域研究的加强与普及“, 智库”与对外政 策制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例如 ,美国的涉及对华政策的智库包括“半官方”研究机构(如兰德公司、 企业研究所、东西方中心、大西洋理事会、对外关系委员会) “、非赢利基金会(如亚洲基金会、福特基金 会、亨利 ·卢斯基金会等) ”以及设在大学的“区域研究”(Area St udies) 组织(如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 中心、康纳尔大学的东南亚研究中心) 。如果对其稍作比较 ,就会发现这些“智库”在冷战期间至少发 挥了五方面的作用 ③: (1) 确定政策“议程”:通过学者的专项研究报告 ,提出“热点”问题 ,建议政策的 中长期研究议题排序与计划安排 ; (2)“聚焦”舆论 :通过发表论文、演说、答记者问等形式 ,引导媒体 , 炒作“热点”,如 60 年代关于“接触中国”与“遏制中国”争论的公开化 ; (3) 教育动员 :主要通过为年轻 学者和博士生符合智库“思想”的研究项目提供研究资助(如博士后和博士论文奖学金) 、组织专业人 64 世 界 历 史 2007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参见翟强《: 美国的盟国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论 文 ,2001 年 4 月 10 —11 日 ,上海。 参见许光秋《: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 , 2001 年 4 月 10 —11 日 ,上海。 参见王建伟《: 美国的智库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 论文 ,2001 年 4 月 10 —11 日 ,上海

拓展冷战研究 65 士(如新闻记者)“中国问题”培训班以及资助各类研讨会等,传播观点,扩大影响:(4)为对华决策与实 施培养和储备人才:由于美国的选举政治,使得政府对不少“专家官员"”形成了一个“旋转门”(即在政 府部门任职有进有出),“智库”就为那些暂时离任的官员提供了一个隐退之处,以便他们再次出山: (5)非正式外交角色:如担任“非正式联络”的策划、组织、运作和参与等(如尼克松“解冻”中美关系时 期的美国新闻媒体的重量级人物约翰·莱斯顿)。 第六,冷战社会。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仍将对外政策当作国内政治的延伸。冷战时期,大国(至 少是西方大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外交与国防政策的影响几乎达到了极致。例如,美国冷战期间 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是“左翼”政治、社会势力蓬勃发展,诸如劳工、女权、民权和平、“反文化”、“新左 派”、乃至人权等“左派激进”运动,均不同程度地成为美国对外行为的“动因”。这些“左翼”团体对冷 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主要具有“正负”两方面影响①。正面影响是:基于其批评美国“帝国主义对外 扩张”的立场,“左翼”势力对当政者“为了特殊集团的利益与中国为敌”的批判,形成了“公共压力”。 几乎所有的“左翼”运动,尽管“政治理念”不同,但都倾向于“少管外部闲事,集中解决好内部问题”,表 现出“传统的孤立主义”倾向。在“中国政策”上,更是认为“与亿万中国人对抗不符合美国人民利益”。 这一观点对美国“公众论坛”中要求与中国“缓和”的声音影响甚大。负面作用是:中国与某些“左翼” 势力(如美国共产党)的交往以及对“反政府”抗议行动、游行示威(如劳工、黑人、反越战团体等)的公 开支持,往往被美国政府以及保守势力认作蓄意“干涉美国内政”、“渗透美国政治”、“颠覆美国政权”, 从而加剧了决策者对中国的“疑惧”、“怨恨”、“防备”与“敌意”,结果降低了中美缓和的可能性。所以 这些政治与社会运动了制约或推动冷战的“社会力量”,而两者之间的互动也建构了具有明显冷战特 征的社会形态冷战社会或“安全社会(A security state)”。 显然,冷战国际关系的研究大有可为。历史分析法的核心是立足档案文献以求做出“接近原来” 的描述与判断,冷战中的主要大国不断公开和解密冷战时期外交与国防档案为传统冷战史的研究建 构了资料基础。然而,冷战研究的进一步拓展需要将“理论指导”与“历史实证”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 上对可能影响冷战战略思考和政策决策行为的多种因素进行多层面的深度比较。这样的跨学科、宽 角度、有深度的研究方法应该成为未来冷战研究发展的必要选项。 由于冷战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冷战研究的发展也需要世界性的参与。现存的成果表明,各国的学 者拥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尽管中国学者参与冷战国际关系的研究的热情越来越高涨,但如果 能够跨越断代和考证的传统,采用“多元、多层、比较”分析,中国完全可能以自身的研究在冷战国际学 术领域占据一席“高地”。 [本文作者张曙光,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上海200083] (责任编辑:高国荣) ①王希:《美国的社会思潮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论 文,2001年4月10H1日,上海。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士(如新闻记者)“中国问题”培训班以及资助各类研讨会等 ,传播观点 ,扩大影响 ; (4) 为对华决策与实 施培养和储备人才 :由于美国的选举政治 ,使得政府对不少“专家官员”形成了一个“旋转门”(即在政 府部门任职有进有出) “, 智库”就为那些暂时离任的官员提供了一个隐退之处 ,以便他们再次出山 ; (5) 非正式外交角色 :如担任“非正式联络”的策划、组织、运作和参与等(如尼克松“解冻”中美关系时 期的美国新闻媒体的重量级人物约翰 ·莱斯顿) 。 第六 ,冷战社会。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仍将对外政策当作国内政治的延伸。冷战时期 ,大国 (至 少是西方大国) 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外交与国防政策的影响几乎达到了极致。例如 ,美国冷战期间 国内政治的一大特点是“左翼”政治、社会势力蓬勃发展 ,诸如劳工、女权、民权、和平“、反文化”“、新左 派”、乃至人权等“左派激进”运动 ,均不同程度地成为美国对外行为的“动因”。这些“左翼”团体对冷 战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主要具有“正负”两方面影响 ①。正面影响是 :基于其批评美国“帝国主义对外 扩张”的立场“, 左翼”势力对当政者“为了特殊集团的利益与中国为敌”的批判 ,形成了“公共压力”。 几乎所有的“左翼”运动 ,尽管“政治理念”不同 ,但都倾向于“少管外部闲事 ,集中解决好内部问题”,表 现出“传统的孤立主义”倾向。在“中国政策”上 ,更是认为“与亿万中国人对抗不符合美国人民利益”。 这一观点对美国“公众论坛”中要求与中国“缓和”的声音影响甚大。负面作用是 :中国与某些“左翼” 势力(如美国共产党) 的交往以及对“反政府”抗议行动、游行示威(如劳工、黑人、反越战团体等) 的公 开支持 ,往往被美国政府以及保守势力认作蓄意“干涉美国内政”“、渗透美国政治”“、颠覆美国政权”, 从而加剧了决策者对中国的“疑惧”“、怨恨”、“防备”与“敌意”,结果降低了中美缓和的可能性。所以 这些政治与社会运动了制约或推动冷战的“社会力量”,而两者之间的互动也建构了具有明显冷战特 征的社会形态 ———冷战社会或“安全社会(A security state) ”。 显然 ,冷战国际关系的研究大有可为。历史分析法的核心是立足档案文献以求做出“接近原来” 的描述与判断 ,冷战中的主要大国不断公开和解密冷战时期外交与国防档案为传统冷战史的研究建 构了资料基础。然而 ,冷战研究的进一步拓展需要将“理论指导”与“历史实证”有机结合 ,并在此基础 上对可能影响冷战战略思考和政策决策行为的多种因素进行多层面的深度比较。这样的跨学科、宽 角度、有深度的研究方法应该成为未来冷战研究发展的必要选项。 由于冷战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冷战研究的发展也需要世界性的参与。现存的成果表明 ,各国的学 者拥有各自不同的优势和劣势。尽管中国学者参与冷战国际关系的研究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但如果 能够跨越断代和考证的传统 ,采用“多元、多层、比较”分析 ,中国完全可能以自身的研究在冷战国际学 术领域占据一席“高地”。 [本文作者张曙光 ,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上海 200083 ] (责任编辑 :高国荣) 拓展冷战研究 65 ① 王希《: 美国的社会思潮与中美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学会合办的“冷战与中美关系研究”国际研讨会论 文 ,2001 年 4 月 10 —11 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