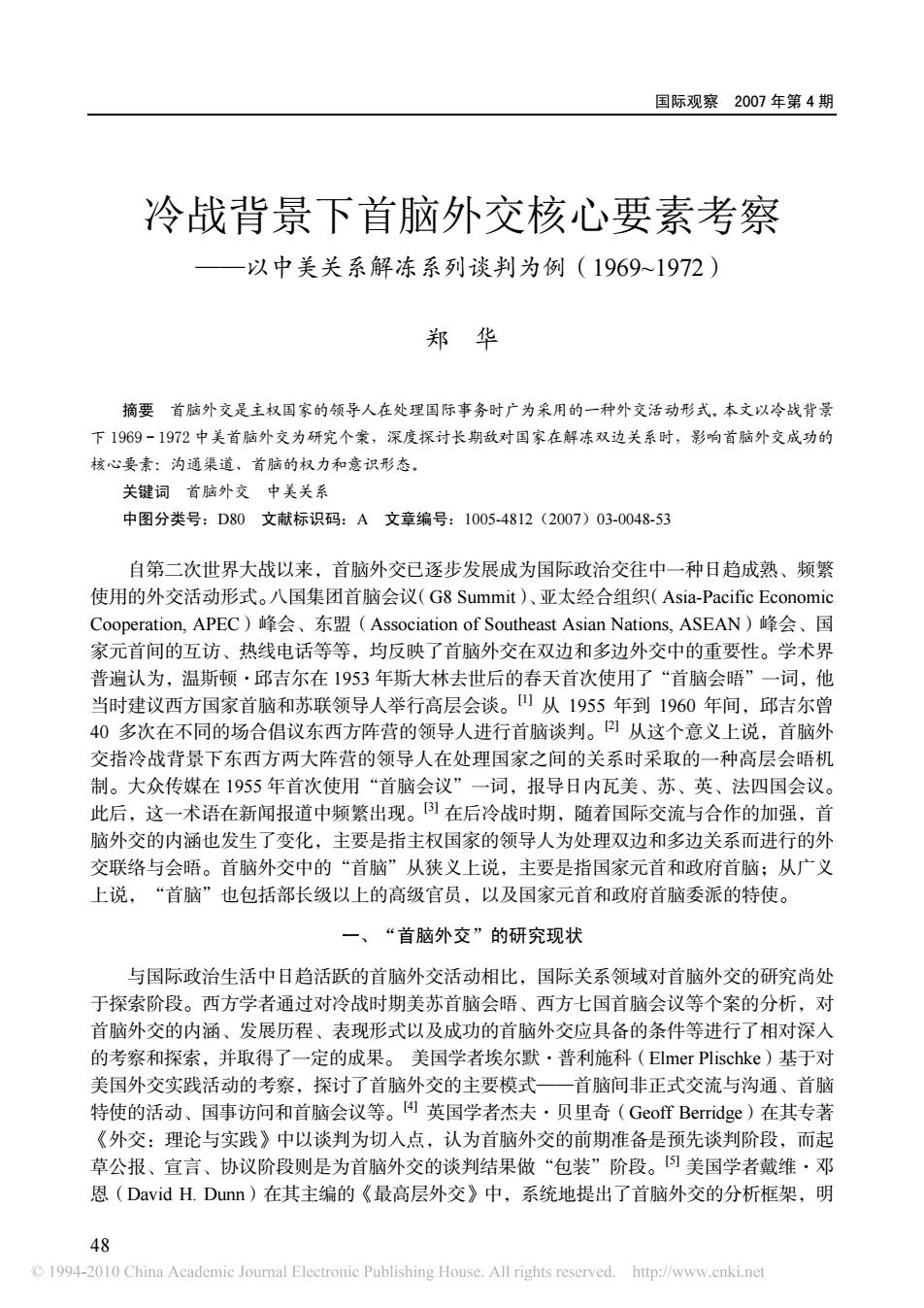
国际观察2007年第4期 冷战背景下首脑外交核心要素考察 以中美关系解冻系列谈判为例(1969~1972) 郑华 摘要首脑外交是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广为采用的一种外交活动形式。本文以冷战背景 下1969-1972中美首脑外交为研究个案,深度探讨长期敌对国家在解冻双边关系时,影响首脑外交成功的 核心要素:沟通渠道、首脑的权力和意识形态。 关键词首脑外交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3-0048-53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脑外交已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政治交往中一种日趋成熟、频繁 使用的外交活动形式。八国集团首脑会议(G8 Summit)、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峰会、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ASEAN)峰会、国 家元首间的互访、热线电话等等,均反映了首脑外交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中的重要性。学术界 普遍认为,温斯顿·邱吉尔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的春天首次使用了“首脑会晤”一词,他 当时建议西方国家首脑和苏联领导人举行高层会谈。山从1955年到1960年间,邱吉尔曾 40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倡议东西方阵营的领导人进行首脑谈判。四从这个意义上说,首脑外 交指冷战背景下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领导人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采取的一种高层会晤机 制。大众传媒在1955年首次使用“首脑会议”一词,报导日内瓦美、苏、英、法四国会议。 此后,这一术语在新闻报道中频繁出现。)]在后冷战时期,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加强,首 脑外交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领导人为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而进行的外 交联络与会晤。首脑外交中的“首脑”从狭义上说,主要是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从广义 上说,“首脑”也包括部长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以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委派的特使。 一、“首脑外交”的研究现状 与国际政治生活中日趋活跃的首脑外交活动相比,国际关系领域对首脑外交的研究尚处 于探索阶段。西方学者通过对冷战时期美苏首脑会晤、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个案的分析,对 首脑外交的内涵、发展历程、表现形式以及成功的首脑外交应具备的条件等进行了相对深入 的考察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美国学者埃尔默·普利施科(Elmer Plischke)基于对 美国外交实践活动的考察,探讨了首脑外交的主要模式一首脑间非正式交流与沟通、首脑 特使的活动、国事访问和首脑会议等。四英国学者杰夫·贝里奇(Geoff Berridge)在其专著 《外交:理论与实践》中以谈判为切入点,认为首脑外交的前期准备是预先谈判阶段,而起 草公报、宣言、协议阶段则是为首脑外交的谈判结果做“包装”阶段。)美国学者戴维·邓 恩(David H.Dunn)在其主编的《最高层外交》中,系统地提出了首脑外交的分析框架,明 48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国际观察 2007 年第 4 期 48 冷战背景下首脑外交核心要素考察 ——以中美关系解冻系列谈判为例(1969~1972) 郑 华 摘要 首脑外交是主权国家的领导人在处理国际事务时广为采用的一种外交活动形式。本文以冷战背景 下 1969-1972 中美首脑外交为研究个案,深度探讨长期敌对国家在解冻双边关系时,影响首脑外交成功的 核心要素:沟通渠道、首脑的权力和意识形态。 关键词 首脑外交 中美关系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3-0048-53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首脑外交已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政治交往中一种日趋成熟、频繁 使用的外交活动形式。八国集团首脑会议(G8 Summit)、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峰会、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峰会、国 家元首间的互访、热线电话等等,均反映了首脑外交在双边和多边外交中的重要性。学术界 普遍认为,温斯顿·邱吉尔在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的春天首次使用了“首脑会晤”一词,他 当时建议西方国家首脑和苏联领导人举行高层会谈。[1] 从 1955 年到 1960 年间,邱吉尔曾 40 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倡议东西方阵营的领导人进行首脑谈判。[2] 从这个意义上说,首脑外 交指冷战背景下东西方两大阵营的领导人在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时采取的一种高层会晤机 制。大众传媒在 1955 年首次使用“首脑会议”一词,报导日内瓦美、苏、英、法四国会议。 此后,这一术语在新闻报道中频繁出现。[3] 在后冷战时期,随着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加强,首 脑外交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指主权国家的领导人为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而进行的外 交联络与会晤。首脑外交中的“首脑”从狭义上说,主要是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从广义 上说,“首脑”也包括部长级以上的高级官员,以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委派的特使。 一、“首脑外交”的研究现状 与国际政治生活中日趋活跃的首脑外交活动相比,国际关系领域对首脑外交的研究尚处 于探索阶段。西方学者通过对冷战时期美苏首脑会晤、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等个案的分析,对 首脑外交的内涵、发展历程、表现形式以及成功的首脑外交应具备的条件等进行了相对深入 的考察和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美国学者埃尔默·普利施科(Elmer Plischke)基于对 美国外交实践活动的考察,探讨了首脑外交的主要模式——首脑间非正式交流与沟通、首脑 特使的活动、国事访问和首脑会议等。[4] 英国学者杰夫·贝里奇(Geoff Berridge)在其专著 《外交:理论与实践》中以谈判为切入点,认为首脑外交的前期准备是预先谈判阶段,而起 草公报、宣言、协议阶段则是为首脑外交的谈判结果做“包装”阶段。[5] 美国学者戴维·邓 恩(David H. Dunn)在其主编的《最高层外交》中,系统地提出了首脑外交的分析框架,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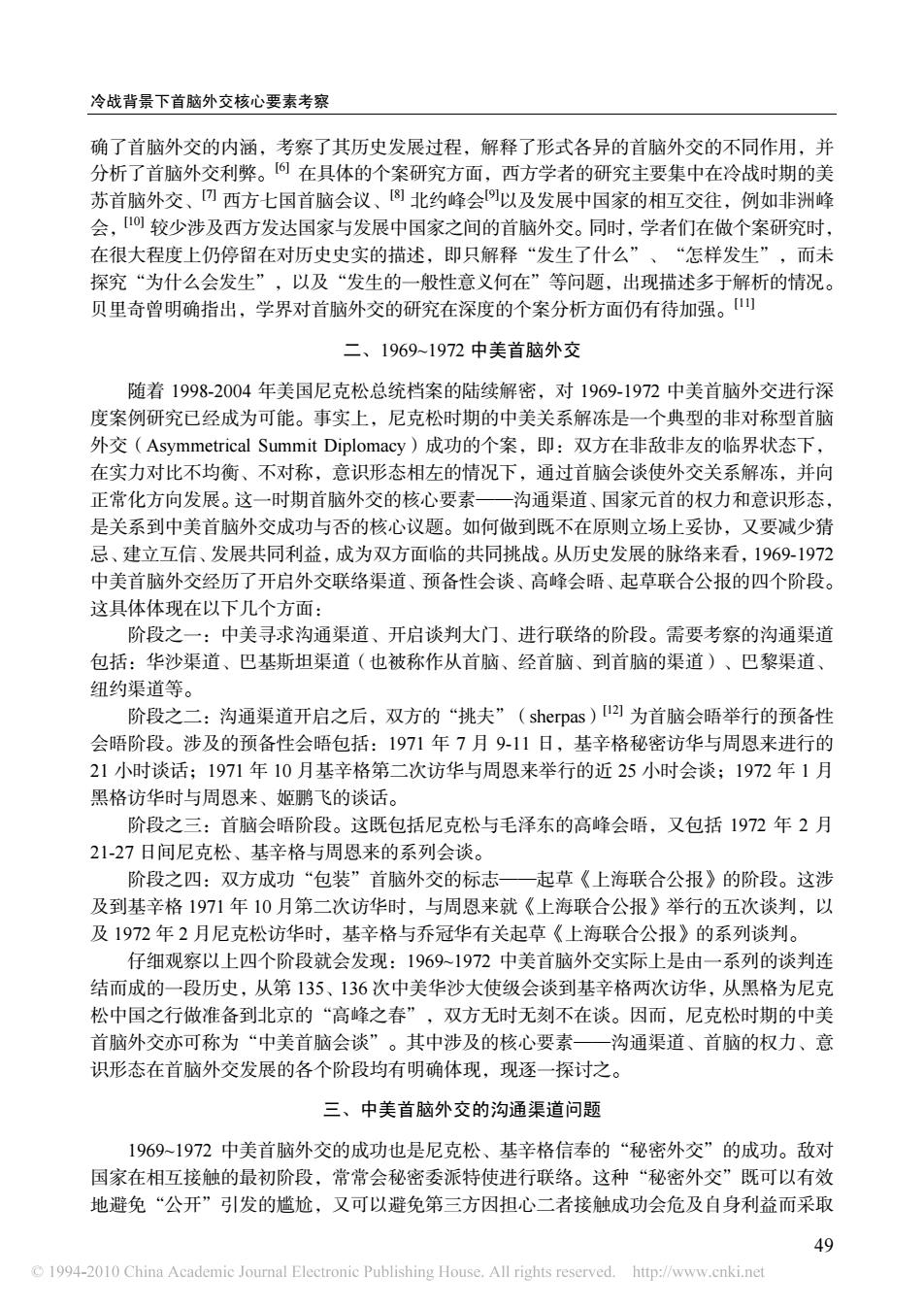
冷战背景下首脑外交核心要素考察 确了首脑外交的内涵,考察了其历史发展过程,解释了形式各异的首脑外交的不同作用,并 分析了首脑外交利弊。向在具体的个案研究方面,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时期的美 苏首脑外交、[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8]北约峰会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交往,例如非洲峰 会,【较少涉及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首脑外交。同时,学者们在做个案研究时, 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历史史实的描述,即只解释“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而未 探究“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发生的一般性意义何在”等问题,出现描述多于解析的情况。 贝里奇曾明确指出,学界对首脑外交的研究在深度的个案分析方面仍有待加强。山 二、1969~1972中美首脑外交 随着1998-2004年美国尼克松总统档案的陆续解密,对1969-1972中美首脑外交进行深 度案例研究已经成为可能。事实上,尼克松时期的中美关系解冻是一个典型的非对称型首脑 外交(Asymmetrical Summit Diplomacy)成功的个案,即:双方在非敌非友的临界状态下, 在实力对比不均衡、不对称,意识形态相左的情况下,通过首脑会谈使外交关系解冻,并向 正常化方向发展。这一时期首脑外交的核心要素一沟通渠道、国家元首的权力和意识形态, 是关系到中美首脑外交成功与否的核心议题。如何做到既不在原则立场上妥协,又要减少猜 忌、建立互信、发展共同利益,成为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1969-1972 中美首脑外交经历了开启外交联络渠道、预备性会谈、高峰会晤、起草联合公报的四个阶段。 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阶段之一:中美寻求沟通渠道、开启谈判大门、进行联络的阶段。需要考察的沟通渠道 包括:华沙渠道、巴基斯坦渠道(也被称作从首脑、经首脑、到首脑的渠道)、巴黎渠道、 纽约渠道等。 阶段之二:沟通渠道开启之后,双方的“挑夫”(sherpas)2为首脑会晤举行的预备性 会晤阶段。涉及的预备性会晤包括:1971年7月9-11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进行的 21小时谈话;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与周恩来举行的近25小时会谈;1972年1月 黑格访华时与周恩来、姬鹏飞的谈话。 阶段之三:首脑会晤阶段。这既包括尼克松与毛泽东的高峰会晤,又包括1972年2月 21-27日间尼克松、基辛格与周恩来的系列会谈。 阶段之四:双方成功“包装”首脑外交的标志一起草《上海联合公报》的阶段。这涉 及到基辛格1971年10月第二次访华时,与周恩来就《上海联合公报》举行的五次谈判,以 及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基辛格与乔冠华有关起草《上海联合公报》的系列谈判。 仔细观察以上四个阶段就会发现:1969~1972中美首脑外交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谈判连 结而成的一段历史,从第135、136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到基辛格两次访华,从黑格为尼克 松中国之行做准备到北京的“高峰之春”,双方无时无刻不在谈。因而,尼克松时期的中美 首脑外交亦可称为“中美首脑会谈”。其中涉及的核心要素一沟通渠道、首脑的权力、意 识形态在首脑外交发展的各个阶段均有明确体现,现逐一探讨之。 三、中美首脑外交的沟通渠道问题 1969~1972中美首脑外交的成功也是尼克松、基辛格信奉的“秘密外交”的成功。敌对 国家在相互接触的最初阶段,常常会秘密委派特使进行联络。这种“秘密外交”既可以有效 地避免“公开”引发的尴尬,又可以避免第三方因担心二者接触成功会危及自身利益而采取 49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冷战背景下首脑外交核心要素考察 49 确了首脑外交的内涵,考察了其历史发展过程,解释了形式各异的首脑外交的不同作用,并 分析了首脑外交利弊。[6] 在具体的个案研究方面,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冷战时期的美 苏首脑外交、[7] 西方七国首脑会议、[8] 北约峰会[9]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交往,例如非洲峰 会,[10] 较少涉及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首脑外交。同时,学者们在做个案研究时, 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历史史实的描述,即只解释“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而未 探究“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发生的一般性意义何在”等问题,出现描述多于解析的情况。 贝里奇曾明确指出,学界对首脑外交的研究在深度的个案分析方面仍有待加强。[11] 二、1969~1972 中美首脑外交 随着 1998-2004 年美国尼克松总统档案的陆续解密,对 1969-1972 中美首脑外交进行深 度案例研究已经成为可能。事实上,尼克松时期的中美关系解冻是一个典型的非对称型首脑 外交(Asymmetrical Summit Diplomacy)成功的个案,即:双方在非敌非友的临界状态下, 在实力对比不均衡、不对称,意识形态相左的情况下,通过首脑会谈使外交关系解冻,并向 正常化方向发展。这一时期首脑外交的核心要素——沟通渠道、国家元首的权力和意识形态, 是关系到中美首脑外交成功与否的核心议题。如何做到既不在原则立场上妥协,又要减少猜 忌、建立互信、发展共同利益,成为双方面临的共同挑战。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1969-1972 中美首脑外交经历了开启外交联络渠道、预备性会谈、高峰会晤、起草联合公报的四个阶段。 这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阶段之一:中美寻求沟通渠道、开启谈判大门、进行联络的阶段。需要考察的沟通渠道 包括:华沙渠道、巴基斯坦渠道(也被称作从首脑、经首脑、到首脑的渠道)、巴黎渠道、 纽约渠道等。 阶段之二:沟通渠道开启之后,双方的“挑夫”(sherpas)[12] 为首脑会晤举行的预备性 会晤阶段。涉及的预备性会晤包括:1971 年 7 月 9-11 日,基辛格秘密访华与周恩来进行的 21 小时谈话;1971 年 10 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与周恩来举行的近 25 小时会谈;1972 年 1 月 黑格访华时与周恩来、姬鹏飞的谈话。 阶段之三:首脑会晤阶段。这既包括尼克松与毛泽东的高峰会晤,又包括 1972 年 2 月 21-27 日间尼克松、基辛格与周恩来的系列会谈。 阶段之四:双方成功“包装”首脑外交的标志——起草《上海联合公报》的阶段。这涉 及到基辛格 1971 年 10 月第二次访华时,与周恩来就《上海联合公报》举行的五次谈判,以 及 1972 年 2 月尼克松访华时,基辛格与乔冠华有关起草《上海联合公报》的系列谈判。 仔细观察以上四个阶段就会发现:1969~1972 中美首脑外交实际上是由一系列的谈判连 结而成的一段历史,从第 135、136 次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到基辛格两次访华,从黑格为尼克 松中国之行做准备到北京的“高峰之春”,双方无时无刻不在谈。因而,尼克松时期的中美 首脑外交亦可称为“中美首脑会谈”。其中涉及的核心要素——沟通渠道、首脑的权力、意 识形态在首脑外交发展的各个阶段均有明确体现,现逐一探讨之。 三、中美首脑外交的沟通渠道问题 1969~1972 中美首脑外交的成功也是尼克松、基辛格信奉的“秘密外交”的成功。敌对 国家在相互接触的最初阶段,常常会秘密委派特使进行联络。这种“秘密外交”既可以有效 地避免“公开”引发的尴尬,又可以避免第三方因担心二者接触成功会危及自身利益而采取

国际观察2007年第4期 蓄意破坏行为。如果双方联络和交往带有一定的冒险色彩,秘密外交则可有效地避免因交往 受挫或失败对国家威望、尤其是对充当“追求者”的一方构成打击。此外,秘密外交更利于 接触双方不断调整、修改或放弃既定路线。]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双方的沟通渠道经 历了华沙会谈探虚实—巴基斯坦传信息—巴黎使馆做安排—纽约渠道送情报这样一个 复杂、漫长的过程。 中美双方解冻双边关系的最初“预热”阶段,也是有效地运用“非言语外交信号”进行 沟通的过程:中方在1969年12月7日(也就是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追逐中国外交官之 后的第四天),释放了两名乘游艇误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美方取消了太平洋第七舰队在台 湾海峡的巡逻。这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非语言行为为开启对话大门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4事实上,当尼克松上任伊始,致力于改善对华关系时,华盛顿首先想到的是通过华 沙大使级会谈同中国进行对话。的]但在经历了第135、136次大使级会谈之后,基辛格感到 华沙会谈公开化的模式太过拘束,国务院介入过多,遂将目光投向了巴基斯坦秘密渠道。由 于中美双方二十年来相互将对方“妖魔化”,双方高层领导人少有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 因而双方最初沟通渠道的开启也相对比较缓慢:华沙渠道的开启用了一年的时间;巴基斯坦 渠道的成功奏效则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巴黎渠道的开启则仅用了三天的时间。自1971年7月19日沃尔 特斯(Vernon Walters)第一次拜访黄镇大使官邸,到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前夕的l0月15日, 沃尔特斯与中方会晤多达17次。沃尔特斯除了为基辛格与黄镇的会晤穿针引线外,还为基辛 格第二次访华做了许多具体的铺垫工作。随着会晤次数的增多,沃尔特斯与黄镇之间的交往 也越来越自然融洽,黄镇会亲自为沃尔特斯倒茶,赠送北京果脯;沃尔特斯也会回赠巧克力。 在国与国的交往中,行为主体并不完全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多次交往之后得出的结论只是 对“意图的推测”(assumption of intentionality)。外交官常常是通过仔细观察对方的行为, 判断其真实的态度和意图。6沃尔特斯严格遵守了这条外交活动中的潜规则。他非常注重 与中方交往时的细节,甚至连中国官员的着装,是否佩戴毛泽东像章,黄镇送别时拍打他的 肩膀的友好肢体接触都会事无巨细地向黑格报告。因为,在外交活动中,姿势、手势、面部 表情、肢体活动、着装等等都会提供与地位、身份、角色和情感相关的重要线索。7 在经历了基辛格两次访华,巴黎渠道趋于稳定之后,纽约联络渠道的启动则格外迅速,仅 用了两天的时间。基辛格先后于1971年11月23日和12月10日,通过纽约渠道两次会晤中 国驻加拿大大使、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安理会代表黄华,向中方通报了华盛顿为解决印巴冲突所 做出的积极努力,并就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台独活动、中东和谈等议题,同中方交换了意见。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沟通渠道与双方高层领导人的会晤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机制: 一方面,沟通渠道传递的信息为中美高层会晤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谈判 前预先讨论议题、加强谈判成功可能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双方高层会晤的成功使中美之 间的沟通渠道日趋顺畅,逐步呈现出多元化、更新快的特点。事实上,美方对这些联络渠道 的重视程度远高于中方,在基辛格两次访华和尼克松访华过程中,确保“联络渠道”的畅通 和保密,都是双方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双方高层会晤的增多,双方信息传递由最初“犹 抱琵琶半遮面”的互探虚实阶段,逐步演化为简单接收信息和传达上级指示阶段,进而发展 到就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阶段。沟通渠道在中美首脑外交中成功地起到了“润滑剂”的作 用。 50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国际观察 2007 年第 4 期 50 蓄意破坏行为。如果双方联络和交往带有一定的冒险色彩,秘密外交则可有效地避免因交往 受挫或失败对国家威望、尤其是对充当“追求者”的一方构成打击。此外,秘密外交更利于 接触双方不断调整、修改或放弃既定路线。[13] 在中美关系解冻过程中,双方的沟通渠道经 历了华沙会谈探虚实——巴基斯坦传信息——巴黎使馆做安排——纽约渠道送情报这样一个 复杂、漫长的过程。 中美双方解冻双边关系的最初“预热”阶段,也是有效地运用“非言语外交信号”进行 沟通的过程:中方在 1969 年 12 月 7 日(也就是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尔追逐中国外交官之 后的第四天),释放了两名乘游艇误入中国海域的美国人;美方取消了太平洋第七舰队在台 湾海峡的巡逻。这种“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非语言行为为开启对话大门起到了积极的作 用。[14] 事实上,当尼克松上任伊始,致力于改善对华关系时,华盛顿首先想到的是通过华 沙大使级会谈同中国进行对话。[15] 但在经历了第 135、136 次大使级会谈之后,基辛格感到 华沙会谈公开化的模式太过拘束,国务院介入过多,遂将目光投向了巴基斯坦秘密渠道。由 于中美双方二十年来相互将对方“妖魔化”,双方高层领导人少有近距离、长时间的接触, 因而双方最初沟通渠道的开启也相对比较缓慢:华沙渠道的开启用了一年的时间;巴基斯坦 渠道的成功奏效则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 在基辛格秘密访华后,巴黎渠道的开启则仅用了三天的时间。自 1971 年 7 月 19 日沃尔 特斯(Vernon Walters)第一次拜访黄镇大使官邸,到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前夕的 10 月 15 日, 沃尔特斯与中方会晤多达 17 次。沃尔特斯除了为基辛格与黄镇的会晤穿针引线外,还为基辛 格第二次访华做了许多具体的铺垫工作。随着会晤次数的增多,沃尔特斯与黄镇之间的交往 也越来越自然融洽,黄镇会亲自为沃尔特斯倒茶,赠送北京果脯;沃尔特斯也会回赠巧克力。 在国与国的交往中,行为主体并不完全了解对方的真实意图,多次交往之后得出的结论只是 对“意图的推测”(assumption of intentionality)。外交官常常是通过仔细观察对方的行为, 判断其真实的态度和意图。[16] 沃尔特斯严格遵守了这条外交活动中的潜规则。他非常注重 与中方交往时的细节,甚至连中国官员的着装,是否佩戴毛泽东像章,黄镇送别时拍打他的 肩膀的友好肢体接触都会事无巨细地向黑格报告。因为,在外交活动中,姿势、手势、面部 表情、肢体活动、着装等等都会提供与地位、身份、角色和情感相关的重要线索。[17] 在经历了基辛格两次访华,巴黎渠道趋于稳定之后,纽约联络渠道的启动则格外迅速,仅 用了两天的时间。基辛格先后于 1971 年 11 月 23 日和 12 月 10 日,通过纽约渠道两次会晤中 国驻加拿大大使、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安理会代表黄华,向中方通报了华盛顿为解决印巴冲突所 做出的积极努力,并就联合国秘书长人选、台独活动、中东和谈等议题,同中方交换了意见。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沟通渠道与双方高层领导人的会晤形成了一个良性的互动机制: 一方面,沟通渠道传递的信息为中美高层会晤的成功铺平了道路,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谈判 前预先讨论议题、加强谈判成功可能性的作用;[18] 另一方面,双方高层会晤的成功使中美之 间的沟通渠道日趋顺畅,逐步呈现出多元化、更新快的特点。事实上,美方对这些联络渠道 的重视程度远高于中方,在基辛格两次访华和尼克松访华过程中,确保“联络渠道”的畅通 和保密,都是双方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随着双方高层会晤的增多,双方信息传递由最初“犹 抱琵琶半遮面”的互探虚实阶段,逐步演化为简单接收信息和传达上级指示阶段,进而发展 到就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阶段。沟通渠道在中美首脑外交中成功地起到了“润滑剂”的作 用

冷战背景下首脑外交核心要素考察 四、首脑的权威性问题 首脑外交的独特魅力在于国家元首会晤所衍生的权威性。然而,在基辛格两次访华、黑 格访华、尼克松访华的多轮谈判中,美国总统的权力却时而被放大,时而被缩小,美方一直 在审时度势地用话语强化或弱化总统的权力地位。在基辛格两次访华和黑格访华时,二人都 有意识地谈到“他们是总统的得力助手”,“谈话内容得到了总统的许可”,其目的是要提 升自身的谈判地位,增强话语的权威性。当谈到为总统访华做准备时,又说“美国总统访华 不能造成听训的印象”,并细致入微地安排总统衣、食、住、行、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其 目的是希望中方对美国总统访华高度重视。而当尼克松与周恩来谈判时,总统本人却在强调 美国国内的大选,两党政治的压力,国内反对势力对中美关系改善的破坏活动,解决台湾问 题遭遇的阻力等等,有意识地自贬身价、弱化总统的权力,从而避免中方迫使他在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做出明确表态。简言之,美方根据谈判目标在有意识地对总统权力做 弹性调整,总统的权力界定是为外交活动的目的服务的。 在美方看来,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权威性一定程度上在于他的“神秘色彩”和“不确定 性”。早在1971年基辛格两次访华和1972年1月初黑格访华时,美方曾多次设想若能得到 毛泽东的接见,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然而,毛泽东终究没有接见他们。正是毛泽东的这种 “神秘感”增强了他在谈判对手心目中的权威性。华盛顿认为“毛泽东非常精明,有敏锐的 直觉,富有创造性,具有诗人气质;他那出其不意的战术非常具有杀伤力”。9美方在抵京 之后不久就突然接到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的通知,以至于基辛格认为“那是奉召去朝见君王, 而不是应邀去会见政府首脑。”0然而当尼克松、基辛格等人步入毛泽东书房时,“书” 和“俭朴的陈设”给这些第一次近距离接近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基辛格看来,“毛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2四从一定意义上 说,毛泽东在对美谈判中表现出的举重若轻、游弋自如的谈判风格彰显了其独特的个人魅力 和领袖风范。 首脑的权威性还体现在国家元首的决策能力、下级对上级的服从等方面。在中美解冻双 边关系的多轮谈判中,中美之间的交往就演化为国家高层领导人、外交官员的谈判,是两个 谈判团队的较量。中方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个人服从集体”,强调“共性”,以至 于华盛顿认为,与中方谈判的实质就是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判,所以,中方谈判者表现出的 “自我”意识并不强烈。“在任何谈判中,自我意识较弱的一方往往容易取得胜利。因为, 谈判者会透过自我的迷雾,读懂对方种种建议的真实目的。”四中方的主要谈判者周恩来、 熊向晖、乔冠华、章文晋等都曾在青年时代留学海外,有的甚至获得了博士学位。西方求学 的经历不仅使他们拥有娴熟的外语语言能力,还具备丰富的跨文化交流经验,这使得他们能 以一种自然的、令美国人感到舒适的方式同对手进行交流。虽然谈判者的性格、行为方式、 个人经历等均具有个体性差异,但源于同一文化的“共质”会使美方感到同中国官员的谈判 具有“同一性”和“连续性”特征。2]而美方的谈判团队则因华府内部基辛格与国务卿罗 杰斯的权力之争,出现罗杰斯被排除在所有敏感政治议题谈判之外、屡次申请参与仍未能如 愿的尴尬局面。所以,当基辛格与乔冠华就《上海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共识,尼克松表示同 意之后,罗杰斯和格林等人却提出了多达十几处异议。美方成员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迫使 基辛格重返谈判桌,出现了被乔冠华质问“为何总统同意的草案还需修改”的难堪场面。下 属不和、部门之间的权力之争导致总统的意见仍需重新修改,美国总统的权威性面临着来自 51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冷战背景下首脑外交核心要素考察 51 四、首脑的权威性问题 首脑外交的独特魅力在于国家元首会晤所衍生的权威性。然而,在基辛格两次访华、黑 格访华、尼克松访华的多轮谈判中,美国总统的权力却时而被放大,时而被缩小,美方一直 在审时度势地用话语强化或弱化总统的权力地位。在基辛格两次访华和黑格访华时,二人都 有意识地谈到“他们是总统的得力助手”,“谈话内容得到了总统的许可”,其目的是要提 升自身的谈判地位,增强话语的权威性。当谈到为总统访华做准备时,又说“美国总统访华 不能造成听训的印象”,并细致入微地安排总统衣、食、住、行、安全保卫等诸多环节,其 目的是希望中方对美国总统访华高度重视。而当尼克松与周恩来谈判时,总统本人却在强调 美国国内的大选,两党政治的压力,国内反对势力对中美关系改善的破坏活动,解决台湾问 题遭遇的阻力等等,有意识地自贬身价、弱化总统的权力,从而避免中方迫使他在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做出明确表态。简言之,美方根据谈判目标在有意识地对总统权力做 弹性调整,总统的权力界定是为外交活动的目的服务的。 在美方看来,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权威性一定程度上在于他的“神秘色彩”和“不确定 性”。早在 1971 年基辛格两次访华和 1972 年 1 月初黑格访华时,美方曾多次设想若能得到 毛泽东的接见,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然而,毛泽东终究没有接见他们。正是毛泽东的这种 “神秘感”增强了他在谈判对手心目中的权威性。华盛顿认为“毛泽东非常精明,有敏锐的 直觉,富有创造性,具有诗人气质;他那出其不意的战术非常具有杀伤力”。[19] 美方在抵京 之后不久就突然接到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的通知,以至于基辛格认为“那是奉召去朝见君王, 而不是应邀去会见政府首脑。” [20] 然而当尼克松、基辛格等人步入毛泽东书房时,“书” 和“俭朴的陈设”给这些第一次近距离接近中国领导人毛泽东的美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基辛格看来,“毛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21] 从一定意义上 说,毛泽东在对美谈判中表现出的举重若轻、游弋自如的谈判风格彰显了其独特的个人魅力 和领袖风范。 首脑的权威性还体现在国家元首的决策能力、下级对上级的服从等方面。在中美解冻双 边关系的多轮谈判中,中美之间的交往就演化为国家高层领导人、外交官员的谈判,是两个 谈判团队的较量。中方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个人服从集体”,强调“共性”,以至 于华盛顿认为,与中方谈判的实质就是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判,所以,中方谈判者表现出的 “自我”意识并不强烈。“在任何谈判中,自我意识较弱的一方往往容易取得胜利。因为, 谈判者会透过自我的迷雾,读懂对方种种建议的真实目的。”[22] 中方的主要谈判者周恩来、 熊向晖、乔冠华、章文晋等都曾在青年时代留学海外,有的甚至获得了博士学位。西方求学 的经历不仅使他们拥有娴熟的外语语言能力,还具备丰富的跨文化交流经验,这使得他们能 以一种自然的、令美国人感到舒适的方式同对手进行交流。虽然谈判者的性格、行为方式、 个人经历等均具有个体性差异,但源于同一文化的“共质”会使美方感到同中国官员的谈判 具有“同一性”和“连续性”特征。[23] 而美方的谈判团队则因华府内部基辛格与国务卿罗 杰斯的权力之争,出现罗杰斯被排除在所有敏感政治议题谈判之外、屡次申请参与仍未能如 愿的尴尬局面。所以,当基辛格与乔冠华就《上海联合公报》草案达成共识,尼克松表示同 意之后,罗杰斯和格林等人却提出了多达十几处异议。美方成员的这种强烈的自我意识迫使 基辛格重返谈判桌,出现了被乔冠华质问“为何总统同意的草案还需修改”的难堪场面。下 属不和、部门之间的权力之争导致总统的意见仍需重新修改,美国总统的权威性面临着来自

国际观察2007年第4期 华府官僚体制的挑战。 五、意识形态因素 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政府习惯以威胁来界定利益,而意识形态则成为预测对手行为、 判定威胁的首要标准。而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对外政策理念中,传统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界定 美国战略利益的唯一坐标,不再是认知对这些利益的“外来威肋胁”的衡量标准,不再是评估 作为“保护”这些利益的战略资源的重要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对美国国家根本利益与目标的 现实和理性的认识。4尼基组合认为应以利益界定威胁。既然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均势战 略格局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一贯性,既然美国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不足以取得均势的战略格局, 那么美国应该能够与不同的国家,甚至可以与社会制度完全相左的国家合作,只要它们拥有 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并愿意共同抵御挑战世界稳定的行为。而苏联的扩张则是对尼克松奉 行的“均势战略”的挑战,是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是尼克松政府为 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美方在对华谈判中有意识地弱化意 识形态因素,避免谈判破裂。建立良好氛围、确保尼克松访华成功则成为华盛顿谈判的重要 指导原则之一。事实上,早在1969年美方为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做准备时,华盛顿就明 确授意谈判代表斯托塞尔,“如果中方对美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指责,美方不要对此 做任何回应。”6]等到为基辛格秘密访华做准备时,美方恪守的谈判策略则是,“强调双 方的共同点,弱化分歧,只要中方不迫使,尽量不谈分歧。如果被迫要谈分歧,要说‘如果 …y 是这样的’,而不要说‘不,除非’”,要对中方的强硬路线做到视而不见;待良好的 气氛建立之后,再谈首脑会晤的事情。”7当军人出身的黑格率领先遣组访华时,这位“照 章办事”、“不善言辞”的基辛格得力助手却反复告诫先遣组成员,“如果中国人谈及伟大 导师毛泽东的教海,要礼貌地倾听,不要做评论。”】当尼克松为与毛泽东的高峰会晤做 准备时,美方则更为关注对毛泽东个人的褒奖。美方认为:“为了实现美国的目的和利益, 要给予毛泽东一定的尊严,并表示一定的尊重,不能和他争吵,即使是批评中方的政策,也 不要针对个人;虽不能称赞共产主义,但可以赞扬中国古代有作为的皇帝,可以称赞中国的 历史、文化,如艺术、绘画、建筑,和中国人的素质;可以赞扬毛泽东写的诗。”29正是 美方刻意营造良好谈判氛围、有意规避意识形态分歧的作法使得中美首脑外交能够取得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同中国和东欧等共产主义国家的交往并不意味着美国能够容忍共产 主义政权在世界其他国家诞生,这一点在“越南议题”的谈判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美方在谈 判中一直强调要维护大国尊严和威望,基辛格认为“美国不能只是从越南走开,就像换一个 电视频道一样。”B0]在尼克松看来,任何新生共产主义政权的出现都会对现存的均势格局 构成挑战。换句话说,华盛顿出于维护全球均势格局的考虑,可以容忍已有共产主义政权的 存在,但却不能允许新生共产主义政权的出现。 1972年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签署标志着中美首脑外交的圆满成功。虽 然战场上曾兵戎相向的两国领导人握手长达约一分钟之久,但双方均未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 正如尼克松所言,“过去一些时候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仍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 起来的,是我们有超越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虽然我们不能弥合双方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 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B创中美首脑外交的成功是双方有效地 把握沟通渠道、理解首脑的权威性、弱化意识形态分歧的过程。 52 C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国际观察 2007 年第 4 期 52 华府官僚体制的挑战。 五、意识形态因素 自朝鲜战争以来,美国政府习惯以威胁来界定利益,而意识形态则成为预测对手行为、 判定威胁的首要标准。而在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对外政策理念中,传统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界定 美国战略利益的唯一坐标,不再是认知对这些利益的“外来威胁”的衡量标准,不再是评估 作为“保护”这些利益的战略资源的重要内容,取而代之的是对美国国家根本利益与目标的 现实和理性的认识。[24] 尼-基组合认为应以利益界定威胁。既然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均势战 略格局而不是意识形态的一贯性,既然美国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不足以取得均势的战略格局, 那么美国应该能够与不同的国家,甚至可以与社会制度完全相左的国家合作,只要它们拥有 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并愿意共同抵御挑战世界稳定的行为。而苏联的扩张则是对尼克松奉 行的“均势战略”的挑战,是美国面临的首要威胁。[25] 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是尼克松政府为 维护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因此,美方在对华谈判中有意识地弱化意 识形态因素,避免谈判破裂。建立良好氛围、确保尼克松访华成功则成为华盛顿谈判的重要 指导原则之一。事实上,早在 1969 年美方为第 135 次中美大使级会谈做准备时, 华盛顿就明 确授意谈判代表斯托塞尔,“如果中方对美进行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指责,美方不要对此 做任何回应。”[26] 等到为基辛格秘密访华做准备时,美方恪守的谈判策略则是,“强调双 方的共同点,弱化分歧,只要中方不迫使,尽量不谈分歧。如果被迫要谈分歧,要说‘如果……, 是这样的’,而不要说‘不,除非……’”,要对中方的强硬路线做到视而不见;待良好的 气氛建立之后,再谈首脑会晤的事情。”[27] 当军人出身的黑格率领先遣组访华时,这位“照 章办事”、“不善言辞”的基辛格得力助手却反复告诫先遣组成员,“如果中国人谈及伟大 导师毛泽东的教诲,要礼貌地倾听,不要做评论。”[28] 当尼克松为与毛泽东的高峰会晤做 准备时,美方则更为关注对毛泽东个人的褒奖。美方认为:“为了实现美国的目的和利益, 要给予毛泽东一定的尊严,并表示一定的尊重,不能和他争吵,即使是批评中方的政策,也 不要针对个人;虽不能称赞共产主义,但可以赞扬中国古代有作为的皇帝,可以称赞中国的 历史、文化,如艺术、绘画、建筑,和中国人的素质;可以赞扬毛泽东写的诗。”[29] 正是 美方刻意营造良好谈判氛围、有意规避意识形态分歧的作法使得中美首脑外交能够取得成功。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同中国和东欧等共产主义国家的交往并不意味着美国能够容忍共产 主义政权在世界其他国家诞生,这一点在“越南议题”的谈判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美方在谈 判中一直强调要维护大国尊严和威望,基辛格认为“美国不能只是从越南走开,就像换一个 电视频道一样。”[30] 在尼克松看来,任何新生共产主义政权的出现都会对现存的均势格局 构成挑战。换句话说,华盛顿出于维护全球均势格局的考虑,可以容忍已有共产主义政权的 存在,但却不能允许新生共产主义政权的出现。 1972 年 2 月 28 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签署标志着中美首脑外交的圆满成功。虽 然战场上曾兵戎相向的两国领导人握手长达约一分钟之久,但双方均未在自己的原则上妥协。 正如尼克松所言,“过去一些时候我们曾是敌人。今天我们仍有巨大的分歧。使我们走到一 起来的,是我们有超越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虽然我们不能弥合双方之间的鸿沟,我们却能 够设法搭一座桥,以便我们能够越过它进行会谈。”[31] 中美首脑外交的成功是双方有效地 把握沟通渠道、理解首脑的权威性、弱化意识形态分歧的过程

冷战背景下首脑外交核心要素考察 注释: [1]Naunihal Singh,Diplomacy for the 21 Century,New Dhlhi:Mittal Publications,2002,p.117. [2]Abba Solomon Eban,"Where-If Not at the Summit?",Diplomacy for the Next Centur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8.p.89. [3][4]Elmer Plischke,Summit Diplomacy:Personal Diplomacy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74,p.4. [5]Geoff R.Berridge,Diplomacy:Theory and Practice,London:Prentice,1995. [6]David H.Dunn ed.,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 [7]R.Schaetzel and H.B.Malmgren,"Talking Heads",Foreign Policy,No.39,Summer 1980,pp.130-142;G. R.Weihmiller and D.Doder,US-Soviet Summits,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86;Joseph G.Whelan, The Moscow Summit,1988:Regan and Gorbachey in Negotiation,Boulder:Westview Press,1990;Michael Andersen Theo Farrell,"Superpower Summitry",in David H.Dunn ed.,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 pp.67-87 [8]R.D.Putnum and N.Bayne,Hanging Together:The Seven-Power Summit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J.D.Armstrong,"The Group of Seven Summits",in David H.Dunn ed.,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pp.41-52. [9]Bill Park,"NATO Summits",in David H.Dunn ed.,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pp.88-105. [10]Richard Hodder-Williams,"African Summitry",in David H.Dunn ed.,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 pp.147-164. [ll】详见G.R.Berridge的个人网站:http:/www.grberridge.co.uk/promote_call.html,2006年4月6日。 [12]“挑夫”最初是指帮助攀登喜马拉雅山的登山者搬运行李的人,自1953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后, 这个词汇和“首脑外交”同时进入外交术语之中,参见David H.Dunn ed,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p.20. [13]G.R.Berridge:Talking to the Enemy,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4,pp.103-105 [14][16][17]Raymond Cohen,Theatre ofPower,New York:Longman Inc.,1987,pp.20,2. [15】有关“华沙渠道在中美解冻过程中的作用”的论述,详见郑华:“华沙渠道与中美关系解冻一华 盛顿决策内幕1969-1972”,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94-101页。 [18]Ronald J.Fisher,"Prenegotiation Problem-solving Discussion",in Janice Gross Stein ed.,Getting to the Table,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p.206-238. [19][29]"Evaluation of Mao Tse-tung Chou En-lai by An American Lawyer",Source:NSC Box 847, Folder 2,National Archives II. [20[21]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陈瑶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8、9、 12、13页。 [22]Patrick J.Cleary,The Negotiation Handbook,New York:M.E.Sharpe,2001,p.19. [23]Guy Oliver Faure,Jeffrey Z.Rubin eds..Culture and Negotiation:The Resolution of Water Disputes. London:SAGE Publication,1993,pp.38-46. [24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1949-1972》,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316-362页。 [25]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274-308. [26]Dec.10,1969,Kissinger to Nixon,"Warsaw Talks,Source:NPMP,NSCF,box 700 Poland-Warsaw Talks,Vol.I,National Archives II. [27]Briefing Book for HAK Secret Visit to China,Source:NSC Files,Box 850,Folder 4,National Archives Il. [28]Memorandum Dec.23,Haig to Kissinger,"Items to discuss with Advance Party",Source:NSC Box 1037, Folder 1,National Archives II. [30]Henry Kissinger,White House Years,Little Brown,1979,pp.227-229. [31]“尼克松祝酒词”,1972年2月2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基辛格档案(NSC,HAK,Box91),National Archives II. (作者简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博士,上海,200030) 收稿日期:2007年5月 53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All rights reserved.http://www.cnki.net
冷战背景下首脑外交核心要素考察 53 注释: [1] Naunihal Singh,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New Dhlhi: Mittal Publications, 2002, p.117. [2] Abba Solomon Eban, “Where—If Not at the Summit?”, Diplomacy for the Next Centu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89. [3] [4] Elmer Plischke, Summit Diplomacy: Personal Diplomacy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74, p.4. [5] Geoff R. Berridge, Diplomacy: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rentice, 1995. [6] David H. Dunn ed., 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 London: Macmillan Press Ltd, 1996. [7] R. Schaetzel and H. B. Malmgren, “Talking Heads”, Foreign Policy, No. 39, Summer 1980, pp. 130-142; G. R. Weihmiller and D. Doder, US-Soviet Summits,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6; Joseph G. Whelan, The Moscow Summit, 1988: Regan and Gorbachev in Negotia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0; Michael Andersen & Theo Farrell, “Superpower Summitry”, in David H. Dunn ed., 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 pp.67-87. [8] R. D. Putnum and N. Bayne, Hanging Together: The Seven-Power Summit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J.D. Armstrong, “The Group of Seven Summits”, in David H. Dunn ed., 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 pp. 41-52. [9] Bill Park, “NATO Summits”, in David H. Dunn ed., 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 pp.88-105. [10] Richard Hodder-Williams, “African Summitry”, in David H. Dunn ed., 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 pp.147-164. [11] 详见 G. R. Berridge 的个人网站:http://www.grberridge.co.uk/promote_call.html, 2006 年 4 月 6 日。 [12] “挑夫”最初是指帮助攀登喜马拉雅山的登山者搬运行李的人,自 1953 年攀登珠穆朗玛峰成功后, 这个词汇和“首脑外交”同时进入外交术语之中,参见 David H. Dunn ed., Diplomacy at the Highest Level, p.20. [13] G. R. Berridge: Talking to the Enem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103-105. [14] [16] [17] Raymond Cohen, Theatre of Power, New York: Longman Inc., 1987, pp.20, 2. [15] 有关“华沙渠道在中美解冻过程中的作用”的论述,详见郑华:“华沙渠道与中美关系解冻——华 盛顿决策内幕 1969-1972”,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94-101 页。 [18] Ronald J. Fisher, “Prenegotiation Problem-solving Discussion”, in Janice Gross Stein ed., Getting to the Table,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206-238. [19] [29] “Evaluation of Mao Tse-tung & Chou En-lai by An American Lawyer”, Source: NSC Box 847, Folder 2, National Archives II. [20] [21] 基辛格:《白宫岁月》(第四册),陈瑶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 年版,第 8、9、 12、13 页。 [22] Patrick J. Cleary, The Negotiation Handbook, New York: M. E. Sharpe, 2001, p.19. [23] Guy Oliver Faure, Jeffrey Z. Rubin eds., Culture and Negotiation: The Resolution of Water Disput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93, pp.38-46. [24] 张曙光:《美国对华战略考虑与决策 1949-1972》,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年,316-362 页。 [25]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274-308. [26] Dec. 10, 1969, Kissinger to Nixon, “Warsaw Talks, Source: NPMP, NSCF, box 700 Poland-Warsaw Talks, Vol. I, National Archives II. [27] Briefing Book for HAK Secret Visit to China, Source: NSC Files, Box 850, Folder 4, National Archives II. [28] Memorandum Dec. 23, Haig to Kissinger, “Items to discuss with Advance Party”, Source: NSC Box 1037, Folder 1, National Archives II. [30] 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Little Brown, 1979, pp. 227-229. [31]“尼克松祝酒词”,1972 年 2 月 21 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基辛格档案(NSC,HAK,Box 91), National Archives II. (作者简介: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博士,上海,200030) 收稿日期:2007 年 5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