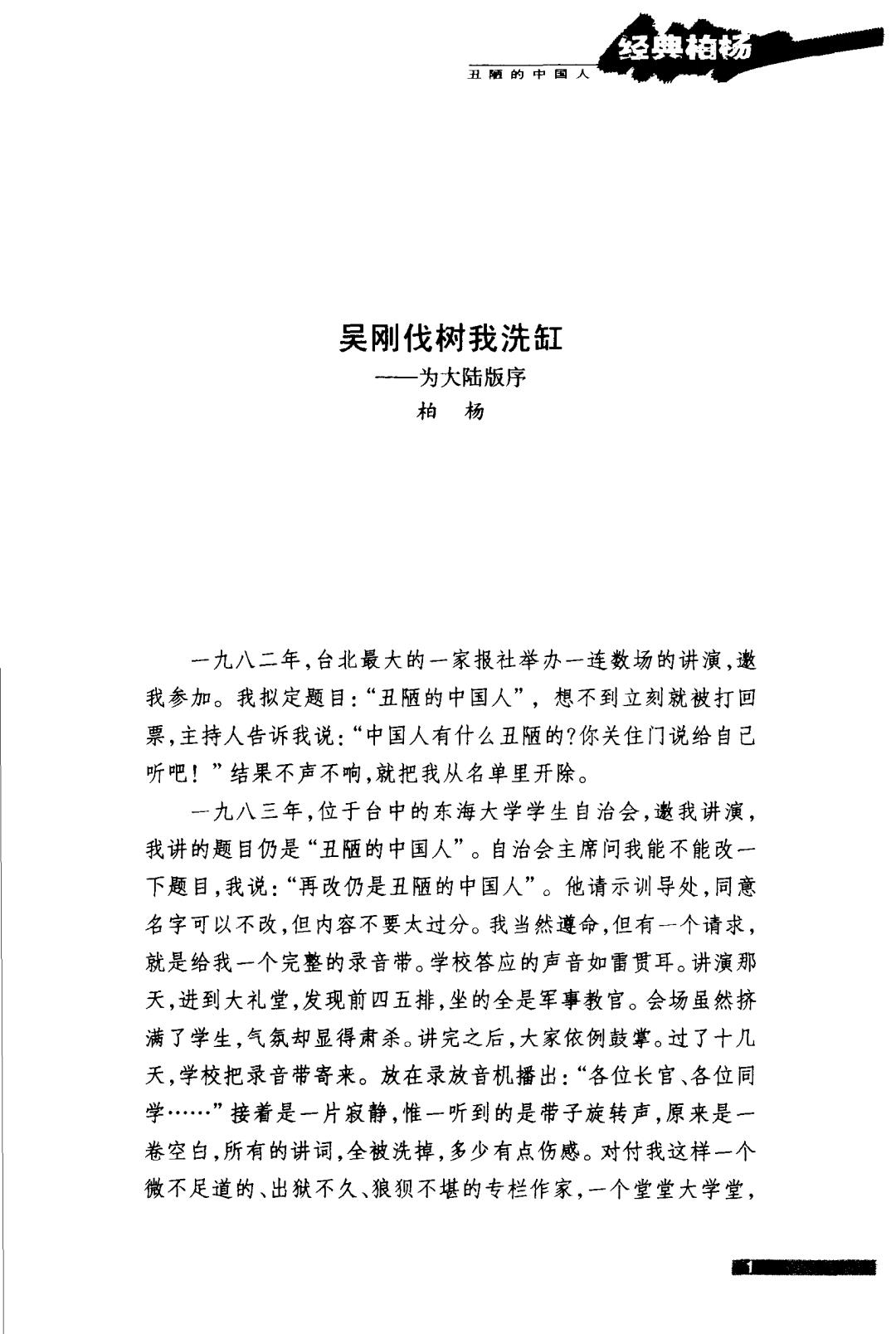
经典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 吴刚伐树我洗缸 一为大陆版序 柏杨 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 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中国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 票,主持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有什么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自已 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把我从名单里开除。 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学生自治会,邀我讲演, 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中国人”。自治会主席问我能不能改一 下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国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 名字可以不改,但内容不要太过分。我当然遵命,但有一个请求, 就是给我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学校答应的声音如雷贯耳。讲演那 天,进到大礼堂,发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事教宫。会场虽然挤 满了学生,气氛却显得肃杀。讲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过了十几 天,学校把录音带寄来。放在录放音机播出:“各位长官、各位同 学…”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到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来是一 卷空白,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多少有点伤感。对付我这样一个 微不足道的、出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作家,一个堂堂大学堂

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我是这么重要吗?我不认为我是这么重 要。但既然连一个大学堂都认为我很重要,我想我大概是很重 要。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华一同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 计划的邀请。在五月花大楼住了三个月,我们充满了惊奇、愉快、 满足,和丰富的回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在爱荷华大学,再次地 讲演“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俱乐部的教 室里,听众三分之二是黄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我不再叙述讲演的过程,只说讲演结束的时候,刹那间,我 感觉到一片幽静,好像深谷那样的幽静。连一声礼貌性的鼓掌都 没有,而听众们却一个一个站起来,纷纷离席。我期待握手、寒暄 的情景,没有出现。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 上,我们相对无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录音带,才辗转到我 手上,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香华请一位华人朋友吕嘉行先生帮我 整理下来。假设这时候,录音带发现空白,我一点也不稀奇。然 而,吕先生全部记下来之后,竟没有一点空白,真是感触良深。我 们的东海大学和人家的爱荷华大学,在这一点小动作上,怎么竟 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向爱荷华大学致敬。 《丑陋的中国人》除了中文本外,还有三种译本,日文、德 文、英文。一九八六年,日文译本出版时,我和香华受邀从台北飞 到东京。在新书发表会上,一群一口流利中文的日本记者,逼着 我问:“以一个中国人的身分,站在我们日本土地上,对你自己的 同胞,无情地指责和揭发,使我们日本人看不起中国人。请问你 会不会感到羞愧?”我回答说:“我想,以各位流利的华语和各位 访问中国时所写出来的报道,我请各位诚实地,用你的专业荣誉 保证,诚实地回答我,在看到《丑陋的中国人》之前,难道你就看 得起中国人吗?你难道从不耻笑中国人吗?”大家互相看看,尴尬 地点点头。我说:“你们事实上根本就看不起中国人,但因为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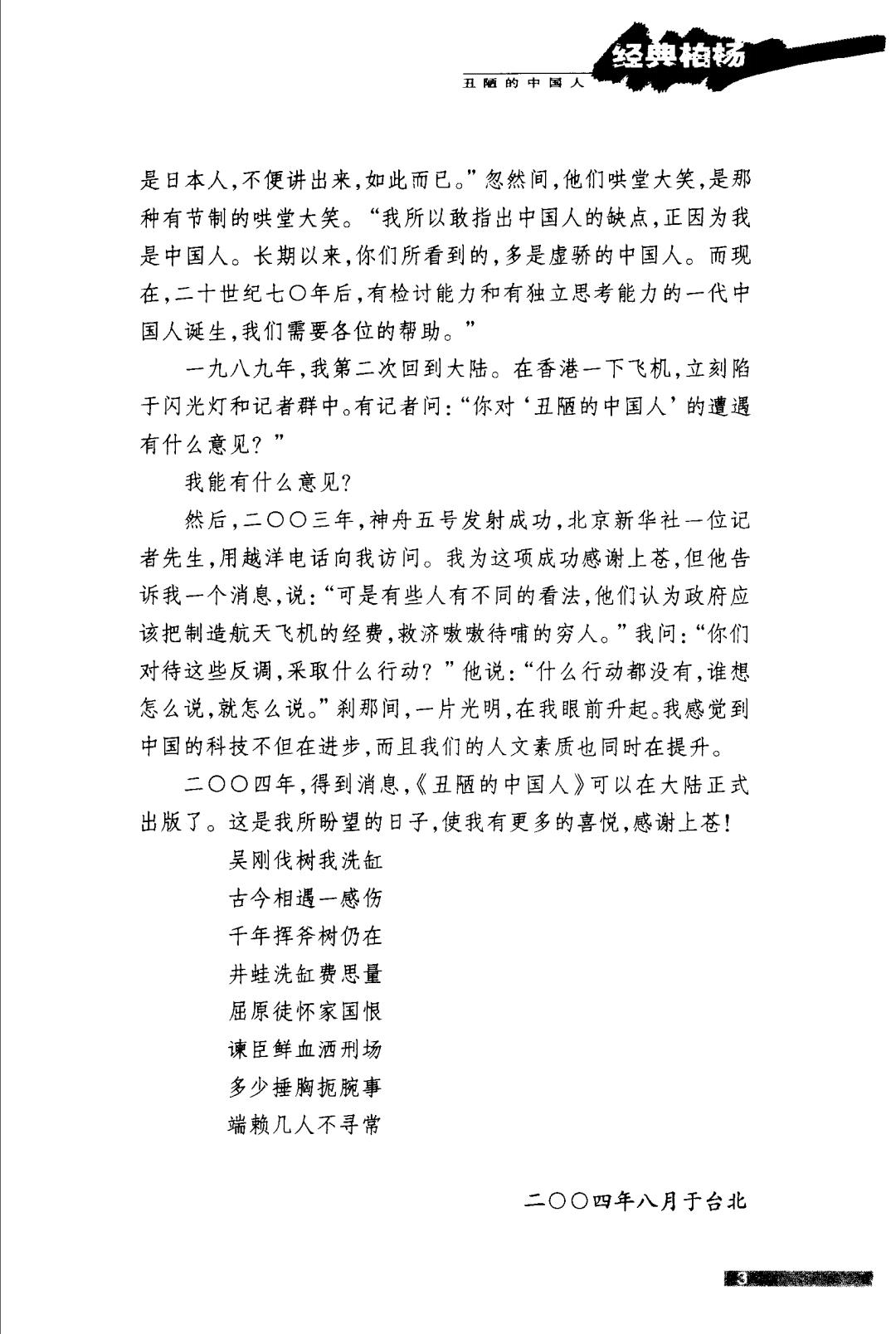
经興柏杨 丑陋的中国人 是日本人,不便讲出来,如此而已。”忽然间,他们哄堂大笑,是那 种有节制的哄堂大笑。“我所以敢指出中国人的缺点,正因为我 是中国人。长期以来,你们所看到的,多是虚骄的中国人。而现 在,二十世纪七○年后,有检讨能力和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一代中 国人诞生,我们需要各位的帮助。” 一九八九年,我第二次回到大陆。在香港一下飞机,立刻陷 于闪光灯和记者群中。有记者问:“你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遭遇 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然后,二。○三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北京新华社一位记 者先生,用越洋电话向我访问。我为这项成功感谢上苍,但他告 诉我一个消息,说:“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应 该把制造航天飞机的经费,救济嗷嗷待哺的穷人。”我问:“你们 对待这些反调,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什么行动都没有,谁想 怎么说,就怎么说。”刹那间,一片光明,在我眼前升起。我感觉到 中国的科技不但在进步,而且我们的人文素质也同时在提升。 二○O四年,得到消息,《丑陋的中国人》可以在大陆正式 出版了。这是我所盼望的日子,使我有更多的喜悦,感谢上苍! 吴刚伐树我洗缸 古今相遇一感伤 千年挥斧树仍在 井蛙洗缸费思量 屈原徒怀家国恨 谏臣鲜血洒刑场 多少捶胸扼腕事 端赖几人不寻常 二○O四年八月于台北 3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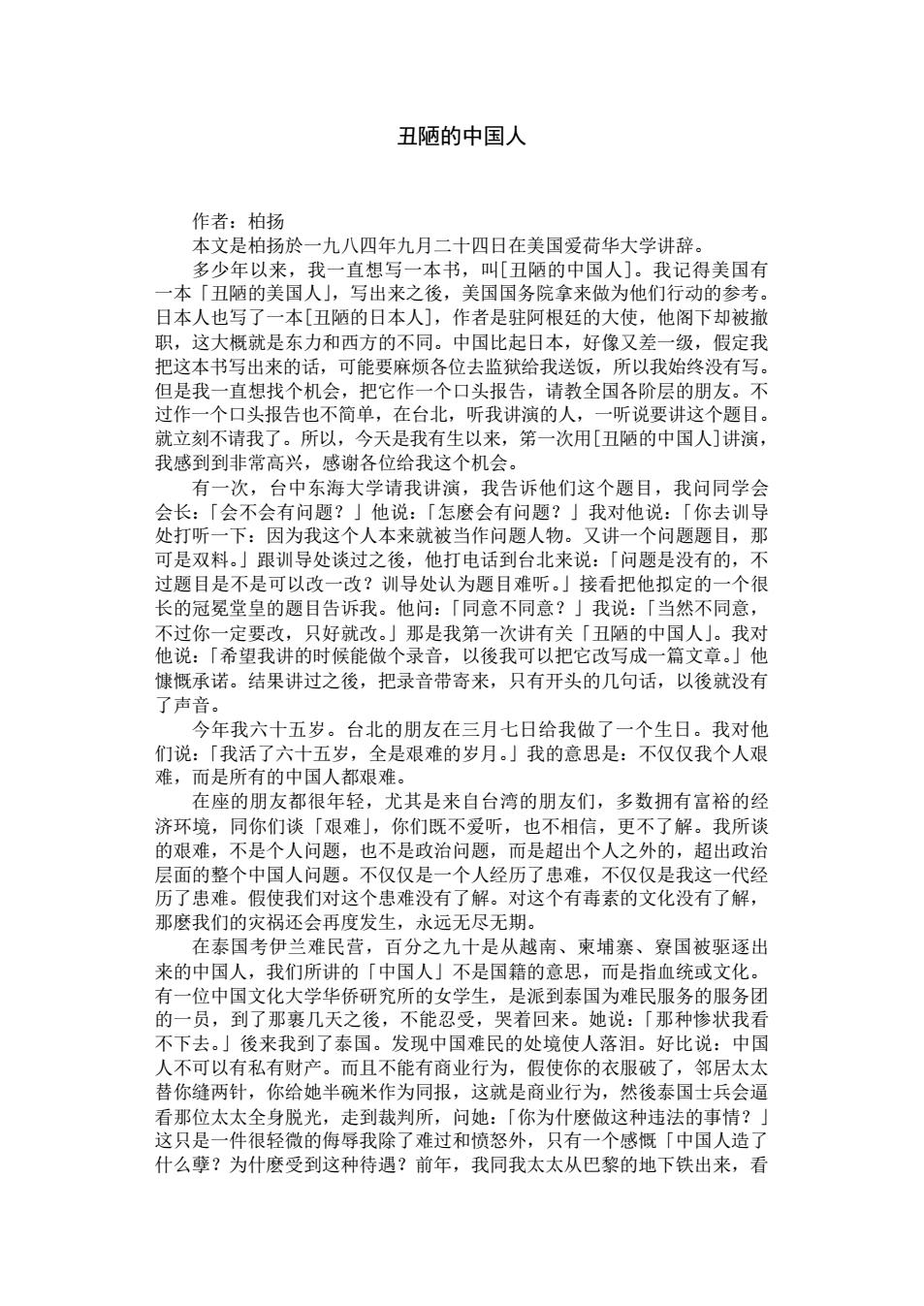
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柏扬 本文是柏扬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 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 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 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 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 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 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日。 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 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 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 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 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 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 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 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 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 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 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 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 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 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 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 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 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 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 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 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 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 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 不下去。」後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 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 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 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 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
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柏扬 本文是柏扬於一九八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讲辞。 多少年以来,我一直想写一本书,叫[丑陋的中国人]。我记得美国有 一本「丑陋的美国人」,写出来之後,美国国务院拿来做为他们行动的参考。 日本人也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作者是驻阿根廷的大使,他阁下却被撤 职,这大概就是东力和西方的不同。中国比起日本,好像又差一级,假定我 把这本书写出来的话,可能要麻烦各位去监狱给我送饭,所以我始终没有写。 但是我一直想找个机会,把它作一个口头报告,请教全国各阶层的朋友。不 过作一个口头报告也不简单,在台北,听我讲演的人,一听说要讲这个题目。 就立刻不请我了。所以,今天是我有生以来,笫一次用[丑陋的中国人]讲演, 我感到到非常高兴,感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有一次,台中东海大学请我讲演,我告诉他们这个题目,我问同学会 会长:「会不会有问题?」他说:「怎麽会有问题?」我对他说:「你去训导 处打听一下:因为我这个人本来就被当作问题人物。又讲一个问题题目,那 可是双料。」跟训导处谈过之後,他打电话到台北来说:「问题是没有的,不 过题目是不是可以改一改?训导处认为题目难听。」接看把他拟定的一个很 长的冠冕堂皇的题目告诉我。他问:「同意不同意?」我说:「当然不同意, 不过你一定要改,只好就改。」那是我第一次讲有关「丑陋的中国人」。我对 他说:「希望我讲的时候能做个录音,以後我可以把它改写成一篇文章。」他 慷慨承诺。结果讲过之後,把录音带寄来,只有开头的几句话,以後就没有 了声音。 今年我六十五岁。台北的朋友在三月七日给我做了一个生日。我对他 们说:「我活了六十五岁,全是艰难的岁月。」我的意思是:不仅仅我个人艰 难,而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艰难。 在座的朋友都很年轻,尤其是来自台湾的朋友们,多数拥有富裕的经 济环境,同你们谈「艰难」,你们既不爱听,也不相信,更不了解。我所谈 的艰难,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超出个人之外的,超出政治 层面的整个中国人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人经历了患难,不仅仅是我这一代经 历了患难。假使我们对这个患难没有了解。对这个有毒素的文化没有了解, 那麽我们的灾祸还会再度发生,永远无尽无期。 在泰国考伊兰难民营,百分之九十是从越南、柬埔寨、寮国被驱逐出 来的中国人,我们所讲的「中国人」不是国籍的意思,而是指血统或文化。 有一位中国文化大学华侨研究所的女学生,是派到泰国为难民服务的服务团 的一员,到了那裹几天之後,不能忍受,哭着回来。她说:「那种惨状我看 不下去。」後来我到了泰国。发现中国难民的处境使人落泪。好比说:中国 人不可以有私有财产。而且不能有商业行为,假使你的衣服破了,邻居太太 替你缝两针,你给她半碗米作为同报,这就是商业行为,然後泰国士兵会逼 看那位太太全身脱光,走到裁判所,问她:「你为什麽做这种违法的事情?」 这只是一件很轻微的侮辱我除了难过和愤怒外,只有一个感慨「中国人造了 什么孽?为什麽受到这种待遇?前年,我同我太太从巴黎的地下铁出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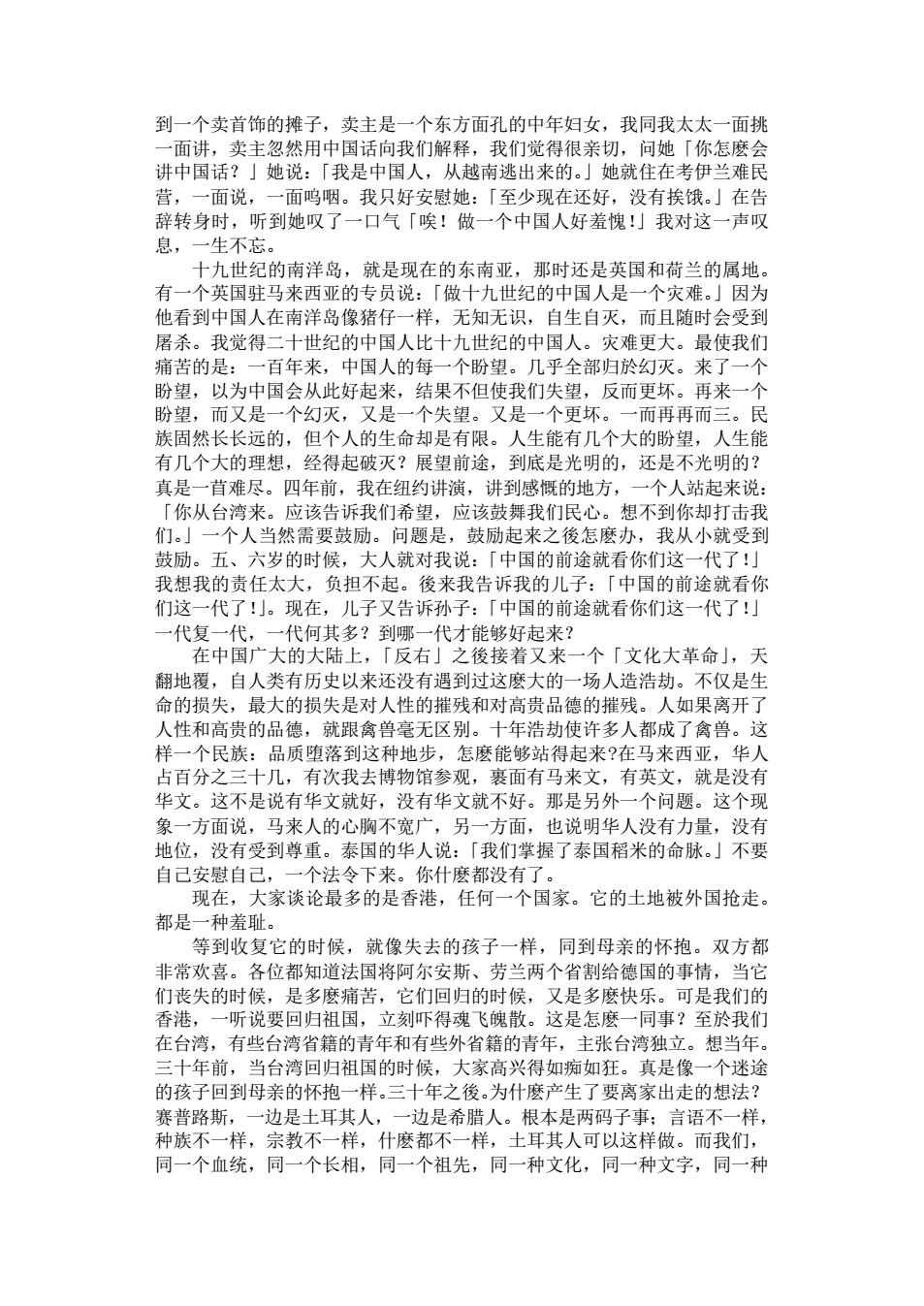
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 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 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 营,一面说,一面鸣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 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 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 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 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 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 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 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 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 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 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 真是一首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 「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 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 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 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 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 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 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 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 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 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西亚,华人 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 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 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 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 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 都是一种羞耻。 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 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 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麼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 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麽一同事?至於我们 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 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 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 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 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 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
到一个卖首饰的摊子,卖主是一个东方面孔的中年妇女,我同我太太一面挑 一面讲,卖主忽然用中国话向我们解释,我们觉得很亲切,问她「你怎麽会 讲中国话?」她说:「我是中国人,从越南逃出来的。」她就住在考伊兰难民 营,一面说,一面呜咽。我只好安慰她:「至少现在还好,没有挨饿。」在告 辞转身时,听到她叹了一口气「唉!做一个中国人好羞愧!」我对这一声叹 息,一生不忘。 十九世纪的南洋岛,就是现在的东南亚,那时还是英国和荷兰的属地。 有一个英国驻马来西亚的专员说:「做十九世纪的中国人是一个灾难。」因为 他看到中国人在南洋岛像猪仔一样,无知无识,自生自灭,而且随时会受到 屠杀。我觉得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比十九世纪的中国人。灾难更大。最使我们 痛苦的是:一百年来,中国人的每一个盼望。几乎全部归於幻灭。来了一个 盼望,以为中国会从此好起来,结果不但使我们失望,反而更坏。再来一个 盼望,而又是一个幻灭,又是一个失望。又是一个更坏。一而再再而三。民 族固然长长远的,但个人的生命却是有限。人生能有几个大的盼望,人生能 有几个大的理想,经得起破灭?展望前途,到底是光明的,还是不光明的? 真是一苜难尽。四年前,我在纽约讲演,讲到感慨的地方,一个人站起来说: 「你从台湾来。应该告诉我们希望,应该鼓舞我们民心。想不到你却打击我 们。」一个人当然需要鼓励。问题是,鼓励起来之後怎麽办,我从小就受到 鼓励。五、六岁的时候,大人就对我说:「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 我想我的责任太大,负担不起。後来我告诉我的儿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 们这一代了!」。现在,儿子又告诉孙子:「中国的前途就看你们这一代了!」 一代复一代,一代何其多?到哪一代才能够好起来? 在中国广大的大陆上,「反右」之後接着又来一个「文化大革命」,天 翻地覆,自人类有历史以来还没有遇到过这麽大的一场人造浩劫。不仅是生 命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对人性的摧残和对高贵品德的摧残。人如果离开了 人性和高贵的品德,就跟禽兽毫无区别。十年浩劫使许多人都成了禽兽。这 样一个民族:品质堕落到这种地步,怎麽能够站得起来?在马来西亚,华人 占百分之三十几,有次我去博物馆参观,裹面有马来文,有英文,就是没有 华文。这不是说有华文就好,没有华文就不好。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现 象一方面说,马来人的心胸不宽广,另一方面,也说明华人没有力量,没有 地位,没有受到尊重。泰国的华人说:「我们掌握了泰国稻米的命脉。」不要 自己安慰自己,一个法令下来。你什麽都没有了。 现在,大家谈论最多的是香港,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土地被外国抢走。 都是一种羞耻。 等到收复它的时候,就像失去的孩子一样,同到母亲的怀抱。双方都 非常欢喜。各位都知道法国将阿尔安斯、劳兰两个省割给德国的事情,当它 们丧失的时候,是多麽痛苦,它们回归的时候,又是多麽快乐。可是我们的 香港,一听说要回归祖国,立刻吓得魂飞魄散。这是怎麽一同事?至於我们 在台湾,有些台湾省籍的青年和有些外省籍的青年,主张台湾独立。想当年。 三十年前,当台湾回归祖国的时候,大家高兴得如痴如狂。真是像一个迷途 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三十年之後。为什麽产生了要离家出走的想法? 赛普路斯,一边是土耳其人,一边是希腊人。根本是两码子事;言语不一样, 种族不一样,宗教不一样,什麽都不一样,土耳其人可以这样做。而我们, 同一个血统,同一个长相,同一个祖先,同一种文化,同一种文字,同一种

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 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 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 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 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 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 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 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 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 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 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 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 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 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 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 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 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 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 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 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 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 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 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 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 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 出狱之後,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 例予?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 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 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 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 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们:「你为 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麽讲了几句实话就 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 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 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 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 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 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 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 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
语言,只不过住的地域不同而已,怎麽会有这种现象? 这种种事情,使得做为一个中国人,不但艰难,而且羞辱、痛苦。就 是身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不晓得他是怎麽一回事,左、右、中、独、中偏左、 左偏中、中偏右、右偏中等等。 简直没有共同语言。互相把对方当作杀父之仇,这算是一个什麽样的 民族?这算是一个什縻样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麽历史悠 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 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 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後裔。为什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 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 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侯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 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麽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 的前途坦落,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 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 母亲悲怆的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麽?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 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 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再看大陆上的一些孩子,从小就要斗,就要诈欺, 就要练习出卖朋友同志,就要满口谎言。多可怕的教育,我们要靠下一代, 下一代却是这种样子。 我在台湾三十多年,写小说十年,写杂文十年,坐牢十年,现在将是 写历史十年,平均分配。为什麽我不写小说了?我觉得写小说比较间接,要 透过一个形式,一些人物,所以我改写杂文。杂文像匕首一样,可以直接插 入罪恶的心脏。杂文就好像一个人坐在司机的旁边一直提醒司机,你已经开 错了,应该左转,应该右转,应该靠边走,不应该在双黄线上超车,前面有 桥,应该放缓油门,前面有一个十字路口,有红灯等等。不停的提醒,不停 的叫,叫多了以後就被关进大牢。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 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我自己在牢房裹沉思,我为什麽坐牢,我犯了什麽罪?犯了什麽法? 出狱之後,我更不断的探讨,像我这样的遭遇,是不是一个变态的、特殊的 例予?我到爱荷华,正式和大陆的作家在一起,使我发现,像我这种人,上 帝注定要我坐牢,不在台湾坐牢,就在大陆坐牢。 他们同我讲:「你这个脾气,到不了红卫兵,到不了文化大革命,反右 就把你反掉了。」为什麽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 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间他们:「你为 什麽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麽讲了几句实话就 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前几 天,有位从北京来的「全国作家协会」的党书记,我同他谈,把我气得讲不 出话来。我觉得我吵架还蛮有本领,可是那一次真把我一棍于打闷了。但不 能怪他,甚至於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 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後,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得是对的。 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得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 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裹。」我年纪大了之後,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 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裹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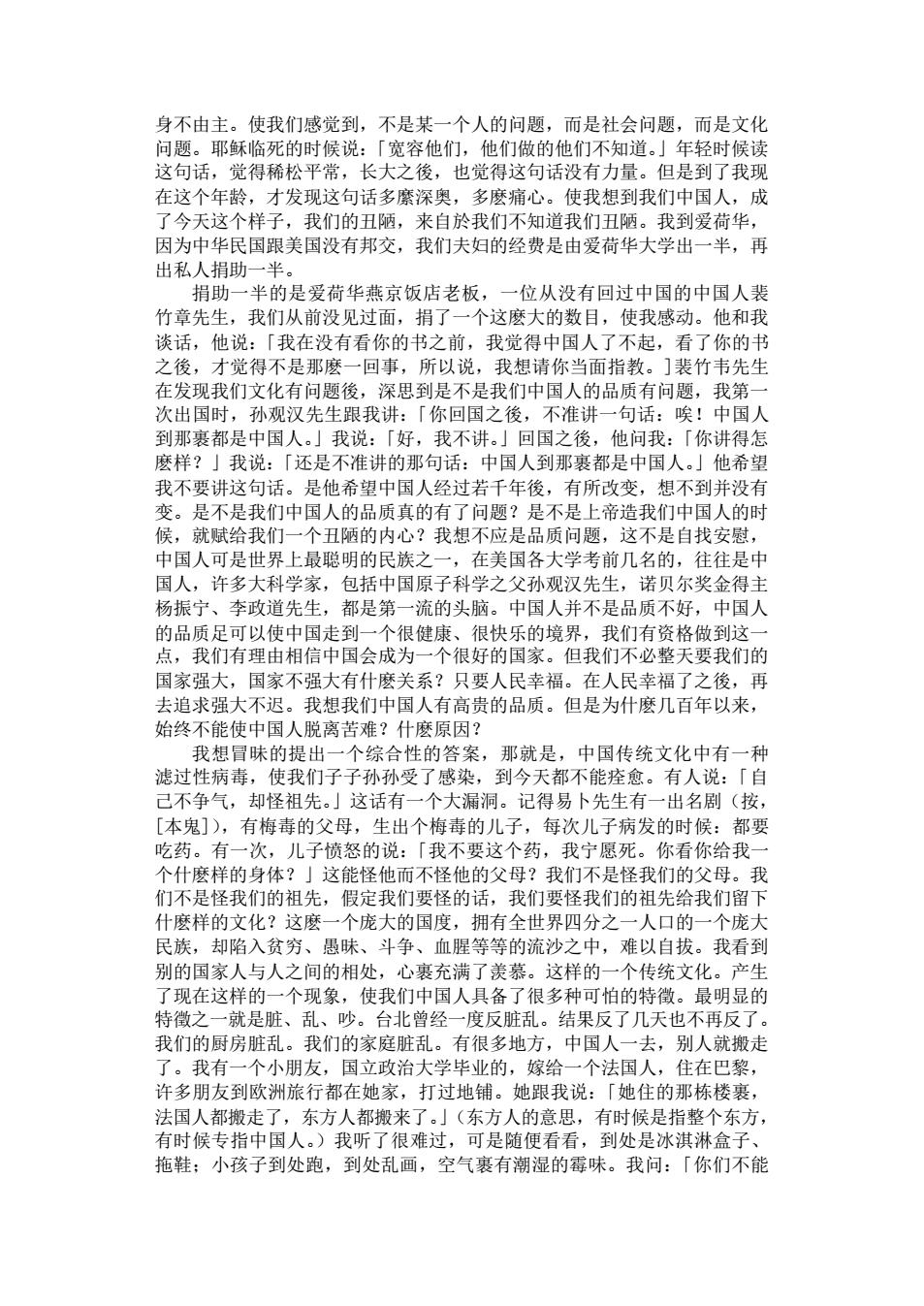
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 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 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 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 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 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 出私人捐助一半。 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 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 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 之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裴竹韦先生 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 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 到那裹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後,他问我:「你讲得怎 麽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希望 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千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 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 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 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 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 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 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 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 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 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 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 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 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按, [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 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 个什麽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 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 什麽样的文化?这麽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 民族,却陷入贫穷、愚味、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 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裹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 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最明显的 特徵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 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 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 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裹, 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 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 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裹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
身不由主。使我们感觉到,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而是文化 问题。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年轻时候读 这句话,觉得稀松平常,长大之後,也觉得这句话没有力量。但是到了我现 在这个年龄,才发现这句话多縻深奥,多麽痛心。使我想到我们中国人,成 了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丑陋,来自於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我到爱荷华, 因为中华民国跟美国没有邦交,我们夫妇的经费是由爱荷华大学出一半,再 出私人捐助一半。 捐助一半的是爱荷华燕京饭店老板,一位从没有回过中国的中国人裴 竹章先生,我们从前没见过面,捐了一个这麽大的数目,使我感动。他和我 谈话,他说:「我在没有看你的书之前,我觉得中国人了不起,看了你的书 之後,才觉得不是那麽一回事,所以说,我想请你当面指教。]裴竹韦先生 在发现我们文化有问题後,深思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有问题,我第一 次出国时,孙观汉先生跟我讲:「你回国之後,不准讲一句话:唉!中国人 到那裹都是中国人。」我说:「好,我不讲。」回国之後,他问我:「你讲得怎 麽样?」我说:「还是不准讲的那句话:中国人到那裹都是中国人。」他希望 我不要讲这句话。是他希望中国人经过若千年後,有所改变,想不到并没有 变。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品质真的有了问题?是不是上帝造我们中国人的时 候,就赋给我们一个丑陋的内心?我想不应是品质问题,这不是自找安慰, 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 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 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 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 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 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麽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後,再 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麽几百年以来, 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麽原因? 我想冒昧的提出一个综合性的答案,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 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有人说:「自 己不争气,却怪祖先。」这话有一个大漏洞。记得易卜先生有一出名剧(按, [本鬼]),有梅毒的父母,生出个梅毒的儿子,每次儿子病发的时候:都要 吃药。有一次,儿子愤怒的说:「我不要这个药,我宁愿死。你看你给我一 个什麽样的身体?」这能怪他而不怪他的父母?我们不是怪我们的父母。我 们不是怪我们的祖先,假定我们要怪的话,我们要怪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 什麽样的文化?这麽一个庞大的国度,拥有全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一个庞大 民族,却陷入贫穷、愚昧、斗争、血腥等等的流沙之中,难以自拔。我看到 别的国家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心裹充满了羡慕。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 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徵。最明显的 特徵之一就是脏、乱、吵。台北曾经一度反脏乱。结果反了几天也不再反了。 我们的厨房脏乱。我们的家庭脏乱。有很多地方,中国人一去,别人就搬走 了。我有一个小朋友,国立政治大学毕业的,嫁给一个法国人,住在巴黎, 许多朋友到欧洲旅行都在她家,打过地铺。她跟我说:「她住的那栋楼裹, 法国人都搬走了,东方人都搬来了。」(东方人的意思,有时候是指整个东方, 有时候专指中国人。)我听了很难过,可是随便看看,到处是冰淇淋盒子、 拖鞋;小孩子到处跑,到处乱画,空气裹有潮湿的霉味。我问:「你们不能

弄乾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麽样 提醒之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於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 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 个广东人在那裹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 来了,问他们在干什麽?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 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要不然我怎 麽会那麽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 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 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 独的口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曰本 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 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 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 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 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 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 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巨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 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 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 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 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 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 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 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中国有一句 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 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 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 教书的朋友家裹,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 「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 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 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裹 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 人,而是中国人。 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 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 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 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 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 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麽 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麼!谁
弄乾净吗?」她说:「不能。」不但外国人觉得我们脏,我们乱。经过这麽样 提醒之後,我们自己也觉得我们脏、我们乱。至於吵,中国人的嗓门之大, 真是天下无双,尤以广东老乡的噪门最为叫座。有个发生在美国的笑话:两 个广东人在那裹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 来了,问他们在干什麽?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麽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 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噪门高,理都跑到我这裹来了,要不然我怎 麽会那麽气愤?我想这几点足使中国人的形象受到破坏,使我们的内心不能 平安。因为吵、脏、乱,自然会影响内心,窗明几净和又脏又乱,是两个完 全不一样的世界。 至於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每一个单 独的口本人。看起来都像一条猪,可是三个日本人加起来就是一条龙:曰本 人的团队精神使日本所向无敌。中国人打仗打不过日本人,做生意也做不过 日本人,就在台北,三个日本人做生意,好,这次是你的,下次是我的。中 国人做生意,就显现出中国人的丑陋程度,你卖五十。我卖四十,你卖三十, 我卖二十。所以说。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条龙,中国入讲起话来头头是道。 上可以把太阳一口气吹灭,下可以治国平天下。中国人在单独一个位置上。 譬如在研究室里,在考场上,在不需要有人际关系的情况下,他可以有了不 起的发展。但是三个中国人加在一起,三巨条龙加在一起。就成了一条猪、 一条虫,甚至连虱都不如。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 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所以外国人 批评中国人不知道团结,我只好说:「你知道中国人不团结是什麽意思?是 上帝的意思!因为中国有十亿人口,团结起来,万众一心,你受得了?是上 帝可怜你们,才教中国人不团结。」我一面讲,一面痛彻心腑。 中国人不但不团结,反而有不团结的充分理由,每一个人都可以把这 个理由写成一本书。各位在美国看得最清楚,最好的标本就在眼前,任何一 个华人社会,至少分成三百六十五派,互相想把对方置於死地。中国有一句 话:一个和尚担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人多有什麽用? 中国人在内心上根本就不了解合作的重要性。可是你说他不了解,他可以写 一本团结重要的书给你看看。我上次(一九八一)来美国,住在一个在大学 教书的朋友家裹,谈得头头是道,天文地理,怎麽样救国等等,第二天我说: 「我要到张三那儿去一下。」他一听是张三,就眼冒不屑的火光,我说:「你 送我去一下吧!」他说:「我不送,你自己去好了。」都在美国学校教书,都 是从一个家乡来的,竟不能互相容忍,那还讲什麽理性?所以中国人的窝裹 斗,是一项严重的特徵。 各位在美国更容易体会到这一点,凡是整中国人最厉害的人不是外国 人,而是中国人。 凡是出卖中国人的:也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凡是陷害中国人的, 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在马来西亚就有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朋友住 在那儿开矿,一下子被告了,告得很严重,追查之下,告他的原来是个老朋 友,一块从中国来的,在一起打天下的。朋友质问他怎麽做出这种下流的事? 那人说:「一块儿打天下是一块儿打天下,你现在高楼大厦,我现在搞的没 办法,我不告你告谁?」所以搞中国人的还是中国人。譬如说,在美国这麽 大的一个国度,沧海一粟。怎麽会有人知道你是非法入境?有人告你麽!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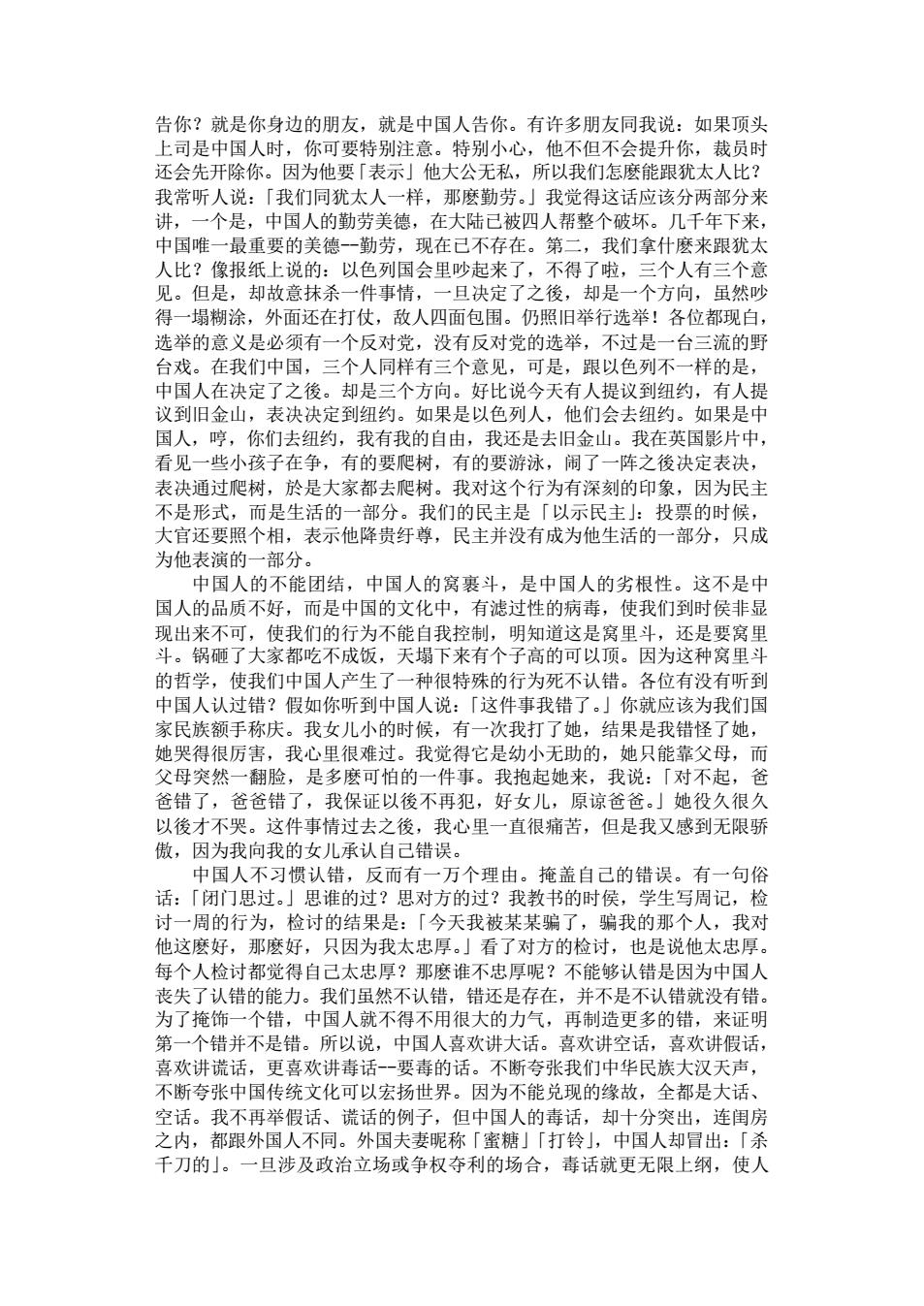
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 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 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 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 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 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一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麽来跟犹太 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 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 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白, 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 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 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後。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 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 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 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 表决通过爬树,於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 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 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 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 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 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 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 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 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 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 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 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 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後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役久很久 以後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 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 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 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 他这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 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 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 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 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 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 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 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 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 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
告你?就是你身边的朋友,就是中国人告你。有许多朋友同我说:如果顶头 上司是中国人时,你可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他不但不会提升你,裁员时 还会先开除你。因为他要「表示」他大公无私,所以我们怎麽能跟犹太人比? 我常听人说:「我们同犹太人一样,那麽勤劳。」我觉得这话应该分两部分来 讲,一个是,中国人的勤劳美德,在大陆已被四人帮整个破坏。几千年下来, 中国唯一最重要的美德--勤劳,现在已不存在。第二,我们拿什麽来跟犹太 人比?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 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後,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 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各位都现白, 选举的意义是必须有一个反对党,没有反对党的选举,不过是一台三流的野 台戏。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 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後。却是三个方向。好比说今天有人提议到纽约,有人提 议到旧金山,表决决定到纽约。如果是以色列人,他们会去纽约。如果是中 国人,哼,你们去纽约,我有我的自由,我还是去旧金山。我在英国影片中, 看见一些小孩子在争,有的要爬树,有的要游泳,闹了一阵之後决定表决, 表决通过爬树,於是大家都去爬树。我对这个行为有深刻的印象,因为民主 不是形式,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的民主是「以示民主」:投票的时候, 大官还要照个相,表示他降贵纡尊,民主并没有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成 为他表演的一部分。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裹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 国人的品质不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侯非显 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 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 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 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 家民族额手称庆。我女儿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打了她,结果是我错怪了她, 她哭得很厉害,我心里很难过。我觉得它是幼小无助的,她只能靠父母,而 父母突然一翻脸,是多麽可怕的一件事。我抱起她来,我说:「对不起,爸 爸错了,爸爸错了,我保证以後不再犯,好女儿,原谅爸爸。」她役久很久 以後才不哭。这件事情过去之後,我心里一直很痛苦,但是我又感到无限骄 傲,因为我向我的女儿承认自己错误。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有一句俗 话:「闭门思过。」思谁的过?思对方的过?我教书的时侯,学生写周记,检 讨一周的行为,检讨的结果是:「今天我被某某骗了,骗我的那个人,我对 他这麽好,那麽好,只因为我太忠厚。」看了对方的检讨,也是说他太忠厚。 每个人检讨都觉得自己太忠厚?那麽谁不忠厚呢?不能够认错是因为中国人 丧失了认错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认错,错还是存在,并不是不认错就没有错。 为了掩饰一个错,中国人就不得不用很大的力气,再制造更多的错,来证明 第一个错并不是错。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 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要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 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宏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 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 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 千刀的」。一旦涉及政治立场或争权夺利的场合,毒话就更无限上纲,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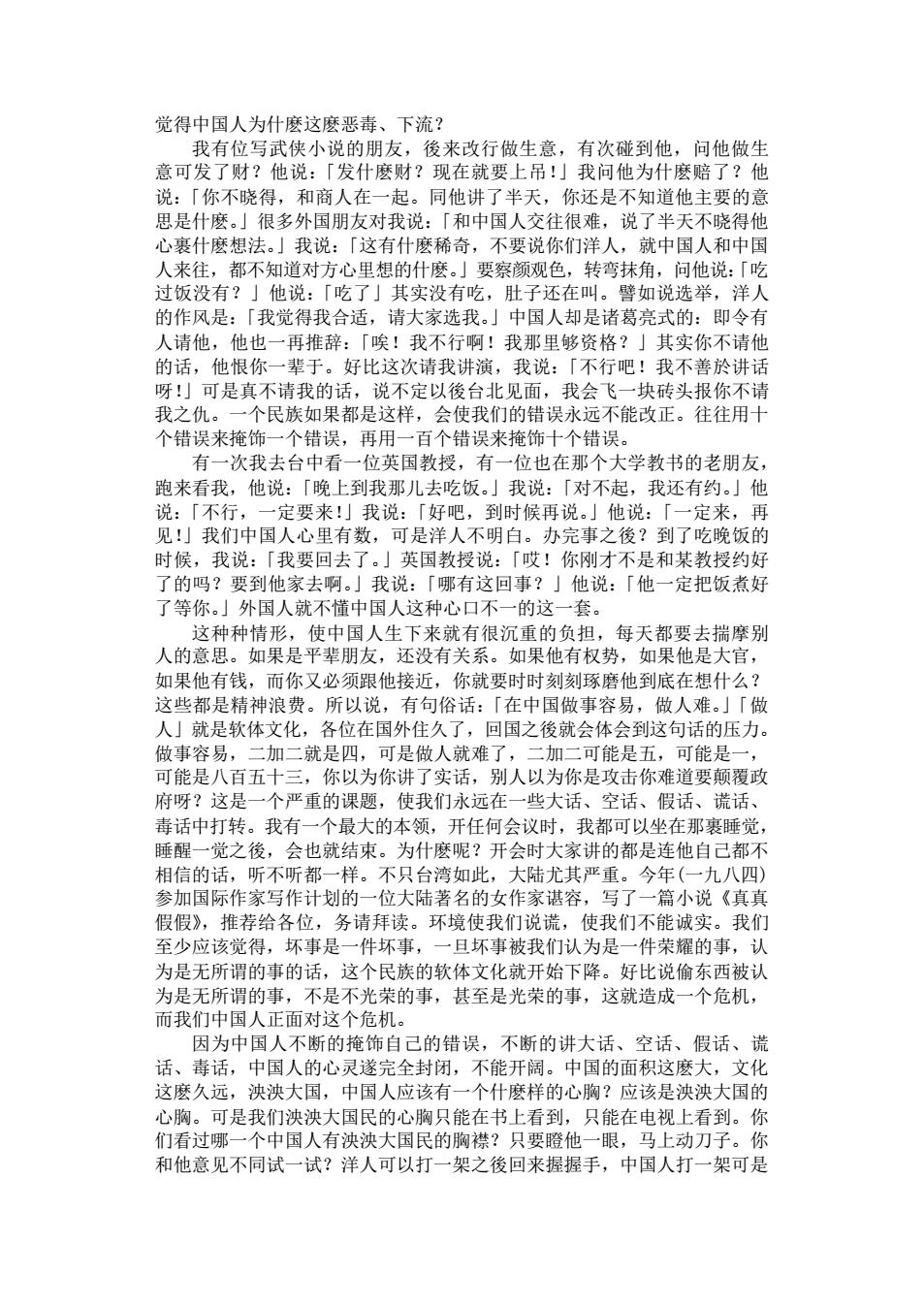
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後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 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 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 思是什麽。」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 心裹什麽想法。」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 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 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 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 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 的话,他恨你一辈于。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於讲话 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後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 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 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 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 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 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饭的 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 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 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 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 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 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 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後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 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 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 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 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 睡醒一觉之後,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 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 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 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 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 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 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 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 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 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 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 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 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
觉得中国人为什麽这麽恶毒、下流? 我有位写武侠小说的朋友,後来改行做生意,有次碰到他,问他做生 意可发了财?他说:「发什麽财?现在就要上吊!」我问他为什麽赔了?他 说:「你不晓得,和商人在一起。同他讲了半天,你还是不知道他主要的意 思是什麽。」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 心裹什麽想法。」我说:「这有什麽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 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麽。」要察颜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 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 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 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那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 的话,他恨你一辈于。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於讲话 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後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 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 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有一次我去台中看一位英国教授,有一位也在那个大学教书的老朋友, 跑来看我,他说:「晚上到我那儿去吃饭。」我说:「对不起,我还有约。」他 说:「不行,一定要来!」我说:「好吧,到时候再说。」他说:「一定来,再 见!」我们中国人心里有数,可是洋人不明白。办完事之後?到了吃晚饭的 时候,我说:「我要回去了。」英国教授说:「哎!你刚才不是和某教授约好 了的吗?要到他家去啊。」我说:「哪有这回事?」他说:「他一定把饭煮好 了等你。」外国人就不懂中国人这种心口不一的这一套。 这种种情形,使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 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 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 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 人」就是软体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後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 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 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 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 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裹睡觉, 睡醒一觉之後,会也就结束。为什麽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 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不只台湾如此,大陆尤其严重。今年(一九八四) 参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的一位大陆著名的女作家谌容,写了一篇小说《真真 假假》,推荐给各位,务请拜读。环境使我们说谎,使我们不能诚实。我们 至少应该觉得,坏事是一件坏事,一旦坏事被我们认为是一件荣耀的事,认 为是无所谓的事的话,这个民族的软体文化就开始下降。好比说偷东西被认 为是无所谓的事,不是不光荣的事,甚至是光荣的事,这就造成一个危机, 而我们中国人正面对这个危机。 因为中国人不断的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的讲大话、空话、假话、谎 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麽大,文化 这麽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麽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 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 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 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後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